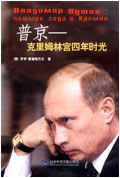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娜更能了解这个问题,但他害怕得到这个答案。那半公升酒也没有提供出答案来。
酒至少使他的脑筋昏昏沉沉,十点后就步履蹒跚地上床睡觉,留下身后的灯一夜未
关。
刚过十一点,一辆小轿车沿着这个公寓前面的林荫大道开过来,一双蓝眼睛在
查看上校的窗户。这回是艾德〔爱德华·弗利的昵称。——译者〕·弗利。他注意
到那些遮光帘。在去他自己公寓的路上,又传递了另一个秘密信息。一个莫斯科清
洁工设下了许多信号。信号看来是不显眼的东西,例如,在灯柱上用粉笔作个记号,
每个记号就是告诉情报传递小组的一部分人要各就各位。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的另
一个人黎明时去检查这些暗号,发现任何异常,弗利就得中止一切活动。
尽管工作紧张,艾德·弗利也发现了许多有趣的方面。举一个例子,俄国人把
红衣主教的宿舍安排在交通繁忙的大街上,就是他们自己给情报工作带来了方便。
又如,他们把大使馆新楼弄得一团糟,使他和他的家属不能住在新院子里,弗利和
他的妻子不得不每天晚上开车走过这条林荫大道。夫妻俩非常高兴的是让儿子参加
了他们的冰球队。离开这个地方他定会怀念这里的,弗利下车时这样自言自语。他
现在喜欢青少年冰球超过了棒球。唔,还有英国式足球。他不希望儿子打(美式)
足球,孩子们受伤的太多了,他还长得不够大。那是将来的事情,眼前还有要担心
的呢。
他在寓所高声说话时不得不小心。美国人住的每一套房子的每一间屋子都安有
大量的窃听器,比蚁巢还密。可是这些年来,艾德和玛丽·帕特也对它开过玩笑。
他进屋来挂好上衣,就吻他的妻子,同时在她的耳朵上搔痒痒。她咯咯笑着表示认
可,虽然两个人由于工作的重担都已筋疲力竭了,不过还有几个月了。
“招待会怎么样?”她问给墙上的麦克风听。
“老一套废话。”录上的是这句回答。
09、机遇
碧翠丝·陶塞格并没有作报告,然而她认为坎蒂失言讲出的事是重要的。她被
允许知道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发生的几乎一切事情,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
未列入计划的试验。当有的战略防御计划工作在欧洲和日本进行的时候,没有谁要
求阿尔·格雷戈里去作讲解。那说明是俄国人的试验,而且,如果他们用飞机把这
个小丑八怪接到华盛顿去——她还记得,他把汽车留在实验室了,那么他们是用直
升飞机把他接走的——这一定是件大事。她不喜欢格雷戈里,可没有理由怀疑他那
优秀的脑子。她不知道这是什么试验,直到现在还不允许她知道俄国的事,纪律约
束了她的好奇心。不能不这样办。她的所作所为是危险的。
这正是有趣的事,不是吗?她对自己笑了。
“只有三个人失踪。”阿富汗人走后,俄国人正在安-26残骸中仔细搜寻。说
话的是一个克格勃少校。他从来没有见过坠机,只是由于扑脸的冷空气才没有把他
的早餐吐出来。
“您手下的人?”苏军步兵大尉(不久以前还是阿富汗傀儡军里—个营的顾问)
四下张望,看他的队伍在外围防线上是否确已就位。他努力使自己不要恶心。看见
他的朋友在他面前几乎肠肚流出,是对他生命的极大震动。他不知道他的阿富汗同
志在紧急外科手术中熊否活下来。
“我认为还是失踪了。”飞机的机身已破成许多碎片,机上前部的人在坠地时
已经被浸在油里烧得无法辨认了。他们还是把所有尸体的碎片收集起来。实际上,
少了三具,将由法医们去确定谁死了和谁失踪了。他们对坠机的死难者一般不这样
关心——这架安-26在法律意义上属于苏联国家航空公司而不属于苏联空军——这
次却要竭尽全力。失踪的大尉属于克格勃第九(警卫)管理局,是一个行政人员,
他在这个地区巡回,在某些机密地区检查人事状况和保安活动。他旅行所携文件中
包括高度机密文件,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熟悉大量的克格勃人事和活动情况。文件可
能已经销毁,因为发现了一些已烧毁的公文包残渣。但是直到少校的死亡被确认之
前,莫斯科中心会有一些入愁苦不堪。
“他留下了一个家——噢,一个寡妇。听说他的儿子上个月刚刚死去,是癌症。”
克格勃少校平静地说。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照顾他的妻子。”大尉回答说。
“是的,我们有一个部门处理这种事。他们会不会把他拖走了?”
“唔,我们知道他们在这儿。他们总是洗劫坠机现场,找寻武器。文件呢?”
大尉耸了耸肩,“我们是在和无知的野人交战,少校同志。我怀疑他会对任何文件
感兴趣。他们可能从军服上认出他是一个克格勃军官,然后把他拖去肢解尸体。您
不会相信他们是怎样对待俘虏的。”
“野蛮人。”这个克格勃咕哝着,“打下一架非武装的客机。”他四下观望,
“忠诚的”阿富汗军队——那是对他们的一个乐观的形容词,他嘟嚷着发牢骚——
正在把尸体和碎块装进一些橡胶口袋,用直升飞机运回加兹尼,再飞往莫斯科去检
验身份,“要是把我手下人的尸体拖走了怎么办呢?”
“我们再也找不到它了。啊,还有点可能性,不过可能性不大。我们每看见一
只盘旋的秃鹰,就将派出一架直升飞机,可是……”大尉摇摇头,“其实你很可能
已经找到了尸体,少校同志。只需要一些时间来查证就是了。”
“可怜的家伙——坐办公室的人。这原本不是他的辖区,可是指派到这里来的
人胆囊有病住院了,他接过了这个额外的工作。”
“他平常的管区是哪里?”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猜想他是想用额外工作去驱散他的苦恼。”
“你感觉怎么样,俄国人?”神箭手问他的俘虏。他们不能提供多少医疗照顾。
离得最近的、由法国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医疗队,是在哈桑亥尔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他们自己能步行的伤员正朝那里走去。那些伤势较重的……唉,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呢?他们的止痛药、吗啡针剂,供应倒还充分,那是瑞士制造的,用来给垂死的人
注射以减少痛苦。有时吗啡帮助他们坚持下去,谁要是有复元的希望,就由担架运
往东南方的巴基斯坦边境去。那些经过六十英里长途跋涉还活着的人,在米拉姆沙
已关闭的机场附近能得到真正医院一样的治疗。神箭手领导这个小队。他成功地说
服了他的同志们——这个俄国人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为了这个俄国政治警察和他
的文件,美国人会给他们更多的东西。只有部落头人才能驳倒他的这个论点,可是
他已经死了。他们赶快按照自己的信仰把尸体埋葬好,现在他去天堂了。这使得神
箭手现在成为队里最年长、最受信任的战士。
新
谁能从他那隧石般坚利的眼光和冷冰冰的言语中,说清楚为什么他三年来第一
次产生了侧隐之心?连他本人也弄胡涂了。这些想法怎么会进入他的脑袋里来的?
这是安拉的旨意吗?一定是的,他想。别人谁能阻止我去杀死一个俄国人呢?
“痛。”俄国人最后回答。可是神箭手的恻隐心伸不了那么远,“圣战者”带
的吗啡是为他们自己用的。他环顾左右,确定没人看见之后,把俄国人的家里人照
片递还给他。刹那之间,他的眼光变得温和了。那个克格勃军官看着他,惊讶压倒
了疼痛。他那只好的手拿着照片,把它们紧贴在胸前。脸上露出谢意,感谢加上困
惑。那人想到他死去的儿子,思考自己的命运。在痛苦得迷迷糊糊之中他打定主意,
最坏的情况就是他同他的儿子重聚,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阿富汗人不能使他在身体
上和精神上更痛苦了。大尉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痛苦竟然成为药石,久尝之后,不
仅觉得可以容忍,而且几乎觉得舒适。他曾听说这是可能的,但他以前还不相信呢。
他的精神功能还没有完全活动起来。在朦胧状态中,他怀疑自己为什么没有被
杀掉。他在莫斯科听过许多关于阿富汗人如何对待俘虏的传说……那就是为什么你
在本职工作之外自愿承担这次巡逻任务的缘故……他不知道现在是否要送命,也不
知道是怎么搞成这样子的。
你不能死,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你必须活下去。你有一个妻子,她受够了
苦。他自言自语。她已经在受苦了……思想主动地停止了。大尉把照片塞进胸前的
口袋里,在他的身体还在努力自我治疗的的候,听任自己失去知觉。他被捆在一块
木板上,放上橇车时,没有醒过来。神箭手带领着他的小队出发了。
米沙醒过来了,战争的声音还在脑海中回荡。外面还一片漆黑——出太阳还早
着哩——他第一件想着要做的事是到浴室去,用冷水浇一浇脸并咽下三片阿斯匹林。
接着是就着恭桶一阵干呕,只呕出了一些黄胆水,他起来去照镜子,看看自己这位
苏维埃联盟的英雄出了什么事。当然,他不能——也不愿——就此不干,可是……
可是看看把你弄成什么样子啊,米沙。那曾是明亮透蓝的眼睛如今充血发红,毫无
生气,那红润的脸孔变得跟死人一样灰白。他的皮肤下陷,两颊上灰色的胡子茬把
这副曾经被称为漂亮的脸孔砧污了。他伸出右臂,跟往常一样,伤疤发硬,看起来
象塑料似的。唉。他嗽完口后,就蹒跚着去厨房煮咖啡。
至少还会有点咖啡,那也是他在特需供应商店里买的,还有一个西方制造的煮
咖啡的炊具。他琢磨半天吃点什么,最后还是决定只喝咖啡。他的书桌上总是有面
包可吃的。不到三分钟咖啡就煮好了,不顾会被那热汤烫坏,一口气就喝下一杯,
接着便拿起电话来要车。他让车早点来接他,虽然他没有说今天上午要去澡堂,夜
车场接电话的中士知道是什么原因。
二十分钟后米沙在大楼前出现。他的眼睛已经在流泪,在寒冷的西北风中痛苦
地眯着眼睛,那风想把他吹回门里去。中士打算伸手去扶住上校,但费利托夫稍稍
移动身体,同那要把他推回去的自然之手搏斗,照平常的样子走进汽车,就象他登
上他那辆老T…34型坦克去打仗一样。
“上澡堂,上校同志?”司机坐回前面的位子后问道。
“我给你的酒,你卖了?”
“呢,是的,上校同志。”年轻人回答。
“做得对,这比喝了对健康有益一些。去澡堂。快。”上校装做认真的样子,
“趁我还活着。”
“德国人没能把您杀死,我的上校,我看这几滴美味的俄国伏特加也不行。”
这孩子乐呵呵地说道。
米沙让自己纵情大笑,心情愉快地同意他脑子里的这一闪念。这司机甚至长得
象他的下士罗曼诺夫。
“你愿意有朝一日当一名军官吗?”
“谢谢您,上校同志,可是我希望回大学去读书。我父亲是个化学工程师,我
想继承他的事业。”
“那么,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中士,咱们动身吧。”
十分钟后,汽车停在一座建筑物前。中士让上校下车,把车停在预定的位置,
从那里他能看到大门。他点燃一支烟,翻开一本书。这是一个好差事,比在一个摩
托化步兵连里踩着泥泞东奔西跑要好些。他看看表。老米沙一个钟头左右不会回来。
可怜的老家伙,他想,这么孤零零的。一个英雄怎么弄得这么悲惨。
在里面,例行程序十分固定,米沙连睡着觉都能照办不误。脱完衣服之后,他
取过毛巾、拖鞋和桦树枝,走向蒸汽室。今天来得比往常要早。老顾客们大部分还
没有露面。那更好,他增加了流向耐火砖的水量,坐下来让他那象是被猛烈敲打的
脑袋能够清醒过来。另外三个人分散在这房间里。他认识其中的两个人,但不很熟
识,谁都似乎不想说话。对米沙来说这非常好。只要轻轻动一动,他的上下腭就刺
痛,今天阿斯匹林的药力来得慢。
十五分钟后,他那雪白的身体汗如雨下。他抬头看看那服务员,听到他那让人
喝酒的行话——那时谁也不想喝——加上关于游泳池的情况。这似乎很象干这一行
人所说的话,但它的确切意义是:平安无事,我已做好传送准备。作为回答,米沙
用一种夸张的动作擦去眉毛上的汗(这在老军人也是很普通的)。准备好了。服务
员离去。米沙开始慢慢地数到三百。当他数到二百五十七的时候,一个酒鬼站起来
走了出去。米沙注意到这事,但并不着急。这种事他经历得多了。当他数到三百时,
双膝突然一直,站了起来,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房间。
擦身室的空气要凉得多。他看见那人还没有离去,还在同服务员谈些什么。米
沙站在那里耐心等待,以引起服务员的注意。他注意到米沙了。这年轻人定过来,
上校趋前几步迎上去。米沙在一块松了的瓷砖上绊了一下,差点跌倒了。他那只好
胳膊向前伸出。服务员抓住了他,或者说差不多抓住了。桦树枝失落在地面上。
那年轻人马上把它们拾起,帮助米沙站立起来。过不了几秒钟又给他一块淋浴
用的新毛巾,并送他前往。
“您没事吧,同志?”那人站在房间的另一头问道。
“没事,谢谢您。我这老胳膊老腿,又碰上这老地板。他们应该好好注意一下
这个地板了。”
“他们真该这样。来,咱们一块淋浴吧。”那人说。他大约四十岁,除了双眼
发红,无可描述之处。又一个酒鬼,米沙立刻认出来。
“那么,您经历过战争了?”
“坦克兵。在库尔斯克凸形阵地上,德国的最后一门炮打中了我——但我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