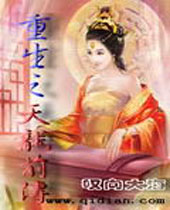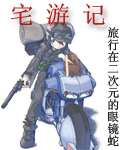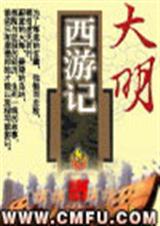神凋天龙游记-第7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女词人聂胜琼有一首词《鹧鸪天…寄李之问》:“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几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写离别相思之情,颇为感人。
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河南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县令蒋兴祖以身殉国,其女被金人掳走。蒋氏在雄州驿馆墙壁上题了一首词《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朝云横渡,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进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女词人心怀凄恻,悲怨情深,充满感伤身世、眷恋故乡的情感。
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也特设童子科,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又称“童子举”。《宋史…选举志一》载:“宋之科目……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童子科年龄限在15岁以下,科考的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要获得神童称号,应试者必须至少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七经”约28万字的儒家经典熟读成诵,其中《毛诗》39000余字。《宋史…选举志二》载:“凡童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
杨亿(974—1021)是北宋初期以早慧知名的诗人,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宋史…杨亿传》载:“(杨亿)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书,又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俄丁外艰,服除,会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宋真宗时期,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馆阁诗人效仿李商隐的诗风,大量写作雕琢用典、铺陈词藻、属对精工、深婉绮丽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宋绶(991—1041)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其外祖父杨徽之是宋初名儒,其母杨氏也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宋史…宋绶传》载:“绶幼聪警,额有奇骨,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绶母亦知书,每躬自训教,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他曾辑录《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1500余首。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经过先后三次兴学后,官学、私学、书院等三类学校的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也更加丰富实用。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待,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因此,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而私学往往集中于蒙学阶段。与前代相比,宋代的蒙学教育更加发达,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十分普遍。宋代蒙学有较完备的蒙学教材体系,包括《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等。其中,《百家姓》、《神童诗》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两种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蒙学读本。蒙学诗歌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神童诗》。《百家姓》在形式上具备了诗歌的特点,可以看作是诗歌类教材。
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时间较长、流传范围很广的一种蒙学识字教材,它将约500个常用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诗,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常用汉字。虽然其内容缺乏文理,但编排合理,句式整齐,隔句押韵,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百家姓》的作者是钱塘(杭州)的一个儒生,前几个姓氏的排列大有讲究,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吴越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百家姓》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三字经》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流传。明代有《皇明百家姓》,清代有《御制百家姓》,但都流传不远。
《十七史蒙求》的作者是北宋时期名扬江淮地区的著名诗人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刻苦读书。十七岁就自立门户,在天长、高邮等地以做私塾先生为生,素有治国安民之志,年仅二十八岁便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王令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在短暂的十余年里就写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由其外孙吴说编为《广陵集》。他的诗多是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志向与人生态度及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他同情百姓苦难,深刻揭露了黑暗政治和民生疾苦,《梦蝗》一诗是其代表作。他的诗受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的影响较深,构思新奇,气势磅礴,意境高远。《暑旱苦热》一诗尤其突出:“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他的诗歌曾受到王安石的极力称赞。
《十七史蒙求》共十六卷,仿照唐朝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韵语,上下两句对偶,生动地介绍了许多历史典故,富有教育意义。如:“宋璟第一,李广无双。燕许手笔,李杜文章。”“石苞当相,卫青封侯。误点作蝇,落笔画牛。一诺季布,片言仲申。衍口雌黄,裒皮阳秋。荀家八龙,贾氏三虎。战胜朝廷,折冲樽俎。汉卧发兵,郝餐击虏。致瓜苏琼,挂黄兴祖。裴楷如玉,卫玠若珠。明牛漏蹄,庾马的颅。”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学者汪洙所作。汪洙,字德温,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县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九岁便善赋诗,有神童之称。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中进士,授明州助教。他曾筑室西山,每月召集诸儒讲学,以教授族闾子弟,乡称崇儒馆。据说,他九岁时曾在一所废弃的学宫旁放鹅,见殿宇破败,心有所感,就写了一首诗:“颜回夜夜观星相,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因而县令召见他,他当即又作一首诗:“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被县令称为神童,受到奖赏。《神童诗》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据学者考证,通行的《神童诗》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对它进行了许多增补。《神童诗》最初共34首,均为五言绝句,其中劝学诗14首,表现科举及第得意心情的诗5首,歌咏时令节气的诗15首。后人又增补了一些描写花草和自然现象的诗篇。通行的《神童诗》有48首诗,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简洁含蓄,浅白清新,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对仗工整,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其中很多诗句已广为流传,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则相天下,穷则善其身。”再如流传久远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神童诗》是优秀的少儿诗歌读物,也是教导少年儿童学作诗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时代局限,这些诗多以高官厚禄引导学童一心读书,曾遭人非议,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很大。
宋初承唐代科举制度,也以诗赋取士,《昭明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
王安石有一篇著名的散文《伤仲永》,记述了当时一个神童方仲永的故事:“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王安石在文中说方仲永五岁就能“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这倒有可能是真实的;但说他“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就能作诗,就太夸张了,恐怕是神话里才能发生的故事,所以王安石只好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实,根据常识来判断,方仲永幼时肯定接受过一些诗歌方面的教育;至于他受教育的途径,或是私塾,或是他人的口授,而后者的可能最大,因而不为人所知。王安石在文中没有说,大概是当地人神化了五岁童就能作诗这件事,以讹传讹,以致真相被湮没了。不过,儿童五岁就能作诗,的确不简单!王安石在文中强调了“受之人”——即受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既刺激了文学作品的生产,又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如曾巩的《苏明允哀词》称三苏的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词在宋代达到顶峰就与此相关。城市中的歌楼酒馆是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歌妓往往以演唱新词新曲为荣,甚至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获得新词,这种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而她们的传唱又使新的词作不胫而走,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柳永的词在当时就赢得了普遍欢迎。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由于传统诗歌体裁成为正统思想观念的载体,词的兴盛也就成为宋代民间诗歌教育的重要形式。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宋代虽难登“大雅之堂”,却获得了极大繁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永的词受到大众欢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
宋代的文学家颇重视研究、总结诗词创作规律,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他们从个人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著作既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这就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王直方《归叟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释惠洪《冷斋夜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吴开《优古堂诗话》、吴可《藏海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等。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历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文艺论著,开创了诗歌理论著作的新体裁,大体上奠定了北宋诗话既有漫笔琐记、逸闻趣事,也有诗歌考证、点评阐发这样的体例。原书只称《诗话》,因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全书共二十八条,各则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逻辑联系,以漫谈随笔形式评论诗歌,记录轶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其篇幅虽小,内容颇丰,有对诗歌规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对佳句的点评赏析,也有掌故轶事介绍和谬说更正等。书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意新语工”等论点,体现出欧阳修追求冲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学思想。欧阳修曾为北宋诗坛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文学创作有深切体会,因而其诗话多有“点睛”之妙。其中对人物典故的叙述则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对诗人的品评大多准确中肯,足资后人借鉴。因此,这本书在后世广为流传。
在北宋时期,胡瑗、程颢、程颐等人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世称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经术,先后在苏州、湖州执教二十余年,创立了“苏湖教法”,宋仁宗时诏令在全国推行。“苏湖教法”采用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和“治事”两科,改变了隋唐以来重辞赋的学风。“经义”科以探索六经义理为主,着重学习研究经学的基本理论;“治事”科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用知识为主,强调学以致用。“苏湖教法”实行分科教学,导致了学风的转变,对宋明理学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