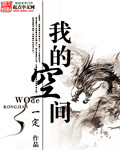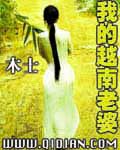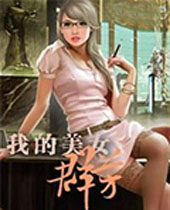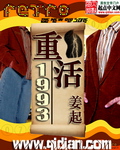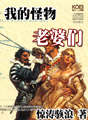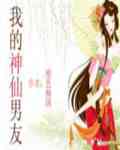我的1976-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邓小平一行离开日本回北京了。采访小组把专机升空远去的镜头传送回去以后,第二天,也登上飞机回国了。当大家刚刚坐定,只见领队脸上绽出了多日来少有的灿烂笑容,只听得他长叹一声:“啊,好啦,都回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多日来毫无水平的言行竟缘于担心采访小组人员的“叛逃”!
回到北京,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出门,心情非常沉重。好一阵子我不想说话只想哭,为我多灾多难的国家,为我多灾多难的民族,也为我自己。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1)
唐禹民
唐禹民,辽宁省朝阳市人,原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摄影干事,转业后到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杂志社任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理事,中国体育摄影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著有《抹不掉的记忆》、《体育摄影理论与实践》、《体育摄影》等。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
1976年7月28日的这一天,唐山市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这一场被世界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的巨祸奇劫,造成了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一座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西方国家一些人士哀叹唐山从地球上“抹掉了”。
地震当天,我就飞往唐山,在飞机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地震消息传来的当天,我作为一名空军摄影干部,很快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清晨得知,震中确定为北京以东130公里的唐山地区。当地空军驻军在震后通讯联络全部中断。
上午9时,我同司令部有关领导及参谋人员一行7人驱车来到通县张家湾机场,登上一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里2”飞机。飞机起飞后,我的摄影工作便开始了。在机组人员的协助下,打开舱门,我系上安全带,半个身子探出舱外,手握相机对准航线经过的村庄城镇,一一拍摄下来,掌握了从北京至唐山沿线的震情。
30多分钟的空中作业,脸被风吹木了,手冻僵了,可我心里挺满足,因为我不仅拍到了照片,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一个村庄房屋破坏得非常严重,几乎全村变成一片废墟,而飞行几分钟后,临近的另一个村庄房屋却完好无损,几乎没有倒塌。再往前一个村庄又遭到毁灭性破坏。面对这种奇特景象,我问自己:地震是否以唐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向四面八方波及,“波峰”上破坏严重,“波底”里破坏较小?我不明白其中缘由,地震科研工作者应该早已掌握了这一自然现象吧?
飞临唐山机场时,天空浓云密布,地面能见度极低,尽管领航员与地面一直用无线电联络,但始终未能听到回答。因此,飞机是在几乎不具备任何飞行数据的情况下着陆的。我们所乘坐的这架飞机,是大地震后第一架降落到唐山机场的飞机。天空正下着雨,飞机滑行时跑道溅起了道道水浪。走下舷梯,一股凉风细雨袭来,我不觉打了一个寒战。指挥塔楼已断裂倾斜,电线杆拉着断线斜躺着,偌大个机场空荡荡的,见不到几个人影,完全陷入了一片瘫痪状态。
领导和机关人员到来,迅速组成了机场指挥部,调来塔台车,扯起帐篷,架起电话线、安装电台,各个环节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
为了全面掌握灾情的第一手材料,我申请了一架被称为“空中轿车”的法国云雀直升机,向东南飞行进入市区。路北区的建筑物倒的倒、塌的塌,留下的只有残墙断壁,线条清晰的完整房屋已很少见;工业区的情景更令人心寒,唐山钢铁厂、422水泥厂以及陶瓷厂已失去了往日生气勃勃的景象;飞临路南区时,能见度明显降低,地面被黄尘及烟雾所笼罩,隐约见到一大片高低不平,黄灰色的碎砖乱石,几乎所有民房倒塌,酷似一片荒无人际的大漠。
市区的几条主要道路挤满了来往的汽车、马车、自行车和行人,从空中看不出有行进的迹象。20多分钟的飞行,我将唐山整个市区尽收镜间。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
在机场南头停机坪上,空军战士们正往直升机上搬运一箱箱食品,准备空投。我随乘808号直升机飞往市区,在飞行中,我发现大部分食品是饼干,还有很多塑料袋装着馒头、烙饼。每个袋里都附着一个信封,我好奇地抽出一个,只见信封上写着:送给唐山人民。落款是:河北邢台一市民。信中写道:亲爱的唐山父老乡亲,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深知遭受地震灾害的痛苦,1966年3月邢台地震,我家破人亡,在极度悲痛之时,敬爱的周总理亲临灾区视察,给了我精神力量。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也包括唐山人民的支援,使我们度过了艰难时刻,我们从废墟上爬起来,历经磨难,重建了家园。我连夜烙了几张薄饼送去,以解燃眉之急……看着这火一样炙热的书信,谁人能不动情?
直升机来到预投空域,位置大概在火车站以东,这是个人口稠密的重灾区。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地面看得一清二楚,市民们聚集在废墟上,仰望天空,双手不停地摆动着。机务人员把舱门打开,系好安全带,将一箱箱一袋袋食品投下去。我不停地按动着快门。
由于地面道路、桥梁的严重损坏,救援部队和物资受阻,机场便成了抗震救灾的生命线。指战员们顶着烈日,穿着背心裤衩,用目测指挥着飞机的起降,一天最多时起降达350多架次,共指挥了数千架次飞机的安全起落。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空运到唐山机场,机场的停机坪上堆积如山的医药、帐篷、油毡、塑料布、食品等救灾物资,又从这里用汽车运送到各区县,有些应急食品进行了空投。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2)
7月29日,由于市区车辆无法通行,我只得从机场步行前往市区。
大地震后的唐山惨不忍睹。原来宽阔的路面已使行人难以插足,车辆无法通行。九死一生活下来的人们,在残垣瓦砾之上用各种残余物搭起了躲避风雨的窝棚,人们后来叫它为“防震棚”。防震棚挨近路边,停放着一些用被褥包裹着的尸体。
目睹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悲哀、苍凉的情景,完全可以致人精神分裂。我参加过正规战争,战争的残酷令人怵目惊心;然而,一座百万人的城市,顷刻间遭到毁灭,夷为墟土,变成埋葬24万生灵的坟墓,唐山的灾难要超过战争的残酷千倍万倍……
人们在废墟上架起了锅灶,从路边排水沟里掏些水,捡拾一些能填口的食物,煮一煮充饥。空中飘荡着缕缕炊烟,宛若死难者的幽魂。
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一位年轻妇女只有一块布裹在胸前和腰间。每个行人都走得那么匆忙,面无表情,每个人心中都装有一部悲惨的家史。令人震惊的是,我没有听到一声哭泣,也没看到一滴眼泪。
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惩罚的枪声不断响起
我在站前街拍照时,周围一些人在斜楞着眼睛盯着我并议论说:“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思照相!”“这个人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再照把照相机给他砸了!”
由于天气炎热,我没有穿军装,受灾群众不了解我的身份,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在一般人眼里,照相这玩意儿,只能在节假日和喜庆的时候才派上用场,而绝不会在大灾大难、家毁人亡的时刻拿出它来。我要想坚持拍下去,只能改变“明目张胆”的拍摄方法,采取隐蔽措施,趁人不备,快速抢拍,有时是偷偷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拍完后即刻把相机装进一个随身带的黑塑料包里。
但是这个塑料包还是招来不少麻烦,很多伤者见我背着包,都以为我是大夫,不时向我伸出手来哀求:“好大夫,给点止疼药吧!”他们求药,不是因头疼脑热,而是高位截瘫、腰椎损伤、骨盆断裂等重伤。
大伏天,酷暑热浪无情地袭击着“死亡之城”。街区道路的严重破坏和阻塞,使救援车辆开到市区边沿却开不进城里,因而使救灾工作严重受阻,灾民得不到粮食和饮水,重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停在路旁的尸体也无法运走。头两天见到的尸体,僵直、呈蜡黄色,后来变得臃肿,呈酱紫色,从被子里往外流黑水,凡是停尸的地方到处流淌着一滩滩的血水,散发着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尸体上和血水中爬满了一群群绿头苍蝇,行人经过时,便轰起一片“嗡嗡”作响的苍蝇。废墟中尚有大批尸体没有挖出来,同样散发着尸臭味,使得唐山市区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人们不得不将口罩、湿毛巾捂在嘴上。在废墟旁,铁路边,在市区通往机场3。5公里的道路两侧以及机场跑道北端,堆起了无数座坟墓,多数坟堆前都插着木牌,上面写着被埋葬者的姓名和年龄。
站前街马路上,架有高音大喇叭的广播车缓缓穿过人群,女播音员提高调门朗诵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反复播送着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告,大意是,“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全体市民要保持镇静,提高警惕,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擅自进入工厂、矿山、银行、粮店、仓库、商店等地方,严禁抢劫,违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人们刚刚挣脱了死亡的羁绊,伤口尚在淌血之时,一股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这股罪恶之风是任何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令人极为痛心。
地震当初,一些人把本不属于自己的衣物、食品拿来遮体充饥,似乎还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人贪婪地把肮脏的手伸向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在路北区,我见到一个防震棚,全部材料用整匹黑白条的长毛绒覆盖着;有些人扛着整箱的香皂、牙膏、五金工具等,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我在经过靠近铁路的一个百货商店时,见到门脸儿的玻璃窗都已支离破碎,里面陈列的各色商品已荡然无存。
郊区的一些人,他们开着拖拉机、赶着小驴车,更多的是骑着自行车,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市区涌来。他们在废墟上掘地三尺,无情地掠夺无辜者的财物,遇难者的尸体也逃不过这些人的搜刮。
在这抵御天灾的非常时期,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令人悲哀,因为它严重地剥蚀和残害着善良人们的心灵。当公安人员和民兵警觉地发现抢掠者的犯罪行径时,他们从瓦砾中爬起来履行职责,废墟上空响起了枪声。枪声从不同方向传来,在告诫那些梦想发“国难财”的抢劫者。
唐山机场成了荒漠中的绿洲
7月28日下午6点40分,我正在帐篷里整理照相器材,突然,地面猛烈颠簸,发出隆隆响声,帐篷呼啦呼啦地摇晃起来。我已无力控制自己的行动,死死把相机搂在怀里。我知道这是一次较大的余震,不知几十万灾民是怎样挨过这暴风雨之夜的,又想到北京的妻子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不知安身在什么地方。唉,现在顾不了这些了!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3)
唐山机场饮用水告急,由于地震引起地下水下降,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是糨糊糊的黄泥汤,只好把泥汤灌到水壶里,沉淀后再喝。机场北头有从全国各地空运来的堆积如山的各类食品,谁也不去动,依然嚼着分配给自己的难以下咽的那份压缩饼干。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那些食品的分量。
地震发生后的头三天,是唐山市灾后最为严重的时刻。饥渴、伤病无情地袭击着人们。
“去飞机场,找解放军。”人们在危难时刻总是首先想到人民子弟兵。
灾民们把唐山机场视为荒漠中的绿洲。人们扶老携幼,用平板车拉着伤员,用自行车驮着老人和儿童,更多的人则是挑担挎篮,步履艰难地,潮水般地涌向绿洲——唐山机场。
机场的营房及四周草坪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人们为横躺竖卧的受伤者架起塑料棚,以避风雨和日晒。战士们架起了几口大锅不分昼夜地熬着米粥,饥渴的人们排着长队在粥锅旁耐心地等待着。机场唯一的水源是一池发绿了的游泳池的水。果园里,七月的青苹果如核桃大小,已被“扫荡”一空。几辆开往市区的卡车,从机场还未开出去,就被饥饿的人群拦住,爬上车强行搬运着食品,押车的战士上前劝阻,没人理睬,只顾往车下扔着一包包的饼干,战士们也无可奈何。
从全国各地调集的一万多名医务人员组成的200多个医疗队,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展开抢救工作。在机场营房的周围逐渐出现医疗队架起的顶顶帐篷,帐篷旁插着白色的红十字旗,标牌上写着:解放军总院、空军总院、上海六院……伤者在亲人的护送下,在医疗队的帐篷外边排起了长队,而且越排越长。重伤者不时发出刺心的惨叫声……
手术帐篷里,医务人员如同处在战争状态下,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做着医院里都少见的大手术。照明用的是汽灯,消毒用的是游泳池里的水……尽管广大医务人员怀有对灾区人民极端负责、极端热忱的革命精神,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仍不能挽救众多人的生命。几十具尸体停放在不远的草坪上,作为医生,他们深感痛心和惋惜。
手术帐篷外的土坑里,在血染的药棉和纱布中,堆积着截肢下来的、鲜血淋淋的胳膊、大腿、手掌……几天来我见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尸体,我没感到恐惧,然而,看到这些从活人身上截下来的残肢烂肉,顿时觉得惨不忍睹,甚至不忍心把镜头对向那里,希望它从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停放尸体的草坪上,大部分死者被装进了深灰色的装尸塑料袋里,一少部分则用棉被裹着。
遭受重创的唐山机场,此时已难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唐山由此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经国务院批准,唐山自7月30日开始了一场向全国范围内转移伤员的壮举。此时大批飞机、列车、汽车从各地陆续调往灾区。作为空中大通道的唐山机场,马达轰鸣,各种飞机呼啸着像穿梭一般,时起时落,出现了空前的繁忙景象。飞来的飞机卸下满载的救灾物资,飞走的飞机满载着负伤的兄弟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