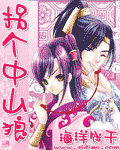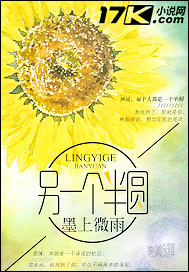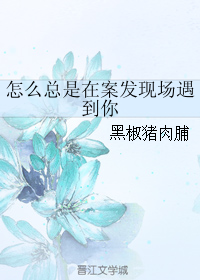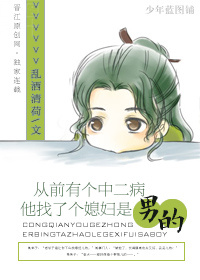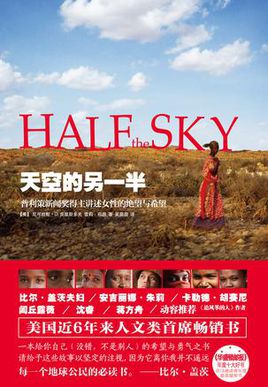发现另一个中国-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人也重朋友、尚武力,不顾当时的法律与道德舆论,一意孤行,有些像游侠;然而他们只是奴役穷人,欺凌弱势人群。他们不仅不是游侠,而且游侠们深以为耻。因为他们所持的精神正与游侠相反,我们可以名之为“反游侠”。后世一些文学作品中以杀人为勇武,漠视生命,滥杀无辜,并把这种“勇武”视为游侠,这其实都是“反游侠”的。
一些年轻人羡慕游侠,但由于达不到侠的人格,只是作表面上的模仿,以为得寻求之三昧,沾沾自喜,实际上是“假游侠”。这种情况在魏晋以来到唐代的诗歌创作中有充分的反映。
诗歌中较早表现“假游侠”的作品,当是曹植的《白马篇》。诗中写道: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之际,不顾妻子父母,为国立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首诗的确是好诗,但所写的已经不是司马迁所说的“不轨由正义”、“赴士之ND076困”、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游侠了;而是报国之士(实际上报的是曹植父兄所建立的王朝),但却顶着“游侠”之名,我们只能说他是“假游侠”。以后这类作品成为一个套路,用“游侠”这个激动人心的名称来表彰那些以身许国、建立功勋的少年志士,如鲍照的《拟古诗》(幽并重骑射)、陈子昂的《感遇诗》(朔风吹海树)、崔颢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少年负胆气)、元稹的《侠客行》(侠客不怕死)、陆游的《剑客行》(世无知剑人)等。这类作品把本来是令统治者十分头疼的游侠,变成了统治者能够接受、甚至是十分欢迎的人物了,把反主流社会的社会现象纳入了主流社会。随着时代不同和当时社会状况的差别,这类作品另有别的社会意义。
说游侠(4)
大量少年人学游侠,主要还是学游侠们的外在,如服装打扮、行为作派,等等。《史记·游侠列传》中并没有写到游侠有什么特殊的打扮,司马迁反而渲染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而后世写到游侠,大多爱写他们的特殊装束与打扮。曹植《白马篇》就写到少年人的白马良弓,身段矫捷。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行》还写到游侠少年装饰的华丽: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
王僧孺的《古意》也写道:
青丝控燕马,紫艾饰吴刀。朝风吹锦带,落日映珠袍。
这些贵族少年平常软玉温香,倚红偎翠,整日在温柔乡中,日久也会生厌,游侠生活是他们寻求的新刺激。但这个“游侠生活”绝不是“不爱其躯,赴士之ND076困”、“存亡死生”。他们不仅没有这种能力,根本也不会产生这种意识。他们的“游侠”不过是走马长林、逐兔丰草而已,有的甚至只是走狗斗鸡罢了,总之不读书,再追逐一种不同于室内娱乐的娱乐,就有了三分侠气。这些“假游侠”们不仅没有一点儿牺牲精神,更不会有丝毫的生死相搏的勇气,其反叛性、危险性都不存在了,游侠就仅存有娱乐价值了。这种纯粹供人娱乐的游侠(像现今的武侠小说)谁都能接受它了,连太太小姐所居住的内室(也就是贵族少年的温柔乡里)也可以用它来装饰了。庾信在《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中,就有一首诗歌咏屏风上画的“游侠”少年。诗中写道:
侠客重连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
这座屏风连环画中的“游侠”,与《史记》中所写的郭解等人能差出十万八千里吧!他们也是呼朋引类,也是走马闹市,但他们是去“惊花”、“醉酒”的,所以才会害怕归鞍日晚,要与人争路呢!
有的诗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假游侠”的可笑,还一本正经地描写他们。如王维的《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长安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当然这只是少年游侠的一个剪影,一首小诗也不可能写到主人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从这首诗的情调的欢快、少年游侠格调轻佻(能喝酒就是了不得的豪气了),都可以断定这位少年不过是借游侠生活玩玩的“假游侠”。真正的游侠的生活是十分沉重的。与王维相反,杜甫就对这类少年人有较深的认识。他的一首《少年行》中这样写道: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古游侠有先秦士风,为人都是“廉洁退让”的,十分低调的,哪像这位少年如此张扬无礼。胡夏客说:“此贵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荡者。既非才流,又非侠士,徒供少陵诗料,留千古一噱耳。”这种“假游侠”是很可笑的。
唐代诗人韦应物少年时正逢盛唐,作为贵族,他成为玄宗皇帝的“三卫近侍”,这个编制是贵族无赖少年的渊薮。年轻的韦应物也与这些无赖少年一起“游侠”,一起寻欢作乐——赌钱、追女人,违法乱纪,而且以其特殊身份(所谓“职位不高地位高”也)傲视官府,不受惩罚。晚年,他在《逢杨开府》一诗中对这段生活作了一些反思。其中写道: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座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
本来韦应物也可以把他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写得非常浪漫(一掷千金的豪赌,入户抢劫美女),十分风光(风雪夜中作为“武皇帝”侍卫的光荣;长杨围猎时的豪气也是能体现“盛唐精神”的)。可是作者没有这样写,而是把自己描写成一群恶少,暴露了自己作奸犯科、无法无天,成为乡里一霸的生活实质,并且写到自己的愚拙,作了真诚的忏悔。传统不习惯忏悔,所以弄得一些评论家认为本诗所写“不类苏州(韦应物)平生”。实际上这正体现了韦应物作品的价值。韦以自身生活为例,揭示了“假游侠”不仅有可笑的一面,还有可恶的一面。
说江湖(1)
说江湖
说江湖(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
上篇
20世纪8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进入大陆以来,“江湖”便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甚至成为使用极为频繁的一个词汇。本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凭借着金庸对它的理想化、文人士大夫化,又借助荧屏的张扬,得以畅行于老式和新式的学子仕女之间。一时间,仿佛是处处江湖、事事江湖,但什么是“江湖”?它的确切的内涵是什么?却是不十分清晰的。
一、三个“江湖”
1江湖本义
“江湖”作为一个词,在先秦就出现了,最初的本义确实是指江河湖海。庄子在谈到“涸辙之鲋”时说,与其在涸辙中相濡以沫,还不如相忘于江湖,这个“江湖”就用的是本义。九州之内,江河纵横,湖泊遍地,因之,人们也用“江湖”来泛指域内四方。
2文人士大夫的江湖
后来这个词发生了变化,由于“江湖”的广阔浩淼、荒僻鄙野,与热闹繁剧、名利所在的朝市恰成对立,于是,“江湖”变成了文人士大夫的隐遁之地。它没有了朝市的喧嚣嘈杂和争名夺利,成为厌倦了鸡争鹅斗的士人们向往的静谧休憩的好场所。此时的“江湖”可以与士人归隐、隐居划等号了。王昌龄送朋友回乡的诗中写道:“故人念江湖,富贵如埃尘。”必须看透了富贵名利,方能与之言江湖。到了江湖,与之相伴的只是“独立浦边鹤,白云长相亲”,耐不住寂寞的人们是早晚要和“江湖”说“拜拜”的。南朝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就是讽刺这类人的。
因为“江湖”这个词与文人士大夫的出处密切相关,所以人们谈到江湖就十分明确地把它与朝市分别了开来。唐玄宗写过一首送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就是他向玄宗推荐了李白)还天台的诗:“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这正像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中所说,“比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当然江湖与朝廷虽是两条道,但静谧的江湖中也不能缺少了吃的、喝的,否则文士们是高卧不下去的。而有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们,即使身在江湖也要心忧国家,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
与朝廷、城阙“异迹”“殊伦”的还有一种“江湖”,它不是静谧安详的,而是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第二十八回中,十字坡的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请武松吃饭,三个人“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便安慰他们,说这只是江湖上好汉说话,不会伤好人的。衙门黑暗,一个公差听过、见过、干过多少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事情,这从《水浒传》所写的林冲发配就可见一二;可是连这些董超薛霸们听了武松讲江湖事都感到震惊、恐怖,这种江湖的状况可以想见。
①江湖是游民们觅食求生的场所
这个江湖不是文人士大夫隐居的地方,而是脱离了宗法网络、在宗法社会中断绝生存之路的游民们闯荡、奔走、觅求衣食的场所。游民一无所有,空手练空拳,全凭个人心智、个人力量和勇气胆量以求生存和发展。这里没有了士大夫江湖的与世无争的气度,不仅要“争”,而且没有主流社会中所应遵守的规则。饥饿能够把人驱赶到最原始的状态中去,游民们为了生存,有时仅仅为了一餐,便能剥去几千年形成的文明的积淀,这些绝不是衣食不愁的人们所能想像的。因此这个“江湖”不仅不是文人士大夫漱流泉、枕白云放松高卧的地方,也不是被金庸武侠小说所美化了的、文人化了的“江湖”(这个“江湖”除了莫名其妙的打打杀杀之外,其不食人间烟火的风格甚至超过文人士大夫的“江湖”),它是游民争斗、生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游民的第一需要是生存,这是“江湖”存在的依据,与这个“江湖”相邻的是“沟壑”。在江湖上挣扎的人们,最后大多填于沟壑。
说江湖(2)
②江湖是个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
在江湖上挣扎的游民不能遵守主流社会的规范,必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打击,特别当主流社会是极权专制社会时,江湖是非法的,是被镇压的对象。如果说主流社会是公开的、显性的话,江湖则处于地下、隐性的位置。江湖一般来说不是个有形的组织(当然其中也有有形的,如被游民们所占据的各个山头——桃花山、梁山和秘密帮会等),它的存在更多地是体现为一个“场”,无形,但人们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制约着游民或与游民有关的人们的生活,它也具有江湖人所公认的准则,并且依此形成了一个评价体系。它能给江湖人带来一些便利,也会制造一些麻烦。人们从这些存在中能够感受到“江湖”的客观存在。统治者有办法镇压、剿灭那些有形的组织,可是对于无形的“江湖”,能够不屑一顾甚至能鄙视它,但是却不能把它消灭,它像“磁场”、“电场”一样,是抓不到摸不着的,统治者对它无可奈何。因为只要有游民就有江湖,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
③江湖确实存在
“江湖”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可以从文化史上第一次透露了“江湖”存在的《水浒传》的许多描写中看出这一点。例如林冲发配到了沧州,在路边的一个酒店里,店主人向他介绍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作小旋风。”“小旋风”是柴进在江湖上的绰号,只能用于江湖。如果他遇到江湖上的朋友,只要一亮“小旋风”这个名号,大多会有个照应,可能会给他带来许多方便;如果在主流社会中,柴进与人交往,比如说他去拜客,其拜帖上决不会写上“小旋风”三个字,这个绰号仅属于江湖。
在主流社会的人们看来,有了绰号(特别是江湖上的绰号),绝非善类。清风寨的知寨刘高抓住宋江以后,因宋江不肯吐露真名,只承认叫张三,刘为了把宋江坐实为土匪,上报其名便写的是“郓城虎张三”。
江湖上互相联系有秘密语,或者称之为黑话。《水浒传》中就有“剪拂”(下拜)、“塔墩”(跌坐在地)等,不过当时江湖秘密语还处在初期阶段,到了清代,江湖的秘密语就十分发达了。江湖上不同的行当和不同的组织都有独特的秘密语,彼此不能相通,把圈子划得很小;其词汇也十分丰富了,如天地会(洪门)的秘密语中有独立意义的词汇就在千个以上,掌握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江湖上的黑话也仅仅是在江湖上用,不会进入大雅之堂的(现在有些电视节目主持人满口黑话。一些洋人学中国话,把黑话当作中国民间语言的精华去学习,是很可悲的;有的洋人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学了一口流氓话回去,他还以此自炫,也是很可笑的),它的使用范围是十分明确的。
江湖还有属于自己的舆论,有属于自己的道德评价标准。例如“智取生辰纲”故事中,吴用劝诱“三阮”参与,当“三阮”感慨梁山好汉占住了水面,使他们很难捕到大鱼时,吴用激他们上梁山去捉“这伙贼”,立功领赏。阮小七说如果捉住了他们到官府那里领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这里不仅反映了江湖游民与官府天然对立的倾向,也可见江湖人的行为受到江湖舆论的制约,这种道德舆论的评价是与主流社会截然相反的。
江湖上还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有了事情很快就会在江湖人中传扬开来,例如林冲上梁山后受到寨主王伦的排挤,江湖好汉们马上就知道了,好像有专门报导江湖新闻的报纸和记者似的。又如,一些非游民想在江湖上投些资,救助一些游民,他一这样做,不仅受惠者感激,而且其他江湖人也很快就知道了,使得这些人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儿”。而且江湖上还能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领袖,有了事江湖人就会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