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对向《纽约时报》提供信息缺乏安全感而无意为之,那么报方应该扪心自问。《纽约时报》的确曾与维基解密合作,刊登了大量文件,但时隔不久,前主编比尔·凯勒费尽心思疏远了报纸与其合作人之间的关系:与奥巴马政府对维基解密的怒不可遏形成鲜明对比,他领导下的《纽约时报》以其“负责任”的报道得到政府的欣赏。
凯勒也曾在其他场合中表现出其对该报与华盛顿的关系洋洋得意。在2010年他做客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中,谈及了涉及维基解密泄露美国外交电报的相关话题,凯勒解释称《纽约时报》在发表什么内容以及是否可以发表的问题上,都是听从美国政府的指示而行事。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将信将疑地问道:“你的意思是,你会事先前往政府进行请示:‘这个该不该发表,还有那个该怎么处理’,然后你会得到批复,是这样吗?”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前英国外交官卡恩·罗斯(Carne Ross),他称凯勒的说法令他觉得爆料人根本不该将这类电报交给《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会将这些内容向美国政府汇报,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媒体与华盛顿之间的如此精诚合作绝非偶然。这些完全是例行做法,例如在与国外敌对势力意见相左时,记者需要了解美国官方立场,并会依据政府所确定的最能体现“美国利益”的方式制定编辑意见。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律师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曾大肆鼓吹他所谓的“未受到充分赏识的现象:美国媒体的爱国主义行为”,指的就是美国国内媒体对政府工作所表现出的忠心耿耿。他援引布什政府中情局和国安局局长迈克尔·海登的说法,他认为美国媒体表现出了“一种非常配合的工作态度”,接着补充道,而若要国外媒体也做到这一点“则相当困难”。
政府对主流媒体的认同通过不同方式得以加强,社会经济学上的因素便是其一。美国许多著名记者现在的身家都超过了百万美元。他们与政要和金融界的精英都是邻里,显然要为之效力。他们共同出席盛大集会,有着相同的朋友圈和同事圈,子女也都就读于同一所精英私立学校。这就是媒体记者可以与政府官员间无缝对接交换身份的原因之一。旋转门可以将媒体人物送上华盛顿高层职位的通道,而政府官员也常常会在离任后,拿到一份就职于媒体且待遇颇丰的合同。《时代》杂志的记者杰伊·卡尼(Jay Carney)和总编理查德·斯坦格尔(Richard Stengel)现在就职于政府,而奥巴马的高级顾问大卫·艾索洛(David Axelrod)和白宫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Robert Gibbs)现在成为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员。这些都属于跨界发展,但绝非是简单的跳槽:他们的职业转换如此水到渠成,全是因为这干人等还在为同样的利益效力。
美国的主流媒体记者绝非是局外势力,而是与国家的主流政治力量浑然一体。从文化、情感乃至社会经济学角度,二者完全整齐划一。腰缠万贯的内幕新闻名记完全不愿推翻现状,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丰厚收益。与所有阿谀逢迎之徒一样,他们希望捍卫当前体系,以求获得相应特权,若有人胆敢挑战对这一体系,势必会遭到这些人的侮辱中伤。
这与完全满足政治官员的需求只有一步之遥。因此新闻透明不会被看好,持反对意见的媒体记者被视作眼中钉,甚至可能是犯罪分子,必须允许政界领导在暗中行使权力。
2013年9月,普利策奖获得者英国《独立报》资深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强有力地揭示了这些观点,他曝光了美军在越战期间的美莱村(My Lai)屠杀事件和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囚丑闻。在一次《卫报》的采访中,赫什斥责道:“美国媒体胆小怯懦,未能对白宫提出有效质疑,不能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他认为《纽约时报》在“取悦奥巴马”方面耗时过多。他表示政府机构在有计划地制造谎言,“可没有一家美国主流媒体、电视网络或报业巨头”对此提出质疑。
赫什为“解决新闻界问题”下的猛药是“关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广播公司的新闻部门,取消90%的出版编辑岗位,回归记者最根本的职责”,即重拾作为局外人的身份。赫什认为:“对超乎你的控制能力之外的编辑应予以提拔,而现状是,这些‘惹是生非之徒’晋升无望。”相反,“那些胆小如鼠的编辑”和记者正在毁掉这一行当,因为他们脑海中最根深蒂固的想法是抱着自己的饭碗,而不敢成为局外人。
一旦记者被贴上激进分子的标签,一旦他们的工作受到从事犯罪行为的指控,他们就会被扫地出局,不再得到记者身份的保护,很容易就会遭到刑事惩罚,这在国安局监听事发之后,在我身上很快就得以印证。
当我从香港返回里约热内卢的家中刚进门不久,戴维就告知我他的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他怀疑此次失窃与我动身前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有关,他提醒我称我在Skype上曾与他通话,谈到我有意通过电子形式发送的大量加密文件。文件到达后,我曾说过他应该把这放在安全的地方。斯诺登曾表示,必须要有个我完全信任的人保存一套文件的完整备份,以防我的文件丢失、受损或失窃,这一点至关重要。
斯诺登当初这样说道:“我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露面,你和劳拉的工作关系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也很难讲,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个人保存一份备份文件,让你随时可以提取,以备不时之需。”
显然这个可靠的人物非戴维莫属,但我一直都未来得及将文件发送出去,只有当我来到香港才有空付诸实际。
“你告诉我此事不过48小时,我的笔记本电脑就从家中失窃了。”我不愿相信电脑被盗会与我们的Skype交谈相关。我告诉戴维,我决意不让我们过于神经质,把一切生活中无法解释的事件都安在中情局身上。也许笔记本电脑是被某个私闯民宅的家伙拿走了,或者这不过是一起毫不相干的抢劫案。
戴维却逐一反驳了我的理论:他从未将笔记本电脑带出家门;他在家里上上下下翻了个遍,都找不到电脑的踪影;除了电脑之外,房间里什么都没动,也没有少什么东西。他觉得我有些毫无理性,居然会拒绝接受看似如此显而易见的唯一解释。
到此为止,许多记者都已发现,国安局对斯诺登掌握了何许情报或是给了我哪些情报基本上一无所知,只知道文件的数量是多少,而不是具体有哪些文件。美国政府(乃至其他国家政府)迫切希望了解我手里究竟有哪些情报,而这也合情合理。如果戴维的电脑里存有所有这些信息,那么他们何不索性据为己有?
到这一刻我也意识到在国安局的监控面前,与戴维通过Skype进行通话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方式都绝不安全。政府有能力窃听到我计划给戴维发送哪些文件,因而会有强烈的动机将其笔记本电脑据为己有。
我从《卫报》的媒体律师大卫·舒尔茨(David Schultz)那里获悉,戴维关于失窃的解释的确合理。通过与美国情报界的接触使他了解到,中情局在里约热内卢的活动较世界各地更为活跃,而且里约热内卢的情报站长“手段之狠远近闻名”。基于此,舒尔茨告诉我,“你应该可以相当肯定地假设,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和所在之处都在受到密切地监视。”
我承认自己的通信能力目前已受到极大限制。我尽量不使用电话,最多不过是说些含糊其辞或是无足轻重的内容。我收发邮件都是通过复杂烦琐的加密系统完成。我和劳拉、斯诺登等知情人之间的讨论都是在加密的在线聊天程序中进行。我配合《卫报》编辑及其他记者的工作也都是要他们亲自来到里约热内卢,与我面对面进行沟通。在我们的家中或是车里,我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笔记本电脑的失窃让我们意识到,这些最为私密的空间可能都会受到监控。
如果我需要更多证据证明我所工作的环境正受到更多威胁,那么从如下情况便可见一斑:美国《大西洋月刊》的特约编辑史蒂夫·克莱蒙斯(Steve Clemons)与我往来甚密,他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华盛顿特区政策分析员,他偶然间听到了一席谈话,并特别告知我。
6月8日,克莱蒙斯在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美联航的休息厅,据他讲,当时他听到了四名美国情报官员大声谈论道,国安局监控事件的相关泄密人和记者应该“消失”。他称自己还在手机上录下了部分谈话内容。克莱蒙斯认为这番谈话看似“虚张声势”,但无论如何还是决定将谈话内容予以公布。
虽然克莱蒙斯相当可靠,但我并未将此事太过当真。可是这类机构人士在公开的闲谈中提及让斯诺登以及与他打交道的记者一并“消失”,的确值得警惕。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关于国安局监控的报道涉嫌刑事犯罪的说法从抽象概念成为了现实,而这一激变是由英国政府促成的。
我从美国版《卫报》的英籍主编简宁·吉布森那里通过加密聊天首先了解到,《卫报》的伦敦办事处在7月中旬发生了件异乎寻常的事情。按照她的话说,过去几周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与《卫报》 之间的谈话腔调出现了“彻底改变”。这家英国的情报机构原本是就此事的报道进行“非常礼貌的沟通”,现在却变成了火药味十足的发号施令,进而是赤裸裸的威胁。
接下来,或多或少有些突然的是,吉布森告诉我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宣布不再允许《卫报》继续刊登涉及绝密文件的报道。他们要求《卫报》伦敦办事处上交从斯诺登那里得到的所有文件。如果《卫报》拒绝,就会收到法庭指令,禁止其再从事任何报道。
这一威胁绝非空穴来风。在英国新闻自由并无宪法保证。英国法院会对政府“事先限制”的要求完全顺从,提前禁止媒体对某些所谓危及国家安全的内容进行报道。
的确,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发现并报道了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存在的记者邓肯·坎贝尔(Duncan Campbell)遭到逮捕并被起诉。在英国,法院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封《卫报》,没收其所有材料和设备。简宁表示:“如果上面要求他们如此行事,法官们不会说半个不字,对此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卫报》掌握的文件是斯诺登带往香港的全部文件的一部分,他强烈认为报告中涉及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内容应该由英国媒体予以发表,在他在香港逗留的最后几天里,他将这些相关文件的拷贝交给了埃文·麦卡斯基尔。
在我们的通话中,简宁告诉我,她和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以及其他员工都已经在上一个周末暂避到伦敦以外的一处僻静所在。他们突然间听到风声,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官员正前往卫报在伦敦的新闻编辑部,希望搜出存有机密文件的硬盘。据拉斯布里杰后来回忆称,官员们表示:“你们应该已经看够了吧,是时候让我们把东西带回去了。”听到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消息时,大家在乡间不过才待了两个半小时,简宁说道,“我们不得已,只能一路开车回伦敦去捍卫办公大楼,气氛十分紧张。”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勒令《卫报》上交所有文件拷贝。如果报社照办,政府就会得知斯诺登转交了哪些内容,而且他的法律地位会愈发危险。相反,《卫报》同意销毁所有相关硬盘,并且销毁全过程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监督下完成,以确保满足其要求。所发生的一切按照简宁的话来讲就是“搁置、外交斡旋、偷梁换柱的精心上演,最后通力合作地‘予以示范性销毁’。”
“予以示范性销毁”是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新近发明的词语,用于描述所发生的一切。这些政府官员在《卫报》员工的陪同下,上至总编下至新闻编辑部的基层员工一同观看了他们销毁硬盘的全过程,甚至要求将硬盘碎片进一步粉碎,以确保“在这些杂乱的金属碎块中不会再含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可以再落入中国情报机构之手”。按照主编拉斯布里杰这样回顾当时的场景,他还想起有位《卫报》员工在“打扫苹果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的残余碎片时”,一位安全专家开的一句玩笑:“我们可以再叫来一架黑色直升机收拾现场。”
政府派特工前往报社强行销毁电脑,这一场景着实令人震惊,西方人一直以为这类事情只有在伊朗和俄罗斯这样的地方才会发生。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一家备受尊敬的报社竟会如此顺从、自愿服从于这样的指令。
如果政府以查封报社相威胁,那么为何还要虚张声势,而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查封?当斯诺登听到这样的威胁后,他表示说:“这种情况下唯一正确的答案就是:请继续,查封我们好了!”造成这种“自愿服从”的假象,不过是政府为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不至于出丑而使的伎俩,目的仍然是让记者不得报道最关乎于公众利益的重要事实。
更有甚者,将知情人士冒着丧失自由甚至生命带出的材料予以销毁,这完全与新闻的目的背道而驰。
除了将这种专横的做法大白于天下之外,政府闯入新闻编辑部,逼迫报社将所掌握的情报资料予以销毁,这本身就极具新闻价值,可是《卫报》显然是准备保持沉默,这更强有力地说明,英国新闻自由的现状是多么的岌岌可危。
吉布森向我保证无论如何《卫报》在纽约分部还存有整套文件拷贝。接着她又告诉了我一件更令人震惊的消息:《纽约时报》手中也有全套的拷贝,这是《卫报》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交给《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吉尔·爱博松的,以便确保万一英国法院迫使《卫报》销毁拷贝,报社还有办法看到相关文件。
这也实属不妙。《卫报》不仅未经同意就私下里销毁了自己手中的文件拷贝,而且事前没有找斯诺登或我进行商议,甚至都没有告知我们,就将这些拷贝交给了《纽约时报》,而斯诺登之所以一开始就将其排除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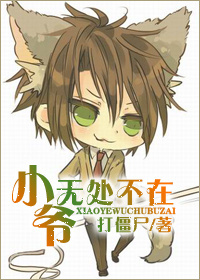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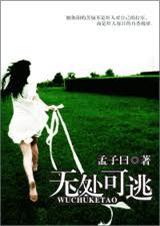

![(综同人)[综英美]无处不在的晋江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9/1906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