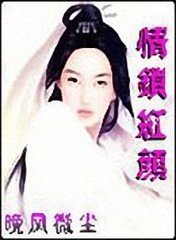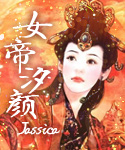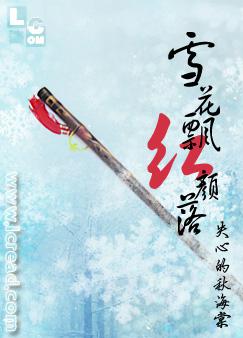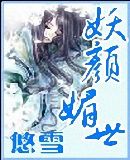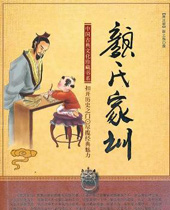凋落的红颜-第6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宗得知竟有这样的事,非常吃惊,连忙召回颁册的使者。
然而以房玄龄为首的众臣(老房这回怎么忘了自家的醋坛子了)眼看太宗怅然若失的模样,都认为魏征是搅了皇帝的美事,闲事管得太宽。纷纷提出:颁诏册嫔乃是大事,怎能因为魏征的几句话就中途废止?另一边厢,陆家也赶紧表明态度,说自家与郑氏绝无婚约,皇帝想咋地都天公地道。
有了陆家的声明,群臣就更起劲了,纷纷要求太宗重新礼聘郑氏入宫。太宗也不禁心旌动摇,将陆家的奏章拿给魏征看。魏征笑道:“陆家只不过是害怕重蹈太上皇情敌辛处俭的前车之鉴而已。”——原来,李渊有一名妃嫔,曾经是太子舍人辛处俭的妻子,李渊夺其妻后又因爱生恨,越看辛处俭越别扭,最后干脆将他降级外调做了县令。倒霉的辛处俭一生都活得胆战心惊,唯恐丢了性命。——一语道破天机,李世民立即表示自己绝不做这样的事情,并赶紧发下诏书自责,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郑氏虽然没能入宫,但我们可以想象,长孙氏为夫纳妾的事情不会就此终止。不过此后应该是一切顺利,所以史书也就忽略不提了。
现在的人实在很难想象二十七岁的长孙氏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主动为丈夫选取新欢的。虽然那是在一千四百年前的时代,但女人对爱情的思绪却都是一致的。何况她身上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隋文帝的独孤伽罗皇后就是她的同族,更是她的表亲。
前面已经说过,长孙皇后早年曾受到异母兄长的虐待,他们的行径极大地伤害了她。然而当她成为皇后,她并未丝毫报复过他们,长孙安业一直稳稳地当到了监门将军。只是他始终心怀鬼胎,不敢完全相信妹妹的善意,最后竟然参与到刘德裕谋逆之中。事发之后,唐太宗决定将这位大舅子处以极刑。
长孙皇后闻讯,立即赶到丈夫的面前,向他叩头痛哭,哀求饶恕长孙安业的性命。她说:“安业谋逆,万死无赦。然而他当年对我不慈爱的事情早已天下皆知,如今处他死刑,外人一定会认为是我趁机报复哥哥,这对皇上您的名声也是莫大的拖累。”太宗答应了她的请求,长孙安业免于一死。
在平常的生活里,长孙氏非常节俭,服饰器物,都只是恰好够用而已。太子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觉得东宫器物不足,要求增加,长孙皇后拒绝了,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然而对于庶出的皇子公主,这位嫡母却照料备至,对宫中其它的嫔妃,长孙皇后也十分关怀,她们患病的时候,长孙氏都要带着最好的药品和食物亲自去看望。李世民的冲动脾气常会按捺不住发作并责罚宫人,每当此时,长孙氏都要设法拖延处罚,等皇帝气消了之后再慢慢为待罪宫人辩解。整个后宫在她的庇护下,从来没有谁受过冤枉的刑罚。后宫的女人孩子因此都对她满怀爱戴之情。
史书记载说,长孙皇后好读书,才学渊博,常与太宗对谈古今,对他深有启发。太宗深知妻子的见识才华,就与她谈论政事,她却从不在这种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她真正对太宗的“进谏”,几乎都只在他做错事要惹祸的时候才发生,都是为了丈夫的江山社稷、为了帮助朝中直臣,她才会挺身而出,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这方面,魏征是最鲜明的例子。
李世民一共有三十五个儿女,而长孙氏为他生育了其中的六个(三男李承乾、李泰、李治,三女长乐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但据《四库全书 子部 宋高僧传 唐上都青龙寺法朗传》中记载:“龙朔二年,城阳公主有疾沈笃。尚药供治无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爱殊厚。……”也就是说,城阳公主也是长孙皇后所生,她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
做为皇后的嫡出长女,长乐公主得到了太宗特别的宠爱,当她出嫁时,太宗下令为女儿准备倍于妹妹永嘉长公主的嫁妆。嫁妆还没备好,魏征就得到了消息(老魏头在管皇帝闲事方面格外得心应手,就象有顺风耳的一样)。他马上跑来进谏,太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宫后,他带着歉意将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妻子。长孙听了非但不埋怨,反而说:“我与陛下是结发夫妻情义深重,每次要说话时仍然要察颜观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如今魏征身为外臣,却能不顾自己的安危犯颜进谏,实在是难得的贤臣。常言道‘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希望陛下详查。”随后,她又赐给魏征钱四百缗、绢四百匹,并传话说:“早已听说您的正直,如今才终于见到。希望您继续保持这样的心地情操不要变易。”
魏征实在是个不会看领导脸色的部下,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当面让太宗下不来台。有一次,太宗实在是被他顶撞得气愤不过,退朝之后恨恨地对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谁是这个乡巴佬啊?太宗咬牙切齿地道:“魏征这个家伙,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我!”长孙皇后听后返回自己的宫中更换朝服肃立于庭中向太宗行礼。太宗惊问原故,长孙答道:“妾闻主明臣直。如今魏征如此耿直,自然是因为陛下你已为明君。我怎能不向陛下道贺。”长孙以她的睿智和对丈夫的了解,轻轻的化解了太宗的怒气,既救了魏征,又令太宗明白直谏之臣的可贵,也加深了夫妻间的感情。
长孙皇后所做的这些,即使你认为她是在做秀,是在故示大度,她也还是做了,而除了她,再也没有其它的皇后做到过。
长孙氏所做的这些,是在做表面文章迷惑世人,以图巩固后位,方便自己做太后并为所欲为吗?
答案:不是。
那一年,正当盛年的李世民忽然身患重病,累年不愈,几度危殆。长孙氏虽然贵为皇后,仍然昼夜不离地侍奉着自己的丈夫。在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的同时,她飘飘的衣带上时刻都系着毒药,当毒药被丈夫发现之后,她平静地解释:“若有不讳,义不独生。”
——长孙皇后的毒药,映照着她的心境,与她的丈夫不惜带着可能是个拖累的她齐赴玄武门之变的那一刻遥相呼应。
史书上的长孙氏,总是那么的端庄慈祥,雍容华贵,似乎她生来就是这么个庙堂泥胎的“娘娘”模样。总算她留下了一篇诗歌,使我们能够看到大唐皇后巍巍母仪下的另一面。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质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那个桃花映照下美丽非凡,毫不掩饰情愫的怀春女子,才应该是真正属于长孙氏的形象吧。只是在这世上,只有李世民才明了那份“出众风流”有多么流光溢彩。
在她端庄无妒的皇后风仪下,仍然是一份鲜卑女子特有的固执爱情。只是她的表现方式,与独孤伽罗那么的不同。与其说她善待宫妃儿女纯是因为天生的善良体贴,不如再浪漫一点说她爱这个男人到了极处,甚至于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让他尽情地随心所欲。(不要跟我说什么因为他是皇帝,她不得不忍耐的话,因为早在少年初婚时,她就已经开始这样迁就他了)。煌煌史册,唯有那颗毒药令人晕眩地展现了一次长孙氏深入骨髓的痴情。
只可惜,面对那颗沉重的毒药,史书却非要说,那是因为长孙皇后不愿让自己重蹈吕后覆辙,所以打算提前解决自己,“以绝后患”。官方的神来之笔,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一对自幼结发的夫妻,在丈夫似乎将要走到生命尽头、妻子甘愿以身相殉的时候,(即使他们是皇帝和皇后),又怎么可能以这样的官腔表白心迹?!
然而,长孙皇后的这颗毒药没有得到派上用场的机会。太宗康复后不久,长孙氏就病倒了。
长孙所患的病,是多年旧疾“气疾”(哮喘、肺病)。用中医的观点,这实在是令人无法轻松的疾病。肺主气主悲,气不畅则郁闷焦虑夜不能寐。就算不发病,人也常有心思缜密多愁善感的倾向。然而就是这样体质的一个女人,却自幼丧父、寄人篱下。虽然长大后她找到了爱情,偏偏爱上的男人是李世民。幼年的不幸似乎只教会了她善待别人,却偏偏没有学会善待自己。嫁给李世民二十三年,是八千多个日子,她究竟又能有几个轻松安眠的夜晚?多年压抑的情绪,只会将她的旧病越积越深。
贞观八年,在生育最后一个孩子新城公主前后,潜藏已久的病魔终于发作,并迅速吞噬着长孙氏的生命。
尽管已经抱病在身,长孙氏仍然念念不忘她的皇后职责,随后的日子,唐王朝的宫廷内部也大事不断: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病逝,贞观十年初,太宗诸弟诸子徙封……于是她的病就始终辗转反覆。
最后,在一个深夜,她强撑着陪太宗出宫视事,风寒侵袭,病情迅速加重,医生也束手无策。皇太子李承乾只得想别的办法:“能不能大赦天下,再多度人入佛道,祈求神助?”长孙氏拒绝道:“生死有命,非人力所能变易。如果行善可以延寿,我自问一生也从未做过问心有愧的事;如果无效,又何必妄求福报?大赦是国家大事,你父亲也从来不参与佛道之事,实在不必为了我一人擅动天下法度,更不能让皇帝做他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
李承乾无奈,只得把母亲的话转述给了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将此事转奏太宗。长孙皇后的话使众臣都嘘唏不已,纷纷请求太宗大赦并礼佛。太宗统统照办并亲力亲为。消息传到长孙氏的耳中,她反复地要求太宗不要如此,太宗只得中止计划。
长孙氏的病,终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然而弥留之际,她最担心的仍然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获谴重臣房玄龄的遭遇前途,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一向小心谨慎,大小奇谋秘计他都有份参与,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过,实在是忠心耿耿。如果不是极大之罪,陛下就一定不要亏待他。”随后她又说:“对于我的家族,要想保全他们长久,就一定不能让他们掌握权要,给一个散官闲职就行了。至于我自己,活着无益于世,死了就更不能耗费世间资财。只须因山而葬,不起坟,不用厚重棺椁,以木器陶器陪葬即可,再举行俭朴的葬礼。还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言,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亦是陛下未忘妾也。”
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逝于立政殿,享年三十六岁。五个月后,唐太宗将年轻的妻子下葬于昭陵,谥“文德皇后”。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当年那副卦中的短短八个字,包含了怎样的含义,需要怎样的睿智、情操和牺牲精神,才能将这八个字写完。然而长孙氏短短的三十六年人生,却近乎完美地成为这八个字的诠释。
长孙氏死后,太宗在遗物中发现了她亲手编纂的《女则》十卷。
《女则》没有流传下来,根据记载,这部书中的内容,是采集古代女子卓著的事迹总汇,是长孙皇后平日翻阅以随时提醒自己所用,与班昭所著的《女诫》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在她生前,即使是她的丈夫都没有见过这部书。太宗手持妻子生前的著述,睹物思人更增哀伤。
长孙皇后生前,太宗虽然与她有结发深情,却仍然不免辗转于诸妃之间。似乎直到妻子彻底撒手人寰,拿到那部被翻阅得已显陈旧的《女则》,太宗才完全地触动,发觉自己失去了怎样的无价之宝,才明白自己曾经让她经历了怎样的冷清孤单。长孙氏在丈夫的思念中,日复一日地完美无瑕。所有活着的女人,都敌不过死去的她。
长孙氏去世前,太宗的女人们先后为他孕育了二十一女十三子。长孙氏去世后十三年间,后宫孕育的孩子却只有一个,而且离长孙氏之死也起码有六七年了。似乎正当盛年的李世民感受男女欢爱的激情,都随着长孙氏一起逝去了。
失去了长孙氏的不仅仅是李世民,大唐王朝也失去了它最好的皇后。
有位大人说,唐太宗李世民其实只是贞观之治的一个中心人物,那个年代真正的灵魂寄托在长孙皇后的身上。她用一种母性的慈爱和怜悯,呵护那个年代和贞观君臣。虽然世人一直认为帝父后母,但自长孙氏以后,中国的耿直之臣再也没有谁象魏征和房玄龄那样,得到过哪位皇后真正如母亲般至死都不曾忘记的照拂。她圆满了中国乾坤学说“父天母地”的女性形象。她的死却又过早结束了这一切。曾经在她的照料下稳稳当当的大唐后宫妃嫔子女,也整个地丢给了唐太宗去承担。以她的逝去为界;贞观纪年被分为前后两段,而这两段的不同,是那样的明显。贞观之治的中心人物唐太宗,也由洒脱豪放的前半生,走进了家事纷扰负担重重的晚年。
在重新起用了房玄龄后,李世民在宫中建起了一座高台层观,时常登台远望昭陵,他的妻子长眠在那里,他却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和她团聚。
然而魏征这个榆木老头却死板板地非要表现自己的百毒不侵,当太宗指着远方告诉他,那是皇后长眠的昭陵之时,魏老儿却坚持说自己老眼昏花看不清楚:“要是皇上也能时常这样望望太上皇的献陵,那我大概就能看得到了。”太宗无奈,只得拆去了那座高台,被迫收回了远眺妻坟的目光。
魏征固然是贞观名臣,但无论他做过怎样了不起的事迹,这番说话却只能勾勒出他僵硬的背影。只有从来不懂爱情更没有激情,靠呼吸教条维持生命的男人,才说得出这样愚蠢的话。只有一个根本不懂人情世故的男人,才会这样偷换概念,干涉别人的感情世界。更何况他伤害和贬低的,是曾经多次救过他的性命、给予他超出帝王知遇之恩的长孙皇后的爱情。
(老魏也许没有想到,自己死后被牵连受贬。长孙氏若还活着,他身后只怕也不会落得如此结果。)
失去妻子的李世民在此后的人生里,一直四处征召世家女子入宫。与其说是好色,不如说他试图在其它女人身上找回长孙皇后的影子。而他也似乎确实找到了一缕影子,她就是湖州女子徐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