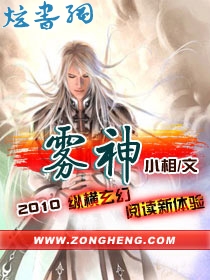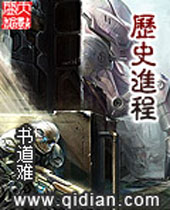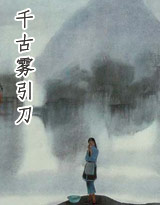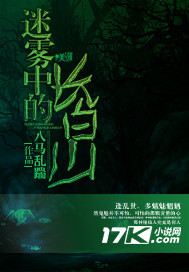历史的云雾-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2。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3。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
所以应参照其他资料,对回忆录进行考辩。尽管如此,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
近二十年来,所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可大致分为几类:1。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2。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3。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4。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5。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纂写的回忆录;6。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7。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8。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9。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10。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
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也有下列几类:1。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2。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3。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4。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5。有关文革的回忆录;6。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上述这些回忆录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宋云斌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
政治人物和文化界名人的相关回忆肯定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这类材料中较少看到普通人和底层民众的生活。九十年代中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天涯》杂志最先开辟了“民间语文”的栏目,陆续刊登了一些普通人的口述材料或当年的文献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民间书信》,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普通人都在纂写他们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有一本《50—70年代基层政治运动记实》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萧牧,1949年是一个21岁的青年,听信去台湾可读台大的宣传,和同窗好友胡里胡涂去了台湾,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陆的家乡,从此一辈子在基层被整、被斗,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去台湾的好友,几十年后成了台湾的名诗人洛夫。萧牧的回忆录没有出版,是自印本,对了解、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
我认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回忆录,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基本事实的了解开始,再来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路向。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毛的时候,应该重视,考虑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感受的问题。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不重视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史的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档案的开放步伐很慢;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对象距今不远,有关资料既多又杂。从资料的情况上讲,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具备,国外和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集中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这是离当下不远的时代,对认识今天和未来的作用更大。
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需要史识的修养和眼光;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具备历史学的基本功底,即真正能够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二十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二十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至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1〉〈2〉〈3〉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4〉这两种叙事方式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然而这两种叙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与“现代化叙事”相比较,“革命叙事”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将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和深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是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勿庸置疑,史学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述”的基本特点是:
1。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性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相,历史学家应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
2。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
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语言风格。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尔称,历史是“灰色的记忆”。即如有的史家所论述的: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5〉(p。191)“‘灰色历史观’反对在历史分析时时‘忘记’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在对重大现象研究中故意回避事实,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灰色的历史观”强调吸取其他社会学科的资源,同时注意运用的范围和界限,防止滥用社会科学方法,以至过度解释,深文周纳,而主张研究者在运用社会科学概念时不露痕迹,“滋物细无声”。所谓“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叙述”对研究的支配,克服在资料选择上的价值判断,重视对各种史料——包括内容上互相冲突的史料——的收集、鉴别和广泛地运用。〈5〉(p。195…196)“新实证主义”也强调对历史细部环节的注意,宏观叙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的,但更应通过细部研究来反映事物的特性。注重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概念先行,运用各种分析框架又不固步自封,强调总体把握也重视历史的细节和差异,显而易见,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当代史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重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当代史强调对基层和社会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故而重视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
研究当代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
在史料的从林中
——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一
本世纪中叶以后,国人写近世中国史,尤其在撰写涉及中共革命历史的著述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共两党隔海对峙,无论在大陆或台湾,学人都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学人稍有闪失,立时就会遭遇无妄之灾。除此之外,还有史料搜集和史实判断方面的困难。因为可得的资料不仅数量很少,且多为单方面的资料,即便这些单方面的资料,许多也已经过删改和过滤。
上述两方面的困难使得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在很长的时期内出现了一些独特且早已被国人司空见惯的现象:1、史官写作甚行,海峡两边皆有史官,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基于民间立场的中共革命历史方面的著述难见踪迹。2、与第一种现象相联系,中共党史研究大多以集团写作的方式进行,这又以大陆为甚,台湾虽有少数私人写作,但作者身分泰半为史官,表达的仍是某一政治集团的解释学,具有个性色彩的写作不是完全没有,但确实不大多见。
意识形态控制严格和资料严加封锁,固然可以封杀住官方以外的任何研究,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资料逐步对外开放后,新一轮的问题又出现了。中共革命为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现象,近代以来,出版业渐趋发达,在30…40年代就已有许多有关中共革命问题的论述问世,如今这些资料都可由学者自由使用。80年代后,国内政局朝开明方向发展,官方已陆续出版大量资料。与一般理解相反,目前有关中共革命的资料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既有中共历史文件的正式刊印,又有大批回忆资料出版,从数量上讲,近20年来这类史料和论著,已到了车载船运、汗牛充栋的程度,以至有学人感叹有消化不了之虞。
“消化”问题即史料研读和判断的问题,此为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关键。80年代后,大陆虽陆续开放史料,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