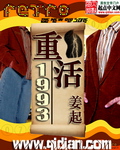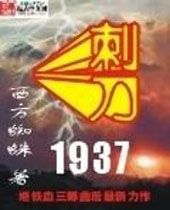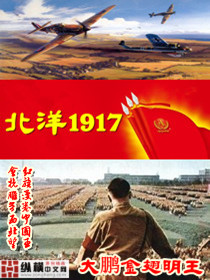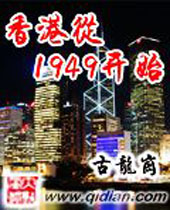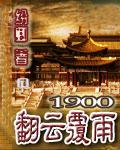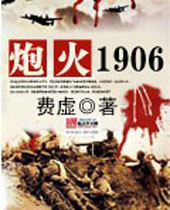生逢1966-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一点表白。再加上小木克是不主张武斗的,他就再也没有吃什么苦头。每天他回到办公室,他临时被关押的地方,他会很自觉地翻开毛主席著作学习。有时还翻开《资本论》、《自然辩证法》之类,初中没有毕业的红卫兵看到这样像砖头的著作,便渐渐有了一些敬意。
有一天,校长突然起不来了。他在他的那个办公室里坐着写检查,写着写着下半身就成了泥塑木雕,膝盖弯曲,双脚麻木,双手不住地颤抖。卫生老师在赤脚医生学习班学过了针灸,就到办公室为校长扎了几针,校长的膝盖松了,就颤颤巍巍站了起来。可是他的老伤复发,实在不能走路了。像一根桩子一样,校长戳在办公室的当中。
“你是在装死啊!”初中生们突然警醒了起来。于是提了浆糊桶就要出门刷标语。
小木克来到校长的办公室看了看。又问了卫生老师。校长本来以为小木克要为难他。不料小木克非常爽快地说,可以将校长送回家去。校长开始有一点疑惑,后来看到一个“反到底”初中生推过来一辆黄鱼车,让校长坐在上面。另外两个人陪着,小木克亲自踏黄鱼车。黄鱼车经过淮海路。校长贪婪地看着久违了的商店,行人,标语,很新奇的样子。他突然感到,他的双腿在这个时候发病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他又看看小木克,小木克很和蔼地回头看着校长,对他笑了一笑。黄鱼车进了大同坊,又转弯进了小弄堂,在校长家后门停住。校长想往下跨,两条腿依然如同假的一样,指挥不动。
生逢1966 9(7)
人群恰好在这个时候聚集过来了。这时出现了一个会被人长久记住的画面,在很多人视线的交集注视之下,小木克往前走上一步,背转身,弯下腰,周围的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在边上呆看着。小木克就用手势示意着,让别人将校长往他的身上靠靠。边上的人在当天简直如同被绷紧的阶级斗争的弦一样,紧张而又笔直地站着,没有动作。小木克于是往后退了半步,用自己的背脊将校长的腹部紧紧贴着,双手后伸,搂住了校长两条指挥不动的双腿,把校长背起。在周围人惊讶的眼睛中走进了后门,手扶着扶梯把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全弄堂的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很多人张开的嘴巴很久没有闭上。
有一天,小木克专程到校长的家中探望,让瑞平陪着。校长要从床上起来,小木克就说:“当心当心,你还是躺着的好。”瑞平看着小木克嘘寒问暖,校长唯唯诺诺,突然感到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完全错位了,小木克越来越像一个领导了。
从校长家出来,小木克就进了瑞平的家门。
“你不再斗争校长了?这不是白斗吗?”
“世界上有白做的事情没有?没有。你我不是已经成为红卫兵了吗?我不是早就说过,我们要砸碎的是自己身上的锁链吗?瑞平,我们在球场上不是要将球扔进篮筐吗?我们就是将对手打个血流满头,还是没有得分。我们得分只是因为我们在正确投篮,而且投中了。”
校长静静地躺倒在床上,从此他和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无缘。沿着小木克的篮球思路,校长这回就像是被五次犯规罚了下来,不能再在场上运动了。学校中依然有大字报,没有人将批判他大字报的内容讲给他听,没有人来报告学校的动态。人们渐渐将他遗忘。
当文革的最初冲击已经过去,学校开始变得安静了。这是因为,很多的学生已经出门串连去了。校长被打倒了,就没有谁能阻止学生的革命行动。学校教导处的老师无数次地为学生敲上证明上的图章。证明起先还是铅印的,后来走的人太多,就变成了油印的。学校已经成为一个空巢,不久就又满了,那是外地的学生从遥远的地方走了进来,睡在了那些空空的教室里面。陈瑞平他们选择的是步行串连,这是那些成分不好的学生的选择。陈瑞平很幸运,因为和他一路的还有汤老师和蔡小妹。他们走的时间最长,一走就是两个月。他们一直走到了北京。当他们从长征回来的时候,“一月风暴”已经在上海卷过了。上海工总司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造反团体。他回家的时候,意外发现妈妈的手臂上缠着一个崭新的工总司的袖章。妈妈造反了。不管怎样,妈妈也算和爸爸划清了界线。爷叔是恒大厂的功臣。他派一个人和工总司接洽,派另一个人和赤卫队联系。就在最后的一刻,他决定参加工总司,于是全厂的工人无一例外全部带上了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章。而董品章同志就成了工厂红色的造反司令。
生逢1966 9(8)
妈妈把瑞平堵在家门口,不许进房门,就在瑞平的手里塞上两角钱和一个装着干净衣服的书包,让瑞平立刻转身到浑堂洗澡。然后,妈妈喊了蓓蓓过来,将瑞平的衣服全部放在一个大脸盆里,用水煮着。热气蒸腾起来。妈妈一面骂虱子,一面在骂瑞平。蓓蓓从对过下了楼,来到90号的灶披间,蓓蓓恢复了她的美丽和伶俐。她看着瑞平,指着面盆里那些有虱子的衣服,一脸坏笑。瑞平忽然感到这个家又有了一点温馨。
“蓓蓓和好婆都要到香港去了。”妈妈说。“以前好婆申请了一年没有批准,现在两个人一道申请,三个月就批准了。”
“好婆先走,我晚走。”蓓蓓说,她很妩媚地看了瑞平一眼。瑞平当然对这样的眉眼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是和汤老师蔡小妹一起长征,毕竟他们是在革命,而汪蓓蓓已经游离在革命的范畴之外了。
有一件事情很叫人意外,这是瑞平到学校之后才知道的。他们长征走了三千里,目前并不能构成新闻;因为校园里到处在流传着小木克在安亭的“壮举”。后来在校园里,瑞平看见小木克站在红卫兵团办公室的门口,手臂上戴着的袖章不是红卫兵的,而是工总司的。
“不容易啊,”小木克说,拍了拍瑞平的肩膀,“走了三千里。”
“不容易,成了安亭事件的英雄。”
小木克就哈哈笑了起来,说不过是碰巧而已。
整个安亭事件就是一种偶然,或者说是碰巧。当年这些工人因为种种原因在工厂里不得志或者被批斗,于是就联合起来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也好拉大旗作虎皮。不料市委就是不承认。他们就威胁说他们要上北京告状。他们栏了一辆火车,火车到了安亭忽然就不开了。那些工人就在安亭阻断交通,逼着上海市委表态。在安亭,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他们渡过了生死攸关的两天,这才想起了肚子饿。
“我去弄点吃的。”一个学生这样说,他不知什么时候上了那列被引上了岔道的火车。
那个有一张白白的脸,俨然一个首领的人物说:“好啊。”
这个学生正是小木克,小木克一向很好奇,只要哪里有事,他一定会出现的。他偷偷到了安亭,“反到底”里谁都不知道。他的怀里正好还有串联余下的钱和十多斤粮票。
他摸到了一个工厂食堂。递上钱和粮票,那个胖胖的老师傅说:“你不要惹祸就好了。弄得不好吃官司!你小人走开。”他找到一家饮食店,那里的店员将头摇得像钟摆,一万个不答应。小木克第三次撞上了一个大饼油条摊头。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谎说是步行串联的,好大一队人走得晚了,还没有吃饭。老师傅这才把炉子捅开,烘了一百多个大饼。
生逢1966 9(9)
饥饿之中的首领和他那一伙狼吞虎咽啃着大饼。他握着小木克的手说:“谢谢,谢谢。”
小镇上传说,安亭已经全是便衣,公安局将来抓人。不管是谁,如果继续胡闹,将严惩不贷。小木克就悄悄离开了安亭,一路上非常担心便衣已经将他的照片拍了下来。
小木克本不确认他们一定会成事。不过他知道,他的爷爷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如此做的。正如当苏北苏南一片混沌的时候,爷爷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之下,奔走在江淮上海之间,想方设法接济过新四军。谁也没有想到,小镇上的这场闹剧,最后变成了一场正剧。小镇上狼狈不堪的故事最后被称为是一场革命。
红旗飘飘的文化广场,一个超大级别的“人民公社”成立了!口号纷飞,誓言铮铮。当背景已经改变,一个站在主席台上的人完全和一个蹲在铁轨边上的人不能同日而语。小木克便也相信,这个面孔白皙的人,确实领导了一场工人运动。小木克耐心地候在文化广场南门的出口,在心里说,如果等到他的大脑皮层淡忘了那些大饼,对于小木克来说,可能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他走出来了。他换上了一件旧的军装,他的脸依然白皙,加上连夜没有睡觉,他的眼睛中满是红丝。他确实记起了小木克,他疲惫的脸上有着笑容,他将手伸向小木克,并且对一边的很多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说:“我们不能忘记红卫兵小将对我们的支持,这位小将,就在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送过大饼。那对我们是有很大的鼓舞的!”
“不仅是我一个人,是68中的反倒底兵团。”小木克这时非凡聪明,记住68中“反倒底”,要比记住穆亦可更容易。
他就这样获得了一个从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发出的红袖章。他也因此成为68中红卫兵团的司令。
生逢1966 10(1)
陈瑞平走在黄渡的街上。
那已经是一九六七年的初夏了。学校几乎已经走上了正规,以往年年要做的下乡劳动,这一年就在盛夏进行。即使下乡,学生也免不了要开批判会,要刷大标语,镇上的文具店一直很热闹。陈瑞平从店里买了红纸,回大队去。
黄渡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那是上海资格最老的土地之一。那些住在亭子间里每天倒着马桶“上海人”人看外地人时候傲慢地将眼睛长在额角头上,其实他们的上海家谱最远不过只有三代。而真正有历史的上海人却安居故土,不愿走过这几十里路进城。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这可能是一种矜持,而下场却是被外地人的后代叫做“乡下人”。
黄渡正是春申君二百二一百多年前誓师渡江助赵抗击强秦的地方,黄渡之“黄”就是他的姓。黄渡镇沿着一条河,这条河正是上海以后因为流淌如同石油一样液体和发出刺鼻的异味而臭名昭著的苏州河。不过这里的人宁愿叫它的古名吴淞江,这样可以回忆它曾经要比黄浦江宽阔得多的江面和无数的帆船。这一段河流委实清澈可爱,苏州河在这里是一个处女,还没有被工业玷污。河上有桥,千秋桥的老桥早已经坍了,桥柱也已经不见了。这新桥也已经很老了,桥柱和桥栏上的水泥已经风化,一片片的掉下来。桥是单孔的,桥下带有江南常见的青苔,被湿热的天气一养,绿得发乌。
陈瑞平没有走过桥去,西面正有一阵乌云飞来。桥下有几枝水杉站立在房子间,水杉去岁的细细的树叶落在屋顶上,红红的散在瓦沟中。他见到中间有一栋高高的房子,门前凸出很宽的一檐,就走过去。上海乡下当年是不锁门的;锁环空空地荡在那里。门虚开着,一推就被风吹开了,他要反身关门,突然就“呀”地一怔。不意背后就是汪蓓蓓。陈瑞平吓了一跳。就像是许仙在西湖边上遇到了白娘娘。许仙不是仙,白娘娘却是妖。蓓蓓和白娘娘一样美丽,一样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确实很妖。
上海郊区的房子往往没有院子,正中的一间就是客堂间,汪蓓蓓就站在那里,她不管怎么站,总有一种特别的风姿,她永远不会很正面地对着你,她知道怎样站最好看。汪蓓蓓看见陈瑞平并不惊讶,很自然地喊了一声:“瑞平。”很久没有听见蓓蓓这样喊自己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的家不是就在黄渡吗,不过是在乡下。小娘舅正好到镇上送公粮。我就顺便过来看看。”蓓蓓很好看地一笑。“你不是在老街上逛过,在文具店里买过东西?”见瑞平有一点愕然,蓓蓓便更好看地笑。“你从桥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坐船正好从桥洞里面穿过去。我就对小娘舅说,我就在镇上走走吧。小娘舅就让我在这里上了岸。我就跟着你走。”
生逢1966 10(2)
“坐下吧,这雨一时总不会停。”这一家摆在客堂中无非是一些沾上泥巴的农具和桌子板凳。瑞平于是和蓓蓓一起坐在一张方桌子边上。蓓蓓两只眼睛看着瑞平,使瑞平有一种被玩弄在股掌之上的感觉。蓓蓓的语气是温和的,她说:“你怎么还像小学里一样分男女生?”
这时,他们听到了像野马奔腾一样的声音,由远及近,接着,听到了门口很响的雨声,屋顶没有做泥幔,雨击在瓦片上听起来如同密集的鼓点一样。他们能从开着的门中见到瓢泼的雨击打着地面生出一片茫茫的烟尘。苏州河上已经没有了船只,只见暴雨将数丛芦竹打得乱点头。水面上长出无数密密麻麻的芒刺,像一片白色的地毯。又是闪电,又是雷声。屋里根本不能听见对方说话,瑞平似乎有了一点解脱。蓓蓓掩起了门。屋里的分贝下降了一点。她又说:“你怎么不说话?”
瑞平无路可逃,眼睛很木然地看着陈旧的石灰墙,那里有一只很大的蜘蛛,正在爬着,顺着墙有一股小小的水流,将蜘蛛的全身泡湿了。
“很困难吗?和我说上几句话?”蓓蓓冷笑着说。“弄堂里谁都知道我是一个逃兵,是一个受不了艰苦从新疆逃回来的人。大家都说这是陈瑞平说的。”汪蓓蓓愤愤不平地说。“当年,我到新疆去。你们都说我是假积极。是为了骗一个团徽。现在我回来了,又说我是《年轻的一代》中的林育生。”
瑞平不说话,当年,他就认为一个人在学习雷锋的时候还是一个落后份子,在贯彻阶级路线的时候,突然就成了积极份子,似乎不可信。所以现在蓓蓓从新疆回来从逻辑上说也是很正常的。他看看蓓蓓,就这样说:“如果是我,我一旦去了新疆,就不会回来了。”
“你啊,我还懒得为你生气呢。瑞平,当年你也报名去新疆的,如果批准你去了,说不定你也要会来的。你不要总想着你是对的。你也有错的时候。就像是在做物理,你也有九十九分的时候。你就是不会从对方的角度想一想。”蓓蓓的两眼满是泪水,她用手帕擦着,总也擦不干。
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