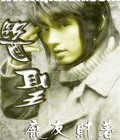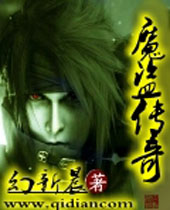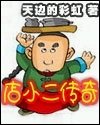医圣传奇-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文
全文
中篇小说
医圣传奇
赵秀林
一
医圣林自傲成为医圣之前,在奉阳城里最有名的药店“仁和堂”学徒拉药斗。
“仁和堂”姓马,一直姓了二百年。马生冰马先生祖上好几代,就已在奉阳城里稳稳扎住了脚跟。
古来,人们根据各自生存手段不同,把各种职业分做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七十二行。儒者居首,医商百工属下九流。
古人重儒鄙商是有道理的。
儒者,孔圣人弟子,清贫固是清贫了些,却清高。用一个字概括即:雅。商人呢,孔方兄信徒唯利是图之辈,满身铜臭气冲天。一言以蔽之:俗!
当医生开药店,表面上似乎介于商儒雅俗之间,其实根子上还是商家本性。
俗语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这是古德古风。当世间做医生开药店的,又有几个能达到这种境界了?虽不至于一个个全都昧了良心恨不得世上人人都生病都吃药都请医生,至少也盼望自家药店生意兴隆,没一个想着早早破产关门大吉。看来,古人将医者药者统统归入下九流,一点不冤。
在医生这行当中,又是分做三等九级的。最差一级是摆地摊,俗称“卖狗皮膏药”的。说是卖狗皮膏药,卖的又远不止于狗皮膏药,什么神力王大力丸牙疼药水粉刺膏,沾点药腥儿的都卖。哪儿人多,哪儿红火热闹,,摊子就往哪儿摆。这种人挣钱不靠药,就靠肚里花花肠子多,靠嘴甜嗓门大,巧舌如簧死人也能说活。反正,吃的就是坑人骗人这碗饭。
比这些人稍好点的,不摆摊了。摇一只嘶声哑气的破铃铛,提只破药箱或是肩条旧褡裢,红火热闹之处不去,专捡偏僻小胡同走家串户游荡。碰巧赶上哪家有人不舒坦,头疼脑热的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不值请医求药,抗两天就好。正在那里抗着,偏偏就有医生送上门来了。什么“国医圣手”、“妙手回春”之类的大牛皮绝对不吹,只是低了头嘴里反复嘟囔一句话:“不治病分文不取。”
治不了病不要钱?那好,那就顺便请进来瞧瞧。治得了更好,治不了反正也扯平。
这一类,比那些摆地摊卖药的高明多了。那些人全凭一条舌头一张嘴,弯来绕去,谓之“套”。人上过几次当,这一套便不灵了。任你玩得再漂亮,也没人肯再充大头叫你捉。
这一类不玩这个。你不信“套”是吧?我根本就不套。手一伸,寸关尺一按,双目一闭,闲话正话统统不说。
大凡做医生的,都讲究个望、闻、问、切,叫做四诊。这先生怪了,偏偏一句话不问,只伸手切脉。切脉就切脉吧,又要闭上双眼,这下好,连“望”也免了。
这叫直钩钓鱼,专钓那些自作聪明的倒霉蛋。
世上还真有这种倒霉蛋。你不说话,不睁眼,他就觉得你高明。岂不知,眼睛闭了,耳朵却是不闭的。正张得大大的在那里,专等着听你说呢!
先生诊脉,病人家属都围一旁看。按理,医家诊病,最忌的就是人多嘈杂。这先生不仅不忌,还就喜欢这个热闹。热闹了才有戏。
不大会儿,果然就有戏了。
见先生作出如此高深模样,看的人忍不住好奇,嘴里就叽叽喳喳小声议论开了。你说这先生兴许还真请对了,有本事。我说不见得,高明不高明就看治不治得了某某这个病。他又说某某又不是什么大病,不过受些风寒暑热,只要找准病根,还不是药到病除……看看,先生那里一句话不说,他这里倒什么都说了。
有人就这样。你问,他不说,小看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不问,他倒以为你高明,什么都知道了。先生要的就是这出戏。这下好了,听一半猜一半,心里有了底。切脉原本就是做样子的,这会儿样子自然不必再做。慢慢睁开眼,先轻轻“哦”一声,张口便道: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
说的是医理病机,又是古文,大多听不懂。听不懂,才更觉先生学问高深,一个个肃然起敬。至于本病,先生早已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然是一说就中。于是人人大惊,连呼“神医”。
病根说中,“神医”却不忙着开方下药,口中念念有词,再次闭目凝神作沉思状。片刻,忽然睁眼,展纸挥毫笔走龙蛇,一服药方一挥而就。有了药方,也不必麻烦跑什么药店,所需货色尽在先生那药箱或褡裢之中。伸手进去,抓一把干草桔梗,或是拈几许自制的丸散膏丹,如何煎如何服又极郑重地叮嘱再三,这才放心。
这时候,先生进门时那句“不治病分文不取”的话,早被病家自己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病人那边吃药,先生这边吃饭。酒足饭饱,大功告成。匆匆将主家奉送的酬金往怀中一揣,双拳一抱扬长而去。
那些摆地摊的,大多对医道一窍不通。卖的狗皮膏药或是别的什么丸什么散,也大多是假了又假。这类先生不同了。虽谈不上什么医术不医术,对医道多多少少还是懂一点的。什么《内经》、《伤寒》、《金匮》之类医家经典,都可随口背出几句。从药箱或褡裢中抓出的货色,也是绝对的货真价实。至于对不对症治不治病那是另外的话,但要说吃他的药立刻便会死人倒不至于。
说来说去,这些下三滥的玩意儿,根本就称不上“医生”二字,整个一伙臭要饭的!
偏偏就没人喊他“花子”或者“乞丐”。
碰巧赶上病好的,尊他一声“走方郎中”;白白赔了饭赔了钱上当受骗的,也顶多骂他一句“江湖野太医”拉倒。
做医生的,能混到在大街上立门面,称某某“堂”这一步,就不容易了,就算入了流。首先不敢靠嘴皮子碰运气。人命关天,怕砸招牌吃官司。走方郎中和摆地摊的都是江湖人,四海为家来去无踪,就算闯了天大祸事也没地方找他去算什么帐。这些大大小小的“堂”可就不同了。招牌在那儿亮着,门面在那儿戳着,走不了天也跑不了地。
做医生开药店,虽说都称“堂”,但这“堂”与“堂”之间区别可就大了。不仅有规模大小之别,更有高下优劣之分。奉阳城里药店不少,但像“仁和堂”这样牌子亮,根基牢的,也是屈指可数。大多数也只是勉勉强强支撑个门面不倒而已。
当然,药本身并无什么高下之分,店本身也没什么优劣之别。硬要分出个高下优劣的,是人。
说明白了,药店生意好不好,根基牢不牢,招牌亮不亮,关键就靠一个人——坐堂先生的名气和本事。
说起“坐堂先生”这称呼,得追溯到东汉张仲景。是时,仲景先生任长沙太守,正值当地瘟疫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为解万民倒悬,先生放下太守架子,就在府衙大堂公开挂牌行医济世,自诩“坐堂先生”。
多少年下来,先生长沙太守官声如何品评无多,倒是凭着一双回春妙手救治不少百姓。自己赢一代“医圣”美名不说,还替后世医者挣来诸如“大夫”、“郎中”、“太医”、“先生”等等诸多尊称。
可惜后世医者,无人再有机会坐上大堂行医。于是便有聪明人出来想主意,将天下所有大大小小的药店药铺统统称作“堂”,主治医生一律尊为“坐堂先生”。
“仁和堂”在奉阳城最繁华最热闹的小东门亮招牌立字号,一立二百年不衰,靠的,自然是马生冰马先生祖上一双双回春妙手。
马先生祖上的医术与功德是不容置疑的。奉阳人都知道,单是“仁和堂”这块匾额就非凡品,乃清时本省抚台亲笔所书。堂堂上九流的朝廷二品大员,为下九流的小小药店亲笔题匾,足见马家“仁和堂”名气之大。
二百年后,“仁和堂”传到马生冰马先生手上,那更是名显及巅如日中天。马先生承袭祖业,却并不倚仗祖宗名气撑门面立招牌,靠的,全是自家真才实学。
马生冰马先生究竟多大本事无须细说,反正奉阳左近都尊他作“圣手神医”。又送一副对联,镌于“仁和堂”店门两侧。那对联是:
医天上神仙难医之病
救世间高手不救之人
你想想,光靠祖宗名气,能挣来“圣手神医“这尊号?没有足够本事,就算别人肯送,自家也绝不敢刻这样一副对联在门上的。
只是,称尊号送对联的都没想到,如日中天的“仁和堂”竟然说倒就倒!二百年的金字招牌,恰恰就砸在“圣手神医”马先生的手上!
这倒怪了!奉阳城里那许多的药店平平庸庸,反倒一个个招牌照亮,门面照立,大名鼎鼎的“仁和堂”怎么倒说倒一下就倒了呢?
其实不怪的。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老祖宗们讲得实在够透彻了。
二
“仁和堂”砸招牌这一年,林自傲刚好二十岁。
这年,马生冰马先生刚刚决定,他的大弟子余鲁,二弟子林自傲正式随师学艺。就是说,即日起,两人不必再拉药斗,可以跟着师傅坐堂打下手,抄方,录病案了。
进药店学徒,跟学任何生意一样,初进门都得从小伙计学起。未入师门的小伙计,干得多是打水扫地之类的粗杂活儿,跟本行离了十万八千里。干活吃饭没工钱。干两三年,掌柜满意了,升一级,站柜台拉药斗,称小学徒。虽说还是吃饭没工钱,到底离本行近了不少,在店里地位也稍高了些。再熬五六年,熬到给师父抄方打下手这一步,才算正式踏入师门。师傅正式宣布收徒,弟子行磕头拜师大礼,店里店外都称“小先生”或“二先生”。
没想到,两个弟子头天刚行过拜师大礼,第二天就发生了天大变故!
这天,“仁和堂”刚刚开门。小伙计扫净店堂。小学徒整好柜台装满药斗。余鲁跟林自傲两位小先生伺候好桌椅笔墨,沏一壶上好的“碧螺春”,恭恭敬敬候着师傅出堂。
师傅没出堂,外头一班人倒呼啦啦涌进来。
先是两个短衣打扮的精壮大汉,一进门两边一立,打桩似地再也不动。随后进来一位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人,白脸,高个,一身青色软绸长袍,手里一把纸扇半开半合,斯斯文文像个饱学名士。再后又是两条大汉,进退不离那人左右。
一眼便可看出,先后进来的四个人都是随从之类,正主儿是中间那位。
那人双拳一抱,话说得彬彬有礼:
“有请马神医马先生出来讲话。”
马先生大弟子余鲁连忙抢前一步,抱拳答礼道:“家师尚未出堂。请教尊客贵姓?”
“请马神医马先生讲话。”
对余鲁的话,那人好像根本就没听见。
余鲁一愣,随即恢复满脸笑容:“尊客稍坐请茶,家师……”
“老子们没这闲工夫!快叫马生冰出来!”
主人斯文,随从可就不那么客气了。余鲁一句话没说完,两大汉膀子一顺,就把他撞个趔趄。
反了反了!青天白日如此上门欺人,还有没有王法了!血气方刚的余鲁脸色涨红,刚要上前讲理,信目一瞥,见店门外还有人。门外也是四条大汉,却非寻常打扮,挎刀带枪全副武装,是军人!
余鲁舌头一缩,赶紧把就要出口的话统统咽了回去。
按说,马生冰马先生既称“神医”,上门求医的自是不少。什么高官贵胄,乡宦名流,“仁和堂”也见得多了。任你职位再高权势再大,到了求人治病救命这一步,没奈何也得稍敛威风装个和顺讲理的样儿出来。
但这回不同了。这回是军人!
“仁和堂”传到马先生手上三十年,还真没跟军人打过什么交道。军人生病自有军医,一般不扰地方。有时候事情急了实在避不开,也多是找那些公立医院,犯不着找这些私人药店的麻烦。也是说呢,又有哪家药店愿意跟军人打交道了?有道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更何况现在,三大战役一打,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这些军人更是成了没头苍蝇,天大爷管不着天二爷,一路逃窜一路横抢竖掠生吃白拿,整个一伙混不讲理的兵痞!
那么眼下呢,眼下怎么办?没办法。
既然你“仁和堂”牌子没摘门没关,那么不论什么歪三瘪四,进你们的就都是天老爷,你敢不装孙子应酬?
余鲁没办法,使劲咽口唾沫,硬着头皮挤出满脸的笑:“请问尊客,是要家师出诊呢,还是……”
“是请教。”
请教?余鲁眨眨眼,不懂。
那人依旧斯斯文文面无表情,半晌才慢腾腾又说:“首先请教贵店门前楹联。”
余鲁心里咯噔一跳。门前那副对联,虽说口气有些托大,意思却是极易懂的。这人开口便说什么“请教”,难道……心里顿时涌上一丝不祥之感。
余鲁本是个极聪明极灵泛的人,脑瓜子跟眼珠子一样转得快。进“仁和堂”学徒刚刚五年,便跟学了十二年的林自傲一同拜了师。而且还做了大师兄!但眼下,这闷葫芦实在有点难解,就连余鲁这样的聪明人,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一点头脑。眼珠子骨碌碌转着,嘴里实在不知如何对答。
等半天不见师傅露面,徒弟又这样张口结舌的干耗,两名随从早不耐烦了。
“什么神仙不治之病,名医不救之人,好大牛比!咱们柴司令老爷子丁点小毛病都料理不来,倒有脸称什么鸡巴神医……”
一听“柴司令老爷子”几个字,余鲁心里一下有些明白了。
前几天,师傅确曾被人请出去看过一次病。来请的是个胖敦敦的中年人,一身寻常便衣。虽没说什么司令不司令,但从那以后,师傅连着几天愁眉不展,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究竟什么心事,师傅不讲,做徒弟的自是不好多问。现在看,多半就是这事了。这样一想,余鲁鼻尖上立刻沁出细细一层汗珠。这伙人,是来找茬闹事的!
这时候,左邻右舍许多商家字号,生意也顾不得做了,掌柜伙计一个个探出半边脑袋,眼珠子瞪圆了往这边瞅。同行是冤家,盼着“仁和堂”早日倒霉的可是大有人在!日头高了,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渐渐多起来。见“仁和堂”这边出了事,一个个也都围上来瞧热闹,观候这场官司究竟如何着落。
看看是时候了,那人就又开了口。依然是斯斯文文慢条斯理,但这回却是冲着围观的人群说话。对呆在一旁张口结舌的余鲁,连看都没看一眼。
“兄弟姓吴,在柴司令手下当差。前几天,咱们老太爷偶染小疾,司令青衣小帽亲自登门来请马神医马先生。从礼数上讲,总该没说的了吧?”
姓吴的环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