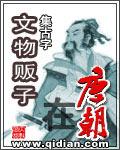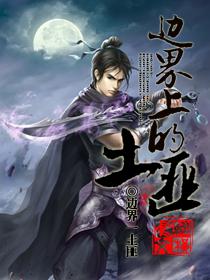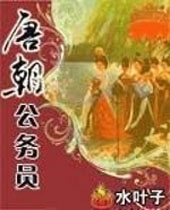唐朝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宗上前拉起房玄龄,“任务很重,卿要多多费心。”
君臣二人都微微一笑。
最后房玄龄等人定京官文武共643人,裁汰了一批官员,大大精简了中央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
同时,房玄龄还编写了《唐律·职制》,对各种官员的违法乱纪现象作出了法律上的制约。比如,规定指出:诸官都有法定的员数。如果主管人置员过限或者不应置而置,多置一人杖一百,多三人罪再加一等,多十人徒二年。这样就有效防止了人员超编。同时,律文中还对官员贻误公事、办公出错等现象规定了惩罚的条款。而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严格实施,贞观初年才出现了政治清明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太宗与魏徵同样也讨论过选任官员的问题。
当太宗提出要为官择人,不可滥进之后,魏徵则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想得到英才,必须认真察访他的言行。如果知道此人品行端正,那即使他办事能力不足,也不会有什么大害。但如果误用品行不好的恶人,危害可就大了。在乱世,用人只求他有才,可以不管品行;但是现在太平之世,就一定要才德兼备才行。”
魏徵提出的是一个用人原则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说具体怎么操作。而房玄龄则是制度的具体制定者和落实人。魏徵与房、杜的不同由此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确定了官员的人数,规定了每个职务的责任,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要真正做到“官在得人”这一原则,还要选择合适的人来担任不同的官职。
贞观三年(629),太宗对分别担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由此可知,为国选才,也是房杜二人宰相工作的一部分。
唐朝官员的选授,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在方法和程序上是不同的。五品以上官的选授不经过考试,是由宰相提名后,皇帝批准的。六品以下官的选授要通过考试,由尚书省吏部和兵部主持铨选。
房、杜作为宰相,自然要承担高级官吏的选授工作。并且杜如晦还兼任吏部尚书,负责中下级文官的任免。可见,房玄龄与杜如晦一直都在做着荐举人才选任官员的工作。
房玄龄本来就很善于发现人才,这在早年就表现了出来。所以太宗一贯很重视他在这方面的意见。
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到翠微宫暂住,玄龄当时在京城留守,没有同去。太宗任命了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不过又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正好有人从京师来,太宗就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拜尚书有什么意见吗?”
来人回答说:“房大人只是说李纬的胡须长得很好看,就没说别的了。”
太宗听后,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知道玄龄并不是很赞同,马上改授李纬为洛州刺史,不让他当户部尚书了。可见房玄龄的意见对太宗是多么重要。
为国家选贤才(3)
所以《资治通鉴》称赞他“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
为子孙立法度(2)
结合制度背景仔细分析太宗的人事安排,就能够发现太宗对房杜二人是多么了解,他用人是多么高明。如上所述,中书省主要职责是出谋划策,正可以发挥房玄龄善谋的特点;而门下省负责国家大政的决定审核,与杜如晦能断的性格吻合,“房谋杜断”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充分展现出来。太宗的这种布局,使贞观初年许多政策的制定及完善可以最大程度地顺利实现,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贞观三年(629),房杜分任左右仆射,太宗对他们说:“两位爱卿担任仆射,要多为朕访求贤才。听说你们每日要处理各种公文上百件,这样哪有时间去选拔人才呢?自今以后啊,小的工作都交给下面的人去干,大事你们再过问,多抽时间为朕挑选国家栋梁才是。”一番话点出了房杜的关键任务和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指导了他们的工作方向。
另外,太宗还对房杜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了一篇《拔士论》,文中指出一个人不可以担任数个职务,暗中其实是讽喻杜如晦等任职太多。太宗看了说:“玄龄、如晦不是因为有功才受到重用的,而是他们的才干确实可以助朕治理天下,师合难道想以此文来离间我们君臣吗?”下令将陈师合发配到岭南去。
贞观十八年(644),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留守京城,处理日常政务。并准许玄龄不用奏请批准,就可以直接拿主意,处理各种军国大事。在这期间,正好有人上访,声称要秘密告发一个人。
玄龄接见了他,问:“你声称要告发一人,那人是谁?”
回答说:“就是你房大人。”
房玄龄看着此人,想了一会儿,径直走出屋去,吩咐侍从:“派人将他送到皇上那里。”言罢便拂袖而去。
却说太宗听说留守房玄龄送来一个告密人,眉头一皱,很不高兴。一边命人持长刀站在旁边,一边叫那人进来。
“你想告发的人是谁?”太宗盯着他,问道。
“回皇上,是房玄龄。”
“果然是这样。”太宗自言自语,然后回头对持刀的侍卫:“拉出去腰斩。”
“陛下,还没有听草民要告什么啊,陛下饶命啊!”告密者脸色大变,连声求饶。
太宗也不理他,挥一挥手,让人将他拖了出去。
几日之后,玄龄收到太宗的来信,责怪他如此不自信,称“再有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因为与自己有关就有所顾忌。”
太宗对房杜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也是太宗自信的一种表现。君臣都如此优秀,也难怪后世常称贞观时期是君明臣贤了。
而更难得的是房杜二人同为英才,但都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能够精诚合作,互补长短,共助圣君。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而杜如晦则明白房玄龄善于提出好计谋,双方都明白只有两人相辅相成,方能建立奇功。
贞观三年(629),太宗与群臣谋事。大家意见不一致,事情怎么办,迟迟没有决定。太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看看下面的人,说:“怎么杜如晦不在啊?他这个人最会拍板。快去召他来见朕。”
旁边的侍从得令,马上去请杜大人。一会儿工夫,人来了。
“参见陛下。”杜如晦一进来就拜。
“不用多礼了,杜卿家。正有一事不决,朕想听听你的意见。”
于是众人又将各自的意见说了一遍。杜如晦听罢,沉思片刻,说:“臣以为采用房大人的意见最为合适。其他办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太宗表示赞同,立即差人按房玄龄的意见去处理。
隔了几日,事情圆满解决了,太宗很是高兴。对着房、杜还有群臣说:“人言房谋杜断,果然不虚啊。”
的确,在国家政务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善于献策的谋略者,也需要当机立断的拍板人,房杜二人正是各当其任。两人这种相知基础上的合作,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气氛和人事环境,保证了政务处理的准确与高效。他们的合作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对方,既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条件,也是贞观之治成就的一种表现。
为子孙立法度(3)
可惜的是,贞观四年(630)三月,杜如晦就逝世了,离开了他的主公和朋友。太宗悲痛难当,之后更是常常想念这位臣子,并流着泪对他的好搭档房玄龄说:“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房玄龄也是唏嘘不已,君臣相对无言。
孜孜奉国的贞观大管家(1)
所幸房玄龄还陪伴在太宗的身边,为太宗又完成了许多大事。比如修订律令,制礼作乐,编纂史书,贞观时期的制度由此更加完善,直至玄宗初年都没有大的变化。这其中有房玄龄很大的功劳。
而比起杜如晦来,可以说房玄龄跟太宗更加亲近。他像一个大管家般,管理着贞观朝的国事和太宗的家事,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魏徵和长孙无忌都不同,房玄龄的角色很是特殊。魏徵是个完完全全的“外人”,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太宗,都是将他摆在一个客卿的位置上。而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大舅子,长孙皇后的哥哥,当然是自己人。房玄龄则仿佛是介于两者之间,与魏徵相比,他对待太宗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
贞观八年(634),太宗想要纳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为妃。册封的诏书都已经下发,就差派使者去迎接的时候,魏徵听说此女曾许配给士人陆爽,于是当即上表进谏。太宗事先也不知道,看了魏徵的上书,才知道人家已经有婚约,于是命令使者不必去了。
房玄龄却上奏说:“此女许配给陆爽,并没有明确的聘书之类。现在册书已经下发了,不应该停止。”而陆爽自己也上表说并没有婚姻之约。
太宗又问魏徵:“房爱卿等人说大礼已经开始,不应该终止。而陆爽自己也说他并没有要娶郑氏之女。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
魏徵说:“陆爽是害怕陛下只是表面上放弃了郑女,而背后会整治他,才这么说的。”
太宗笑道:“外人可能真的会这么想。朕的话难道这么没有可信度吗?”最后还是放弃了迎娶郑女的打算。
其实,太宗对魏徵的再次发问,就表明他还是很想册封郑仁基的女儿为妃的。房玄龄心中一定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会上奏,给太宗再创造一次机会。在魏徵那里,太宗就是帝王,是一国之君,必须动静合乎礼义,才堪为臣民的表率。但在房玄龄那里,太宗除了是皇帝,更是他的主人。所以房玄龄会更多地考虑太宗作为一个人的个人感情,会对太宗表现出一种服从。
正因为如此,在太宗发火的时候,魏徵可以面不改色,房玄龄却总是会叩头流血,惶恐不止。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人的性格不一样,更是因为他们对太宗的定位和感情不一样。魏徵秉承的是儒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他认为只要自己忠心为国,就没有什么不对。而房玄龄本来就是小心谨慎的人,再加上对于太宗,始终怀有侍奉主公的心情,所以看到太宗生气,自然会觉得自己办事不力,理应赔罪。而对于太宗出于人之常情,但不符合国家制度规定的要求,房玄龄也常会满足他。
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史官所记之国史,都不让人君观看,这是为何?”
房玄龄答曰:“因为史官的记载,既不虚美又不隐恶。人主见了一定会发怒,所以不敢献给圣上看。”
太宗却说:“朕跟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希望可以自己看看国史,以后就能够改正不足、发扬优点,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
房玄龄心里明白,太宗是想看看玄武门事变到底是如何记载的,即使有谏官劝阻也没有用。果然,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请求太宗不要亲观国史,太宗没有采纳。于是,房玄龄将国史摘录了一些,呈给太宗。
太宗看过之后,对玄龄说道:“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何必写的那么隐晦呢。令史官如实写就是了。”
玄龄赶忙领旨。他明白太宗的意思,就是纂改国史,将夺权说得合情合理。虽然身为宰相,房玄龄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作为太宗的属下,他这个管家选择了忠于主人的立场。情有些时候是会战胜理的。
可是有时候,太了解反倒令房玄龄帮不上太宗的忙了。
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承乾以谋反罪被废为庶人,太宗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立魏王李泰为太子还是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当时朝中分为两派,各有所支持,但房玄龄自始至终都没有表态。不是因为房玄龄明哲保身,而是因为他十分矛盾。房玄龄明白太宗喜欢魏王泰,可是他也清楚地看到朝中的形势发展对晋王治有利,太宗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正因为对太宗,对周围的人和事都太了解,房玄龄才陷入了和太宗一样的矛盾中。他觉得劝太宗立谁都会增加太宗的困扰,所以干脆不发言。也许当时,真的能不怀个人目的、而又能同情、理解太宗的,也就只有房玄龄一个人了。
孜孜奉国的贞观大管家(2)
而太宗以及他的家人也同样不只是将房玄龄看作一个大臣。
贞观十年(636),长孙皇后生病,久治不愈。
太子承乾很是担忧母亲的身体,一日侍奉之际,偷偷建议:“母后,不如奏请父皇赦免一些罪犯或者度人入道,积些功德,也许母后的病会好转。”
“万万不可。”长孙皇后听了坚决不同意,“生死有命,非人力可以挽回。如果为善有用,我平日也不是为恶之人;如果无用,那又何必?赦免罪犯乃是国家大事,佛、道也是关系到国家政体的。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坏了国法?此念不可对你父皇提起,知道了吗?”
太子含泪点了点头。可是他还是不忍母后受到病痛的折磨,于是专门找到了房玄龄,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房玄龄明白太子的心意,于是将此意转达给了太宗。
太宗听了也很是悲痛,对房玄龄说:“皇后为朕操劳太多了啊,朕对她关心太少了。可怜承乾这孩子有这个孝心,他的建议也不是不可行啊。”
后来因为皇后的坚持,太宗没有接受承乾的意见,但此举却是发人深思的。
太子将这等家事告诉房玄龄,自然就是没有把他当成外人。也许在他的心目中,这位管家反倒比严厉的父皇更亲切。所以他不敢告诉太宗却告诉了房玄龄。而太宗对房玄龄扮演传声筒的角色也没有异议,丝毫不觉得这是介入了他们的家事,可见他们一家对于房玄龄的感情是多么特殊。
当年的六月,皇后病危。
在立政殿中,太宗拉着奄奄一息的长孙皇后那瘦弱的手,泣不成声,他这位妻子,实在为自己付出太多太多。
“陛下不要太伤心了,人总有一死。”皇后已经气若游丝。
“朕以为还有许多日子能与你一起,谁知老天如此待我们。”太宗真的很后悔,没有多照顾自己的爱妻。
“臣妾还有事想跟陛下说。”长孙皇后挣扎着想起来。
太宗轻轻扶起她,让她靠在自己身上。
“房玄龄……在陛下身边最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