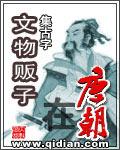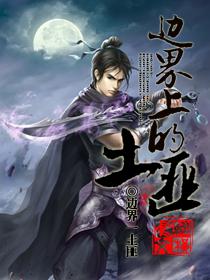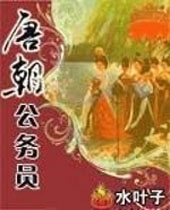唐朝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薛仁贵:生逢其时的新生代将领(3)
现在,更因李治被选为太子,使得这个问题愈加紧迫。太宗深知,九子李治性情相对温弱,李治继统,乃是权衡抉择之结果。但李治将如何继续大唐的功业?太宗并无清晰的概念。东西南北,辽东、吐蕃、突厥等等,归服的未归服的,关系都须经营。更远的,朝鲜半岛、倭国、大食等,友好还是紧张,关系皆须处理。太宗留给李治的基业太大,但唯因家业大,李治的担子十分沉重。
辽东一直未平。出兵辽东,总是迟早之事。
但当此贞观十九年(645),太宗急于把这一件事付诸行动,亦不无更隐秘一层的考虑,即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辽东,减轻以后李治的负担:最后的紧迫感!
但上一代人若企望为下一代人做事,助益注定是有限的。最根本的是李治自己要会治国。治国须人才,李治的治国之才原本不如太宗,要拓展太宗留下的大唐基业,他该比太宗更需要人才。而太宗现在能够留给李治的最有价值的财富,恐怕也莫过于人才。太宗权衡再三,把李治托付给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以李世之自爱又不乏忠心,太宗为李治拉拢他,也算费了心思。但太宗仍然不能回避一个事实:他晚年所面临的将才匮乏的问题,也将随着庞大的基业留给李治。
此时,太宗对人才的饥渴,相对于当年,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宗想起刚才薛仁贵受宠若惊又竭力按捺内心激动的情境,心里道:“薛仁贵啊薛仁贵,你只知邀功求赏,哪里明白朕的心思?”太宗一再优待推重李世,李世固然不会不明白用意何在。而真正明白太宗更深忧虑的人,恐怕只有李靖。此时若能再出一个或几个李靖,即使此行打不下辽东,太宗也大可放心回师。太宗突然很想李靖在身边,可以和李靖谈谈兵法,太宗还想对李靖说,“朕打辽东,是为自己,为大唐,为太子!”这话除了说给自己,就只能说给李靖,才有意义。或许,还可以谈谈薛仁贵。虽然,一个薛仁贵的出现,比起武德年间群雄竞出的局面,显得太过冷清和惨淡。并且,这个河东人薛仁贵,是否是一个将才?若把期望放在薛仁贵身上,薛仁贵是否有能力承担?毕竟单纯的英勇善战不等于谋略过人,更不等于就有超人的眼光、御军指挥的才能。而这些都是一个将才所必须。太宗只是期望,期望新生一代的成长。
雨过天晴,群星不知何时已布满夜高空。
太宗对星空叹息。一个帝国啊,千端万绪。从即位到即将老去,去冬霜雪刚过,今夏雨水又多,作为天子,一事刚了又有新事来,每年有每年的忧虑。
这个夜晚,有多少人思绪万千?在另一个军帐里,李世同样难以成眠,虽然李世在此前的出征之议中婉曲地投了赞成票,但是身处战事中的他,很难完全乐观。他不敢保证战争的最终结果,唐军能在多大程度上获胜?
刚才,皇上召见了一个无名小卒,李世从属下口中听来这样一个小插曲。他或许没有时间去在意这些无关大局的小事。但是现在,他不免陷入这件小插曲所激起的思绪涟漪中。当年和秦王、和他李世一起战斗过的将领们,如今都哪里去了?在孤独感日益加深的这些年里,即使豁达如李世,也无法不感叹岁月的无情。当今的天子,必定有着比他更深的感受……
思绪太乱,李世从战争的形势想到自己的孤独感,又从自己的孤独感想到不完全乐观的形势。思想纷乱中竟渐渐入了梦去,带着未能排解的担忧。
李世的担忧在次日醒来前暂且留给了周公,但战事的进展却未能超越他的担忧。安市之役持续几十天,伤亡有,战果亦有,但安市城迟迟未能攻下。战势不容乐观,太宗理智地决定结束安市之役的第一轮战斗。
战后,太宗更名北山为驻跸山。大赏军士后,七月五日,营地移往安市城东,开始再一轮战斗。
太宗一面令张亮帅海军围攻位于辽河下游、辽东半岛西北部的建安,一面令陆军继续进军安市城。他同时派人示威性地送了一副御弓给大权独揽的高丽权相泉盖苏文,希望对方不战而服。但太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期望又一次落空。
薛仁贵:生逢其时的新生代将领(4)
安市城抵抗颇为顽强,每次太宗旗帜出现,安市人便在城墙上喝倒彩。太宗大怒。而薛仁贵只是有一种迫切感,迫切要杀这帮安市人。李世提出城破之日将城中男子杀光。这一建议或许有助于平息太宗怒气,于大局却难有助益,反而更激起安市人守城决心,横竖是死!太宗命李道宗筑土山于城东南角,土山高过城墙,但土山根基不稳,未等攻城,已经倒塌,把城墙亦压崩了。压崩的城墙缺口为高丽兵所占,唐军又功亏一篑。
太宗又将士卒分成几批,轮流进攻。但是日复一日,转眼间九月来临,天气转冷,士兵疲累,粮草短缺。
太宗终是不得不抱憾班师。
正值九月,辽东已是草枯水冻。班师那天,太宗望着安市城,这座耗了几个月仍旧未能拿下的城池。萧瑟秋风中,太宗的表情有种虚无飘渺的复杂。李世顿时生出深深的遗憾,未能助天子成功的遗憾。
太宗感慨道:“朕今功未成而班师,虽有遗憾。但大唐有李世、程名振、契何力诸将,又有薛仁贵这样新秀涌现,朕亦可感安慰。朕固知百年之后,可以无忧。”
唯有经此一战,亲眼看过大唐将士力量,太宗才能安心。
十月,军返营州(今辽宁朝阳)。太宗召见薛仁贵。薛仁贵自从被太宗封为游击将军、云泉府都尉,不久又从张士贵旗下调任北门长上,成为太宗警卫部队的军官,并得到牲口和十个奴婢的赏赐。他虽是抱着求显达的美梦入了军旅,但当梦成真时,薛仁贵依然难以置信。或许他的梦本不具清晰轮廓,或许他以自己的一穷二白之身,亦根本无法期望太多。这次,他带着惶恐的快乐急急应召而来,太宗意味深长地说:“朕诸将皆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阃外之寄,是对将领的期望与信任。
推重如是!薛仁贵再度受惊,有不堪承受之感。扑通跪下,语无伦次:“陛下圣明,仁贵不才。但有忠心,必以身效死力!”
“起来!起来!”太宗道,“朕看重卿,大唐事业须卿出力,卿但兢兢进取,大唐亦必不负卿。”
太宗意甚恳切,薛仁贵受惊之际,亦不由得不感动,于是铮铮表态道:“仁贵此身,从此自属大唐。”
不久,授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依旧北门长上。右领军郎将品阶正五品上。只是终太宗之世,不见薛仁贵再显功绩。或许薛仁贵,本是太宗要留给高宗的人才,也只能是太宗留给高宗的人才。太宗的最后这几年,已经无法提供造就英雄的舞台。所幸是多年之后,薛仁贵也算是不负此时太宗所寄。
且说这年十一月,太宗车驾返至定州。十二月,太宗病痈,御步辇而行。
褚遂良对太宗说:“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尹、霍光旧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
太宗想起出发前刘洎的话,“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正不舒服,听褚遂良如此说,正好顺水推舟,于是下诏称:“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
太宗杀了刘洎。对李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震动。“原来太宗辽东之行,对内对外都是考验。”李世恍悟。
李世愈加佩服太宗的心思缜密。
托孤与考验(1)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李世上完朝,像往常一样到官衙当值,处理一些事务。午时,李世正欲归家,突然接到诏书: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为叠州(今甘肃迭部)都督。
诏书没有写明任何理由。
李世手持诏书,呆立片刻。风吹来,诏书的一角随风吹起。李世突然觉得这诏书像是一颗火种,随时会趁风势燃烧起来,将自己烧得尸骨无存。
“皇上啊皇上!”李世心中叹道。
李世没有回家,他径直从官衙出发,往叠州上任去了。
太宗听到李世已经在前往叠州路上的消息,长长舒了一口气,心中连叫了几个“李靖”。
太宗何以叫“李靖”?
几个月前,太宗问李靖道:“卿曾说李世懂得兵法,天长日久还可以任用他吗?如果不是我亲自驾驭控制他,恐怕就不好使用了。将来太子李治即位后,怎么控制他呢?”
李靖对道:“为陛下计,不如由陛下贬黜李世,将来再由太子起用他。那么他一定会感恩图报。这在情理上也没有什么妨碍!”
太宗道:“好,朕没有什么疑虑了。”
这是诏书的由来。对李世的这个安排,真的是由李靖提出来的?也许在问李靖时,太宗已经有这种想法。也许这就是李靖的主意,被太宗采纳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到这个时候,太宗、李靖、李世,互相之间的了解,使得他们之间玩心计也是透明的。
这个时候,在东宫,太子李治也舒出了一口气。他对父皇的话一直心怀忐忑,父皇说:“李世才智有余,但你对他无恩,恐怕不能怀服。我现在把他贬黜出去,如果他接到贬黜诏书就去上任,等我死后,你就把他召回来,用他做仆射,要重用他;如果他徘徊顾望,不肯离京,以后你就把他杀掉。”
“可是父皇,李世是大唐的功臣。”
“正因为是功臣,你才必须驾驭他。他若顺从,自然是大唐之福。他若不好驾驭——”太宗叹一口气,“就算是天命吧!”
太子惶恐点头。他不希望李世死。其实,太宗也不希望。
李世没有给太宗父子任何困扰,他利利落落赶赴叠州上任去了。太宗不得不承认,李世对天命人事看得很通达。太宗有些后悔让他在并州守了那么多年。
几天后,太宗病重。太子昼夜不离侧,连日忧心不食,头发日渐变白。太宗不免心疼,道:“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说话间,不觉泪流。
眼看病情日重,太宗知道不能好转,因召长孙无忌入含风殿。太宗躺在床上,长孙无忌跪在床前,太宗伸出一只手,颤抖着。长孙无忌不胜悲伤,泣涕不止。太宗竟半天不能一语,只得令长孙无忌出去。
过一两日,复召长孙无忌及褚遂良入卧内。太子、长孙无忌、褚遂良并排跪在床前。太宗平静好多,缓缓道:“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
“陛下!”长孙无忌悲泣,“陛下放心,我等必将尽心辅佐太子。”
太宗已经没有力气点头,他的目光停留在长孙无忌脸上,又转移到褚遂良脸上,像要把他们看个通透。
终于,太宗的目光转向太子,道:“有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太子只是连连点头,泣不成声。
“褚爱卿,”太宗又谓褚遂良道,“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
“有遂良在一日,必不让谗人害长孙大人。”褚遂良无限悲凄。
“嗯,嗯。有爱卿这句话,朕放心了。”太宗用尽力气,提高了声音说:“褚爱卿!”
“臣在!”褚遂良移动膝盖,靠近一些。
“为朕草诏,传位太子!”
“臣领旨!”褚遂良深深俯拜,泪光闪烁。
太宗示意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出去,独留太子。太宗握住太子的手,道:“我儿啊,为父将能留给你的,都留给你了。”
托孤与考验(2)new
太子泪如雨下,不能一语。
少时,褚遂良草诏完毕,复进卧内,念与太宗听。
安静的寝殿回响着褚遂良颤抖的声音。
太宗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父皇!”“皇上!”一时间,整个寝殿被悲凄所笼罩。六宫嫔妃,皇子公主,纷纷赶来,悲声云集。太子抱住长孙无忌脖颈,号恸几欲气绝。长孙无忌一边轻拍太子肩背,一边吩咐处理后事,令妥善处置,不得使内外生乱。
太子痛哭不已。长孙无忌道:“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太子惊觉。
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甲戌朔,李治(庙号高宗)即位,赦天下。初四日,下诏以叠州都督李世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因“世”字犯太宗名讳,从此被世人称为“李”。赶赴叠州的李此时正好到了洛阳。
不久,又任命李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要他回京担任宰相之职。李回返京城,大殿之上,已是新天子。
九月,乙卯,以李为左仆射。
见证后宫天子气(1)new
高宗永徽元年(650)九月,李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李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永徽四年(653)二月,以开府仪同三司李为司空。
在高宗朝中,专掌朝政的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回朝后,一贯行事低调。李说:“李本是武将。朝堂上之事,李不应过多言语。”
“所谓臣子,本是食禄尽职。做好分内事,也可无愧于先帝之托了。”李夫人道。
李摇摇头。他其实不敢说无愧于先帝之托。他只是明白,即使太宗有意于笼络所有的力量,但是事到如今,长孙无忌其实和李所走的路不同。所以在如今的格局中,必须是李保持低调。
但是有一天,李上完早朝,回到家里。冷不丁说了一句:“恐怕迟早变数生。”
李夫人听得,诧异道:“夫君何以言此?”
“嗯?”李挥手道:“没事,没事!”
“夫君说变数生,可是朝廷有什么动向?”
“我也就随口的话。”李道,“如今不是朝野安宁么?”
李夫人看李不愿意说下去,也就作罢了。
几天后,朝廷内外,街头巷尾,客店酒肆里,传议着一个共同的话题:王皇后杀了武昭仪的女儿。
这日,李一回到家里,就听到几个小丫头聚在一起,窃窃议论着宫中武昭仪女婴的死事。李咳一声,皱眉道:“小丫头不可妄议宫事。”
几个小丫头一哄而散。
李径直进房,心绪有些纷乱。倒不是自己跟事情有什么关系。只是人在朝中,难免受朝野风云的影响。听到到处都在议论帝王家丑事,未免不舒服。
李夫人看李回来,不发一语。知他心绪不好,亦知趣噤声。
直到晚上,灯光摇曳中,李才禁不住自己跟夫人道:“发生此事,皇上恐怕有废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