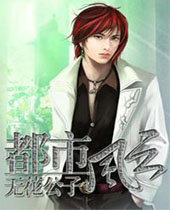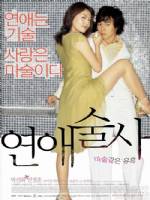景山的晚风-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宁锦大捷
要说到袁崇焕的冤案,就须追述一下天启朝以及崇祯帝即位前后的辽东形势和人事变动。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突然率兵反击明军。当时,辽东经略熊廷弼(天启元年六月复出任此职)和广宁巡抚王化贞(天启元年五月由参议升任)关系不和。王化贞凭着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等人的支持,不听熊廷弼调度,力主全线反击,荡平建州,并先后几次组织军事行动,但都劳而无功。努尔哈赤却在精心准备后打了王化贞一个措手不及。
努尔哈赤此次西击,先攻下西平堡,然后击败明军援军,占领了重镇广宁及远近40余座城镇。熊廷弼、王化贞竟率军全线溃退,弃关外之地而不顾。关西蒙古人喀尔沁诸部乘机占领关外5城72堡。
熊廷弼、王化贞被下狱论罪。后来魏忠贤利用熊廷弼,大杀东林党人。最后熊廷弼被枭首九边。直到崇祯初韩鑛为相时,熊廷弼的儿子还向朝廷吵着要他父亲的脑袋,以便回老家安葬。
熊廷弼被逮之后,王在晋任辽东经略。当时山海关外之地,尽被蒙古喀尔沁诸部控制,经略王在晋和蓟辽总督王象乾主张利用这些蒙古人守关外之地,作为官军与努尔哈赤之间的缓冲带。为此,他们请朝廷发给蒙古人粮饷,予以正式确认。同时,他们又主张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修筑重城,驻兵4万,等等。
这时,有位名叫袁崇焕的宁前兵备佥事提出了不同意见,显示出他独到的军事战略眼光。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一说祖籍东莞,至袁崇焕时已迁居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曾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被监察御史侯恂推荐到兵部,破格担任职方主事。侯恂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朝宗)的父亲,有东林色彩,后在镇压明末农民军的战争中被委以重任,提拔过名将左良玉,兵败后曾被逮捕入狱,后获释。后世对此人争议颇大,说法很多。不过在天启初,侯恂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东林官员。
袁崇焕能破格入兵部任职方主事,除侯恂的荐举外,可能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他与韩鑛的关系。袁崇焕考中进士时,主考官就是韩鑛,当时他的官职是礼部右侍郎。因此,韩鑛与袁崇焕之间,有“座主”、“门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当时官场上是一种很重要的人情渠道。至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被破格调入兵部时,韩鑛正是在内阁阁臣的位置上,而且内阁首辅也是东林党人叶向高。
不过,袁崇焕能入兵部,不仅是因为有这层关系,而且更与他本人的条件有关。袁崇焕虽从小就习举子业,却同时对武略很有兴趣,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本朝的习惯是重文轻武,武人在朝廷中,很难谋得与文官相等的地位,而社会的精英,也很少去走武人这一发展道路。话又说回来,即使想在武略方面有发展,也必须先通过科举谋得文官的资格。在当时,像兵部尚书、经略、巡抚之类率兵带将的高级职位,全由文官担任。就是说,文官做到一定时候,有可能统率武将,而武将却不太可能去统辖文官。当然,这种体制也有问题,因为文官去管军事,虽能约束武将,但能精通兵书同时又武略超群的毕竟是少数,一旦选人不当,像万历末的杨镐那样,就会误大事。因此,像袁崇焕这样既长期熟习兵书韬略,又关注边疆政治的文官,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脱颖而出,也不算奇怪。
袁崇焕的胆子也够大的。他在王化贞广宁兵溃后,曾一人单骑走遍山海关内外,考察边情。当朝廷上下无不谈辽事而色变时,袁崇焕却在兵部扬言:
“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卒守此。”
意思就是只要给我兵马粮草,我一人就能守住山海关。朝廷正愁没有这样的人,于是便再次破格,给他一个监军佥事的官职,把他推上山海关前线。袁崇焕赴山海关后,没过多久便得了个“铁胆”的称号。辽东经略王在晋也较倚重他,奏请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正式负责防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和前卫屯二地。这在当时就是明军的最前线了。袁崇焕力主在此筑城,作为山海关外的屏障,而王在晋却提出收缩防线,在山海关外不远的八里铺筑城,两人发生了矛盾。
袁崇焕便越级向首辅叶向高禀告,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袁崇焕的不简单。叶向高接到报告后,也拿不定主意,便与另一位阁臣孙承宗商量。
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榜眼,天启帝即位后,以左庶子充日讲官,据说深得天启帝这位少年皇帝的赏识。天启二年(1622)初广宁失守后,辽东形势危急,孙承宗因平素通晓兵法,而被破格由礼部右侍郎提升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这在本朝历史上还没有多少先例。孙承宗的入阁,是由东林党魁、御史左光斗提议的,叶向高对此积极支持,所以孙承宗一般被认为是东林中的温和派人物或者是东林党的同情者。
孙承宗看到这种情形,便向朝廷提出自己亲自赴山海关,了解详情后再作定夺。孙承宗到达前线后,明确支持袁崇焕的计划。到了此年八月,孙承宗更是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经略蓟辽,这在本朝也是少见的。
孙承宗在辽东筑城、练兵、屯田、造铠甲,并进行了一系列人员调整。天启五年(1625),已被提拔为山东副使、山东右参政的袁崇焕,以宁远为据点,向东开拓疆域2000余里,分遣将领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等,筑城设防,一时形势颇为有利。不幸的是,此年十月,孙承宗因遭到多方压力而辞职。魏忠贤乘机以其党羽兵部尚书高第取而代之,出任经略。
这位高第,虽是兵部尚书,但素无胆略。据说高第得知被任命为经略时,吓得直哭。他到前线后,认为山海关的战线太长,不易据守,便悍然下令全线退缩,撤入山海关。袁崇焕坚决反对,他说:
“兵法有进无退。锦州、右屯(原广宁右屯卫)动摇,则宁远、前卫必将动摇,山海关内也就失去了保障。”
袁崇焕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他的主张就是山海关外应有纵深防御,避免山海关直接受敌攻击。而这位高第大概是过于害怕,希望把全部力量收缩在山海关一线,孤注一掷。这与前面王在晋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样的战略有两大问题:一是山海关要直接承受敌方的攻击,一旦关破,京畿便无险可守,敌军的铁骑片刻就能到北京城下。二是即使山海关守得住,敌方也能绕过山海关,在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上寻找攻击点,切入山海关之里的京畿之地。由于山海关外没有纵深防御,明朝的军队就无法对敌军进行堵截,破坏其战略实施。后来的情况也确实证实了这种推测。
可高第不管这些。他本来就不懂,加上胆子又小,所以要让他理解、接受袁崇焕的计划,真是太难为他了。因此,他不仅要撤掉锦州、右屯防线,而且要把袁崇焕的宁远、前卫一并撤入关中。袁崇焕急得都要跳起来,坚决反对。他说:
“我是宁前道,职守在此,死也要在此。我坚决不会撤退!”
遇到这种犟脾气的“铁胆”人物,高第也没有办法,所以宁远、前卫两城仍由袁崇焕驻守,没有撤退。朝廷为安抚袁崇焕,还提他做了山东按察使。但锦州一带的防守据点,如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塔山、杏山等,全部撤守,军民尽撤入关,哭声震天,米粟辎重被委弃者不计其数,明军实力大损。
依高第当时的想法,凭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前卫两座孤城,大概也挡不住努尔哈赤的铁骑。你袁崇焕既然想逞能,不肯撤入关内,那就让你吃点苦头,到时候你就会乖乖听话了。没想到,袁崇焕竟然依靠孤城,立下了大功!
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乘明军全线撤退之际,率兵西渡辽河,直逼宁远。袁崇焕得到谍报后,迅速召集将士,誓死守城;书写血书,激励士气;传檄山海关、前屯,凡自宁远城逃出者,全部斩杀,以肃军纪。全城人心始稳,誓死守城。
当时努尔哈赤所率军队,超过10,而袁崇焕在宁远的守军,仅万人,双方实力悬殊。袁崇焕在努尔哈赤围城之初,故意放弃外城,把敌军放进来。后金军队不知是计,便蜂拥而入,攻打内城。袁崇焕立即下令发射刚刚引进的西洋巨炮,配之以滚石矢木,后金军队吃了大亏,努尔哈赤本人也受了重伤,只得全线撤退。这就是“宁远大捷”。
当时的朝廷上下,谁也没想到袁崇焕能打这样一个大胜仗。袁崇焕一下子名声大震,先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不久又被任命为辽东巡抚。而那位经略高第,因拥兵不救、折辱诸将而遭交章弹劾,被赶下了台。朝廷上下最痛恨的是高第在宁远激战时拥兵观望,不予救援。不过,在高第看来,他是不便去救。他本来就不同意袁崇焕守宁远孤城,现在仗打了起来,如果袁崇焕打胜了,不是证明他自己原先的战略是错误的吗?对这种打胜了却只能证明自己是错误的仗,像高第这样的人能去拼命吗?
高第之后,王之臣出任经略。王之臣与袁崇焕意见不合,朝廷为调和关系,干脆把辽东的防务一分为二,山海关内由王之臣负责,山海关外由袁崇焕负责。这种做法不免滑稽,因为辽东防务本是一体,现在却被活生生割裂。对这种划分,袁崇焕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或猜忌;同时王之臣也不会满意,因为他职为辽东经略,本应全线统筹,而现在却只让他负责关内。朝廷的原意是调和两人关系,现在反而弄巧成拙。
在宁远大捷之后,形势一度对明朝有利。此年的八月,努尔哈赤因在宁远被击重伤,久治不愈而亡。努尔哈赤临终前曾对诸贝勒说:
“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何单单宁远一城却没有攻下?!”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接位。皇太极当时面临许多困难。自己以第八子身份接位,并无多大合法性,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统辖2旗,实力最强。而且,努尔哈赤临终前曾明确告诫,要八贝勒共同治国。因此,当时皇太极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另外,宁远惨败,加之辖区内的长期经济衰败,皇太极也不太想在即位之初,就与明朝大动干戈。更重要的是,皇太极想借正面缓和之机,压服朝鲜,以解后顾之忧。
天启七年(1627)初,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互派使者,互换书信,进行商谈。皇太极在信中列述了“七大恨”,申诉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的冤屈,表示愿重修两国之好,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就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袁崇焕则要皇太极退出开战以来侵占的城池,归还被俘的军民等等,也就是要后金恢复到从前的地位。双方的筹码不一,很难达成一致。
就在和议进行之时,双方都采取了一些举措,各打着自己的算盘。
皇太极乘议和之机,出兵朝鲜,并攻击据守在皮岛(今朝鲜椴岛)的明朝将领毛文龙。朝鲜、皮岛同时告急,请求朝廷支援。
而此时的袁崇焕,正忙着布防筑城。当时经略王之臣已被罢职,经略一职空缺,由袁崇焕以巡抚的身份全面统辖辽东军务。袁崇焕掌权后,与总兵赵率教巡历锦州、大小凌河3城,并重新设防。正在此时,朝鲜告急,袁崇焕急命部将增援,而朝鲜却因敌不住后金军队的猛攻,已正式投降。朝鲜的投降,使皇太极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使明军失去了从东面夹攻后金的有生力量。
天启七年(1627)五月,已取得朝鲜之战胜利的皇太极,率兵向袁崇焕反扑,说是要报努尔哈赤之仇。在其攻势之下,大、小凌河守城之卒溃逃,皇太极乘势围住锦州。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遣使请和。袁崇焕急派祖大寿率精兵4000人,绕到敌后,又派水军东出,试图从背后发起攻击。援兵才出发,而敌兵已至宁远城下。袁崇焕故伎重演,用重炮打击攻城之敌。与袁崇焕不和的满桂,也率兵来增援,合击敌军。后金军队伤亡惨重,城外濠沟尸积如山,不得已而撤出宁远,集中力量攻打锦州。锦州守城之兵奋力抵抗,外部援军也纷纷赶到,后金军队便全面撤退,临撤时,毁掉了大、小凌河两座城池。这就是有名的“宁锦大捷”。
宁锦大捷,对皇太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明朝来说,似乎是一个转机。不幸的是,朝廷内部的矛盾再次影响到了辽东局势。
宁锦大捷后,袁崇焕被魏忠贤手下的党羽交章弹劾。他们说袁崇焕没有及时救锦州,毛文龙遭后金袭击,也是因为袁崇焕与后金议和引起的,等等。袁崇焕当然受不了,愤然乞请致仕归里。朝廷顺水推舟,同意袁崇焕之请,而让王之臣复出,指挥辽东军事。
不过,尽管袁崇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宁锦大捷还是要论功行赏的。朝廷文武,因宁锦大捷而被增秩赐荫者不下百人。魏忠贤的从孙魏鹏翼虽尚在襁褓之中,却也因宁锦大捷而被封了安平伯。至于袁崇焕,魏忠贤也格外加恩,给他增了一秩。对此,就连魏忠贤的心腹尚书霍维华也觉得太少了一点,因为毕竟是袁崇焕辛辛苦苦打了宁锦大捷,但魏忠贤对这种想法断然拒绝。后来梁启超读到这段历史,曾大发感慨说:
“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
其实,梁任公只说对了部分。奸臣在内,大概也希望名将能立功于外。魏忠贤在朝廷大杀东林党人时,东林党的同情者孙承宗、袁崇焕则在拼着命守住辽东。魏忠贤当然希望他们能立功于外,只不过功劳要算在或大部分算在自己这位“九千岁”头上,能为自己所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行了。另外,名将不能立功于外,并不一定要有奸臣在内。袁崇焕这位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