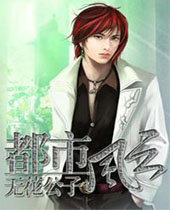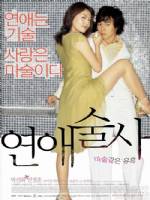景山的晚风-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以诸皇子婚娶为由,要求从太仓银库(国库)取用白银2400万两。这对于当时的朝廷财政而言,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户部自然难以满足。万历帝见此,竟尽遣宦官到各省核查积银,颇有点不刮尽天下财物决不罢休的架势。此前,万历帝向全国派遣税监、矿使,搜括财物的做法,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至此,他竟又变本加厉,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动荡。更令人不解的是,万历帝把这些钱财敛于内廷,不肯与朝廷分享丝毫。对朝廷的财政危机,他简直就是视而不见,似乎与他毫无关系!
皇帝既然如此,大臣们也自然要为自己的生计考虑。万历后期的吏治,败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时期的各级官员,似乎很少有不谋私利的。有些官员所积下的巨额财富,令人瞠目结舌,很难与他们每年几十两或至多几百两的俸禄联系起来。像出身贫寒且在当时(甚至在今天)被认为是清廉之至的东林党魁顾宪成,在其兄弟分家时,尚获得数千亩的田产。世风日下的程度由此可见。既然皇帝、大臣们的日子是如此好过,那么,天下百姓日子的难过,也就可想而知了。
皇帝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
万历皇帝仍然是我行我素。除了拼命用钱同时拼命捞钱之外,他似乎对朝政越来越没有兴趣,借口当然还是“圣体违和”。可仍有一些大臣,不思体恤,不知深浅,竟然还喋喋不休,说些皇帝绝不想再听的事情。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月,给事中赵德完就给万历帝上了一疏,煞有其事地说什么郑贵妃阴谋在多病的皇后驾崩后,自立为后,并立其子常洵为太子等等。万历帝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件事,自然不免龙颜大怒,命下诏狱,廷杖一百,开除官职,永不录用。
大概是群臣十余年的不懈斗争,再加上赵德完挨的100大棍,万历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十月进行了正式册封。皇长子常洛最终被立为了皇太子,同日被封的还有福王常洵(封地洛阳)、瑞王常浩(封地汉中)、慧王常润(封地汉中)、桂王常瀛(封地衡州)。既然是册封这样的盛典,而且还要成婚,万历帝自然不会过分精打细算,他早就提前向户部提出了2400万两白银的预算作为开支。可惜户部拿不出这笔款项,所以最后还算节俭,只用了1000多万。为这事皇帝还对户部有点意见,并派宦官到各地查账,看看是否真的是没钱。大概是万历帝对户部官员的敛财能力不太满意,所以他不得不加派税监、矿使分赴各地,开辟财源,弄得十分不成体统。
或许是万历帝看透了朝廷这帮人物,而一心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多为子孙(尤其是他最宠爱的福王)谋点产业,免得在他死后受苦。没想到他的这种做法,恰恰是动摇了大明朝的根基,最后祸及子孙。那位受他百般宠爱的福王常洵,后来在洛阳成为李自成的刀下鬼时,不知能否想通其中的因果关系。
伤透了心的万历帝,在此以后更是心灰意懒,不理朝政。就连朝廷最重要的人事安排,他也懒得过问。而部院主管大臣之类的任命,又非要皇帝钦命不可,否则,也只能空缺。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大学士沈鲤等就向皇帝诉苦说,吏部尚书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则尚书、侍郎全缺,礼部仅存一侍郎,户部也只有一位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31位,竟缺了24个。如果去掉那些在职不谋事的,几乎就是无人理政。对此,万历帝仍是不闻不问。到最后几年,像内阁这样最重要的机构,竟也只有首辅方从哲一人,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朝廷,怎么还能指望它有什么作为。
朝廷的统治能力下降,还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朝廷官员之间的派性斗争至此也越演越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东林党是万历后期党争的主角。在张居正统治期间,后来成为东林党魁的青年官员邹元标,就上疏攻击张居正,说他不丁父忧,名为夺情,实则贪位。张居正以后,又有一批年轻官员,像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等,在朝中互相呼应,干预朝政,并小成气候。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中,顾宪成等人操纵吏部,罢免了一大批与内阁关系密切的官员,激化了矛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此后,朝中大权被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等掌握,人称“浙党”。但顾宪成等人也不甘寂寞。他们以无锡东林书院为中心,以讲学求道为名,裁量人物,讽议朝政,以天下清流自居,名动天下。顾宪成之流及其后继者,后来被魏忠贤扣上了“东林党”这一大名。
起初,东林党人大多尚能称得上正人君子。他们希望重建道德权威,并通过道德手段解决当时的一系列危机。这种激进的道德主义旗帜,加上东林党人本身的人格魅力,在开始时犹如一阵新风,给人带来了希望。但道德的力量,并非无限,它需要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与之相配套。而且,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有双重性格,在道德和利益之间摇摆不定。只有实现了相对的利益,才能谈得上道德。除了极少数圣人,绝对的道德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道德还会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党同伐异的武器。许多人借道德之名,谋自身利益,并以道德去约束别人,放纵自己。至于他们自己到底相信多少,又去做了多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开始的东林党人,就是一些绝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但当他们的组织一旦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时,其性质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东林党的许多行为,实际上就是党争行为,其动机也未必像他们自己当初所标榜的那样堂皇,更多时候党派利益要显得重要得多。他们在野时,对当权者样样看不顺眼,动辄口诛笔伐;而当他们得势时,也同样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治国手段来。更严重的是,东林党到后来虽声势浩大,实则鱼目混珠,不仅招忌,而且也为其对手提供了不少口实。后来的血光之灾,其实已于此时埋下了因果。
东林的主要对手是浙党,以及依附于浙党的齐党、楚党、宣党。两派在一切问题上似乎都要针锋相对,并互相倾轧。浙党沈一贯任首辅时,东林虽居下风,但顾宪成等人仍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影响朝廷,甚至出位论政。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东林党人借京察之名,联合吏部尚书孙丕扬,逐斥浙党诸人,掌握了主动。但不久浙党方从哲入阁,浙党又进入反攻状态。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时,方从哲已居首辅,浙党势力进一步加强,东林党人被纷纷罢免。虽然不久后东林党人又在天启初期占了绝对优势,可是,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屠刀,很快就要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了。
大明朝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辽东守战(1)
尽管逼死崇祯帝的是李自成,但最终建立起新王朝的是满族人,即女真人。
在明王朝相当长的时期内,外族的威胁主要来自蒙古。辽东的满族还基本上构不成威胁。出乎意料的是,恰恰是辽东的这一不起眼的民族,最终入主了中原,在明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强大的清帝国。
满族的兴起和强大,正是在万历朝。万历朝在辽东问题上的严重失策,以及万历朝中央政权的式微,是导致后来满族入主中原的直接原因。
洪武初期,明朝不断用兵东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以辽阳(今辽阳市)、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城)、开元(今开元县城北之老城镇)为中心,下辖卫所,建立起以军统政、军政合一的体制。永乐年间,明朝又在黑龙江西来支流亨滚河(今在俄罗斯境内,名阿姆贡河)口对面的奴尔干,设立奴尔干都司,以镇抚女真等少数民族各部,护送朝贡。但至宣德(1426…1435)以后,奴尔干都司已名存实亡。明朝在女真各部也广设羁縻卫所,授其头人、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职,由其各统其部,分而治之,互相牵制。
明廷在东北的做法,一方面是想借适度的军威保持对女真的弹压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授以官衔、给予贸易优惠(互市)等恩惠手段,来笼络住女真各部的首领,并由此间接控制住其所属各部。这一统治模式的关键,在于能否控制住女真首领。每年的冬天,明朝官军往往借“烧荒”的名义,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各部首领,赏赐各种物品,让他们在感受浩荡皇恩的同时,诚心诚意地替天朝出力,护边安疆。不难看出,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能否有效维持,一方面取决于朝廷派驻东北的长官能否熟练而有效地行使这套驾驭之术,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女真部落能否长期安于现状,有没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因此,其基础是十分脆弱的。
至万历年间,这两个方面恰恰都出现了问题。长期经营东北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举措屡屡失当。而此时的女真族,也正好出了个野心勃勃、才华出众的努尔哈赤。
李成梁,长期任辽东总兵一职,替朝廷经营东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东北王”。辽东的财政,他几乎完全垄断。军赀、马价、盐课、市赏之类,也由他一人说了算。其中到底有多少入了私囊,更是无人说得清。全辽东的商民之利,他也尽笼入己。由于经济实力雄厚,他就有条件用重金结交朝廷要人权臣,礼送得重,交情自然就深。那些要人权臣,便个个夸他好。就连万历皇帝,也对他另眼相待。他的儿子个个得以封官,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都是总兵官,其他如李如梓、李如桂、李如梧、李如楠也官封参将,可谓是一门虎将。他的部将,也多是私人亲信。
在辽东,李成梁几乎建起了一个独立王国。辽东总兵这个职位,好像就是专为他设置的。一旦换了别人,就难以胜任。如在万历十九(1591)年至万历二十九(1601)年,李成梁一度被调离此职,但其影响力仍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于他的继任者根本无法真正行使职权。十年之中,辽东换了八帅。无奈之中,朝廷大概也看出了辽东问题的症结,认识到了李成梁在东北的法力,加上其子李如松当时又是朝鲜战场上的主帅之一,便不得不又在万历二十九年,干脆重新任命他为辽东总兵。当时的李成梁,已是76岁的高龄了。现在看来,明廷在辽东的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使辽东的局面过分依赖于一人。万历时的辽东,可以说是成也李成梁,败也李成梁。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女真苏克素护部的宁古塔穆昆。其祖父名叫场(觉昌安)、父亲名他失(或译作塔失、塔克世),虽不是显赫的氏族贵族,但也大概是指挥使一级的头目。努尔哈赤10岁丧母,因受继母虐待,19岁那年(万历五年,1577)就分居另过,自立门户。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带兵进剿建州右卫阿台部时,竟误杀了当时与朝廷关系不错的叫场和他失父子两人。一下子失去了祖父、父亲两位亲人的努尔哈赤,自然是悲痛欲绝。或许是出于内疚,李成梁父子此后一直比较偏袒努尔哈赤。在善后处理中,努尔哈赤得到了明朝的敕书20道、马20匹,同时世袭其祖父的头衔,被承认是建州左卫的头目之一。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到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最终完成了对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并一跃成为东北最为强大的女真领袖之一。
对努尔哈赤的崛起及其威胁,明朝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朝廷明显受到辽东前线官员的误导。对努尔哈赤,李成梁先是扶持、纵容。当其崛起后,李成梁又产生畏惧之感,不敢采取断然措施,甚至还梦想借其力量安定女真,以致坐失良机。二是努尔哈赤也对朝廷极表“忠顺”,绝不得罪朝廷,骗得了信任。到万历十七年(1589),朝廷竟授予努尔哈赤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一职。万历十八年(1590),努尔哈赤第一次进京朝贡。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廷加爵努尔哈赤,授龙虎将军。万历二十五年(1597),努尔哈赤第三次到北京朝贡。
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后,开始了对其他女真各部的吞并战争。当时的形势也对其十分有利。在李成梁离开辽东的十年中,辽东主帅竟先后换了八次,根本无法对东北进行有效控制。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央朝政的混乱和懈怠等等,也使得朝廷根本无暇顾及东北。到万历三十年(1602)后,朝廷已开始逐步意识到了努尔哈赤的威胁,但此时的努尔哈赤,已是尾大不调了。
当熊廷弼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任辽东经略时,已明显感到了努尔哈赤的威胁,而且认为这种威胁不可能在短时间解除。因此,他主张朝廷与努尔哈赤进行谈判,必要时可做出一些让步,以争取时间加强辽东防务。这在当时不失是可行之策,但对于许多住在北京的官员们来说,却绝对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熊廷弼作为堂堂辽东经略,竟然要与努尔哈赤妥协,天朝颜面何在!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不仅熊廷弼的计划被否决,连熊廷弼本人也被召回。他的继任者便对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强硬对策,试图予以压服。
但这时的努尔哈赤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恭顺了。他于万历四十四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老城)即汗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他以“七大恨”誓师讨明,出兵攻占明军在东北的重镇抚顺,并击败其援军,明军损失惨重。
至此,朝廷才如大梦方醒,仓促应战。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辽东守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