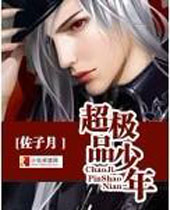极品男保姆-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两头儿地和嫂子快活,你不知道压抑的味儿啊。”
我笑:“没错儿,昨夜我还阴阳大调合呢。”
“可是我不行啊哥,我一出去就是半年,少的也得三个月啊。几个月之前,我看了一篇关于民工性压抑的文章,说性压抑可能导致性功能障碍。我怕呀,就找了一个小姐,结果,发现自己真的就不行了,那女人脱光半天了,我半天没硬起来,等硬起来了,半天没找着门,找着门儿了,半天没敢动,动了半天又没感觉,等有感觉了,忽一下就败了,总共结束没有两分钟,而且,那根筋儿还抽抽着疼,这家伙儿我信了,性这东西就象草种子,压个三层五层的土它能拱出来,要是一直压,非他娘的捂死下边不可,要经常练练。”
“行行,我敬你一杯,总结得不错。”我兴趣勃勃了,起给志远倒酒。
“别霉我了,”志远伸胳膊接酒,“就这那女人还笑话我呢,说,你老婆不喜欢你早泄,干我们这行的最喜欢了,多快多省事儿啊。唉,真他娘的悲哀啊。”
“哈哈……从那以后你就经常操练了?”
“是啊。直到染上性病。不过,我以毒攻毒,这会儿总算重振雄风了。”志远笑了一下,成分象酒,甲醛乙醇的,成分复杂。
“你觉得是让那玩意儿正常地坚挺重要还是保持身心俱净重要?”我盯着志远,不是我高尚,我开始反思了我。
“少给难民装高尚,反正我们也是没办法。知道吗哥,更多的打工者更可怜,有时一年也不能回家一趟,又不舍得出钱嫖嫖,性压抑就更厉害了,有一个员工,他说他因为这个已经得上抑郁症了,多少天都不硬一回。”
性压抑啊性压抑,看来,这真是很好的小说题材呢!这真是去北京的最好的理由呢。我,心动了。
“那你回来不完了?天天背床睡。”
“回来?你一个月开给我两千块钱的工资啊?”志远讽刺加得意。
“这么说,作为打工族,想金钱肉体双丰收是不可能的喽?”
“是啊,哪里有民工哪里就有性压抑,你可以去调查啊。哥,我不是说了吗,你好歹也是个作家,为咱民工写写呗。”
我呼呼倒了一杯酒,兴奋地冲志远举杯:“好!干!”
志远愣了一下:“咦,你疯了?从来没见你主动给人碰杯啊?”
“我这叫兔子咬人狗跳墙!”我再次冲志远举杯。
志远于是就和我碰,狠得把我杯子里的酒都撞出来了。
放下酒杯,起身,扭脸,窗外,阴天,远处,平时需要仰视的城墙竟然矮了好多,心不顿生脚踏北京天安门城楼的豪迈感觉——
我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我在三楼喝酒、绝对没站在二楼站的缘故。
晕呼呼慢悠悠地回家。
三分醉意下看古城老街最有味道。我喜欢这座老城。
会写两笔的人没有不喜欢呆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地方的。就象酒鬼,情愿离酒厂近点儿。如果不是因为小语,我想,我一辈子也许都不会有离开它的念头。我,特别喜欢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象征的地方。比如,这里的城墙象征男人;城河象征女人;再比如;城墙上风化的老式青砖象征历史,而青砖上爬过的各种虫子则象征我等众生。还有的象征我看不懂,比如那棵千年黑槐树。
天阴成一汪水,空气中好象漂满了各种透明的细白芽芽儿。老房子和青石板,倒是苍老了许多。
两个女孩儿皮鞋答答地照面走来,十几岁而已。擦身之际,我听见一妞儿对另一妞儿说:我没事儿好舔牙。另一妞儿就嘿儿嘿儿地笑。
我也笑了,以雷锋的口吻在心里说:傻乖乖,你那是身上缺维生素了。
回到家,老妈正坐在院子里读圣经,神情专注,好象耶稣他老人家正坐她对面授课一样。老妈心地善良,也很聪明,虽是文盲,但做了十年教徒,一本圣经已能通读了。她说,她只上过四天学,到现在唯一能记得的当时课本的内容是:王二小,不洗脸,不洗手,鼻涕抹到两袖口。母亲是好学的,尽管姥姥已经去世多年,但看到我看书她还会说:唉,都怨你姥娘,小时候不叫我上学,看看你们,看看书多好。其实她老人家不知道,我看的书大多是可以为我提多稿费的流行杂志,并不是什么高雅之举。
“感谢主,你回来了乖。”老妈摘下老花镜,站起来,“锅里还给你留着汤,熬得好喝得很,我给你端去吧?”
“我吃饱了,娘。”我感激而温暖地应着,要是个外国人,我肯定会加上一句“谢谢你”。进了卧室,我觉得我是以电影里的那种英雄中枪慢慢倒地的样子倒在床上的,然后,双手一伸,拽了一床叠好的被子入怀,软如人体,头一勾,脖子一弯,脸就贴了上去,心里的欲望随之拱动:小语不是头晕吗……不如躺下来,让我抱着小睡好了……
身上一暖,——老妈给盖上了另一条被子……
4月10
早饭后,老爸老妈回老家看我爷爷去了。
“晌午你得做饭,我得忙。”妻子在卧室里大声训话。
“小意思嘛。”我嘴里轻松心里烦地应着。
“看我这件褂子好看不?”妻子从卧室里出来,在我面前转了一圈儿,胸前大红,背后大紫。我尽可能从艺术高度又审美一遍,很诚实地说:“一般。象个农村妇女穿的。”
妻子又扭了一下身子:“胡扯,咋会象个农村妇女呢?”
我笑:“当然,这会儿是穿到你身上了。”
“去,我觉得挺靓的。”
我再笑:“穿玻璃不比这亮啊?”
妻子带着儿子走了,我随后又去了办公室——总觉得只有登上QQ才会离小语更近。
上了QQ,小语的那个企鹅头像还是灰灰的,象一粒泡得饱饱的种籽,但迟迟不发芽儿。没给我回留言,看来她一直没上网。真后悔当初没腆着脸要她的手机号。
当然,我还有其他的正事儿,我在“google”,这个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里输入了“民工性压抑”这几个字--
乖乖,就象闹蝗灾一样,一下子竟然蹦出了几千条与之相关的新闻!认真读了几条,其中一条说,光在北京的海淀区,强奸案有40%多是外地的民工干的。天,比志远说的还严重呢,看样子真是大有文章!
手机响。来电是“010”的开头!我的心猛一跳,赶紧接听——
“你丫的还是个男人嘛,人家急得麻爪儿,你还是小姑娘儿入洞房死不吭声!”是陈述个混蛋,一嘴的北京味儿,学得真快。
“快了,办事就象砸核桃懂吗,力道不到它不开呀。”
“我肠子都急青了知道吗您?好了哥,看在对桌办公的份儿上,明天上午十二点之前给我回话,我丫的不能再等了,回见,我得划版去。”
唉,我更情愿这电话是小语打来的。
坐着发了一会儿愣,抬眼看到笔筒里几枝毛笔,就挑了一支“大狼毫”,用水泡开其尖硬如刀的笔头,找了打儿报纸,好一通狂草,然后,带一手墨迹回家。
走到一条小街的街口,看一条黑狗四肢抱在一起,卧在那儿,很虔诚的样子,并且竟也是满脸的哀愁。这狗东西不会是因为没找到它的狗友吧?我的眼也真毒,连狗的不快乐的表情也能看出来。我服我自己!快走过去的时候,我又回头,看看那狗,呵,狗也正斜眼看我,露半拉眼白儿。
刚做好午饭,儿子张开就抢进院子来,接着是妻子。张开,我起的名字,如果叫“张开嘴”,那肯定饿不死的主儿,可是这小子托着小腮,只盯看电视看动画片《三毛流浪记》不看饭碗。
我用筷子敲他的碗:“快吃饭。”
儿子冲电视扑塌着眼皮:“不想吃。”
我训:“看人家三毛儿,连吃的都没有,你却不知道珍惜。”
儿子斜我一眼:“当三毛才好呢,不用吃饭。”
我恶毒地:“再说没良心的话给你喝尿。”
儿子这才扭头笑:“你尿哎。”
我:“你喝你自己的。”
儿子:“我够不着。”
我说:“你可以先尿到杯子里,再端着喝。”
儿子坏笑:“那我一个杯子尿一点儿,叫你喝不成茶。”
老婆筷子左右一分,叭叭地打我们俩的碗:“恁哥俩儿,别操(吵)了行不?”
第五章 一个问题枪毙了,更多问题站出来!
我笑,儿子也笑,总算拿起了馍。
吃着吃着,我舀饭,剩下个馍头,直接用嘴一咬开始舀。
儿子嘎嘎乐:“妈,看俺爸,象狗一样,用嘴衔馍!”
我在他脸上捏了一下:“妈的,胡说,狗衔的是骨头儿!”
妻子大乐。
儿子偏脸儿想想:“我说错了爸,我要是说你是狗,那我也是狗了。”
这还差不多。
儿子继续有理有据地解释:“俺爸是公狗,俺妈是母狗,我是小狗儿……”
我闪过去,把馍头儿塞进了张开嘴里:“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的?”
儿子把馍吐出来:“啥叫‘上辈子’啊爸?”
我笑:“这么说我不欠你的了。”
妻子狠狠地骂着儿子,然后对我说:“哎,吃罢饭你拾掇厨房啊,别一推碗儿就看书看电视的,我今儿个有点累了,生意忒好了。”
我报怨:“凭什么叫我干这么多啊?”
老婆:“上辈子欠我的呗。”
“欠也不能欠这么多吧,你这么连本带利地整治我啊。”
老婆:“我忙里忙外,又是欠谁的啊?”
儿子得意地:“欠我的。”
这小子,什么事儿他都要插一嘴,将来又是个长舌夫。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小日子真的叫人百过不厌哪。唉。
收拾好厨房,我直接上床抱被子睡觉,省得再想小语和北京的事儿了。但睡不着,只要有心事,不管白天黑夜,一样失眠。我里子面子地反复想北京,想小语。我最终认为,去北京,特别是去北京摸摸民工性压抑,对我来说应该是生活事业的双重转折,是个好机会。所谓有机可乘,就是不要加不要减也不要除,而是大胆地去乘!我是乘数,可是,被乘数是哪个呢?是陈述,是金钱,是小说还是小语?哥的,一个问题枪毙了,更多的问题站出来!
一小觉儿醒来,刚四点,眼迷头晕的,遂出去走走醒神儿。
院外的胡同,宽只有八尺,离大街却不下百米,黑槐白杨都没有,路面也不是青石板的,全是水泥板子,下面,盖出一条直肠一样的下水道,好儿不好的就让人撬起来掏污泥,又黑又臭,放到庄稼地里比尿素都好,可城里不让种庄稼,当然,让种也种不起。
刚到街口,人,车,狗,让或不让地到处走,嘈杂之声,让沉默的黑槐树更加沉默。
“哞——哞……”
几声惨烈的牛叫,象数块青冰,顺着石板路直贯我的耳朵,疼——所有的声音都压不住这惨叫声。
抬头,看到的,是“刘家雪花牛肉”的绿招牌。用“雪花”形容牛肉,就象用芳香形容牛粪一样不恰当。我知道,就算古城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屠夫也不会心软到把自己花钱买到的活物放掉。
刘家牛肉铺又要杀牛了,发出惨叫的,正是一头未成年牛,头上的角,刚刚冒出头皮,象草芽儿刚拱破地皮儿。此时,它,已被死死地拴在一根粗壮的木桩上,绳子勒得又紧又短,冒白沫儿的牛嘴,都跟桩子接了。
穿着黑皮夹克的刘屠夫根本没看到我在看他,他高高地扬起长把儿油锤,对准牛的脑门儿,就是小人书中小牛犊头顶正中画可爱的毛旋儿的地方,一锤下去,牛,发出低低的一声哞,扑通倒地。我脑门子一热,竟然觉得,要是我不去北京,我的未来就会象这头牛一样,被机遇的大锤一下夯死。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去北京!
但我并不急于告诉陈述,我还是想先对小语说,我十分想知道她的态度。
牛腿还在本能地抽搐,刘屠夫蹲下,一抬右脚后跟儿,长刀就捅进了牛的温暖的尸体,象我们把挖耳勺伸进自己的耳朵眼那样准确而自然,象人血一样鲜一样红的牛血,咕嘟咕嘟地从牛身子里流进事先备好的大盆里。盆中,血沫子好久不散,象是在愤怒地沸腾。
脸上一凉。终于,下雨了。街上的人好象中了邪一样,动作集体加快。
老爸老妈从远处小跑而来,我赶紧迎上去,心里都想好了。要是他们问我干么呢,我就说接他们哪。儿女骗爹娘,就象母亲把乳头送进儿女的嘴里一样容易。
开饭之前,我把陈述要我去北京的事儿故作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还好,除了老妈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声感谢主,妻子和老爸都支持。妻子更是态度鲜明:“真要是有机会你出去闯闯呗,看你这会儿成了啥了,文章憋不出来,钱也赚不多。”嗬,真没想到这小娘子现在做生意做得都有点儿看不起我了呢!“你最好多挣点儿钱回来,”妻子说着一指院子,“我想把前边刘家的这个院子买下来,然后把那破房子一扒,再把我们的平房一扒,盖个三层小楼,大门朝南,多敞快啊。”老爸和老妈都赞同地看着他们能干的儿媳妇。我用好象很有钱的语气问:“刘家要多少钱?”妻子:“早都打听好了,最少得6万。这会儿我们存了三万多了,你要是用两年把挣个三四万就齐啦。”
我看了一眼自己做的那盘儿麻辣鸡丁:“大门朝哪都无所谓,关键是出了家门要有路走。”妻子:“光有路走也不行,还得走好,别象志远扣了一身病回来。”这女人跟我结婚八年,“抗日”的事儿不干,糟贱人倒是学会了。
“啥时候上北京啊乖?”老妈眼里泪水开始泛花儿。
心里毛毛地就酸了一下,我给老妈夹了一筷子菜:“后天吧。”
4月11日
雨下了流流儿的一夜,早晨还在沥拉不息。夜半,雨滴落在竹叶上的声音,让我睡得很香。
今天星期一,七点半我就出了家门。我想到QQ上等小语,而不是让她等我。
雨中的古城,最有韵味儿,象鹅卵石,不泡在水里就难得温润之美。而远方的城墙,近处的伞花,更是让人把古城幻作了一段老梅干,花开几度,不得而知。
进办公室我就打开了电脑,上了QQ,小语当然不会在,她不会象我上班这么早。
9点,我们文联的全体人员总算到齐了,总共四个人,平均每25分钟报到一人。文联这单位好象相当于阑尾,上边自然不大注意,当然自在点儿。
阿铁第一个到的,按点儿,进门后就把U盘插电脑上了,叫着我“张主席”,说他写了几篇小说,绝对诚恳地请我指点。
我笑笑,说没时间了,我准备去北京混了。阿铁失意地说,有机会可别忘了叫我也过去。我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