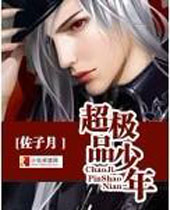极品男保姆-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盘我输,三喜赢,这家伙笑得屁儿屁儿的。我摸出张十块的先押给他了。
江儿一边替我洗牌一边说:“张老师,快讲笑话,越黄越好。”
我还没等讲呢,花狗进来了,根本没注意到我,我也懒得给他打招呼。
花狗笑着对杰子勾了一下手:“走,到我屋里喝酒去?”
杰子迟疑了一下,佝身子屁股离床跟他去了。
三喜儿咦了一下:“这个南蛮得咋舔住花狗嘞腚啦?花狗咋请他喝酒?”
江儿说你管咋嘞闲事儿,打牌打牌。
又有人催我讲笑话。于是我就讲:“从前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眼看着就要老死了,众徒弟立在床前,问他临死有啥要求。老和尚显得很不好意思,说,师父我活了一辈子,啥都见过,就是没见过女人的那儿……”
一屋子都开始哈哈地笑,眼睛和嘴一齐张着等我下文。
“小和尚们都很为难,但为了不让师父遗憾,还是花钱请来了一个妓女。小和尚对师父说,这就是女人,这就脱给你看。这时,妓女普一件一件脱衣服,老和尚大张着一双死鱼眼就那样等着看……”
呵呵,我看听到这会儿一屋人全是他哥的死鱼眼了。
“快讲快讲,我急毁啦快……”有人拍我肩膀催我。
“这时,那妓女终于脱掉了最后一件小衣服,只见老和尚勾着头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唉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你们猜是啥话呀?”我吊他们胃口。
胖子学老尚垂死的腔调:“能不……能让俺……临死戳一家伙呀……”
大家全乐了,三喜儿更是一下一下地按着胖子的脖子笑,我甩了一张牌:“人家老和尚素质高;说的是:唉,原来和尼姑的一样啊……”
轰的一声,全他哥地笑翻在席喽。
离开工地时已经快十点了,脖子上痒痒的,有个小疙瘩,一定是蚊子吻的。正揉,小山吹着口哨回来了,看见我,兴奋地打着招呼,毫不避讳地说他去和鲜花遛着玩了——这个幸福的怀春的少年郎,真叫我羡慕哦。
6月2日
上午;我正给报社编稿子,陈述打来电话,说胡老板的书付印了,让我去公司拿那5千块钱。乐坏我了,正好;把车票顺便买了。而擦汗之间,我又有了个小小的决定。
赶到陈述那儿已是9点半,陈述一边给我钱一边说他又联系了一个碴儿,赶明儿再催催就成了。我把钱放进包里的时候,陈述又说了一句话,让我很不高兴,这小子说,像这么些字,要是找个枪手,四千块钱就能拿下,署名还是他陈述的。那意思是给我的钱太多,亏了。
刚想骂他,推门进来个年青人,二十三四岁的,进门就冲陈述“陈经理陈经理”地衬上了。
陈述马上一指我,对他说:这是公司的张总,也是著名作家,学着点儿。
那人马上又给我问好,脸色谦卑。看样子,也是个找工作找了三年以上的人。
我像个当官的那样说了句好好干。陈述说这是小李,新招聘的,跑跑腿儿什么的。
我才不管谁进谁出,这个比狗窝大一点儿的公司想想我就会打哈欠,产生不了多大的热情。
为节省时间,我打的赶到西客站买车票。
拿钱的手放进售票窗口的时候,我回家的信念还坚定得像千年龟壳似的,但当钱变成两张车票时,我却决定只回河南不回老家。因为回老家必见爷爷,见爷爷就应该再拐到城里去见爸见妈,见丁清远,最主要的是,还要和妻子“短兵相接”。以上所有内容,都是我非常乐意做的,尤其是和妻子在一起。可这些加在一起最少也得一天,而我和小语总共才有两个白天的时间。再说,我和亲朋在一起的时候让小语到哪儿去?让她跟着肯定不成,不让她跟着她会怎么想?那得受多大的委屈啊?我可不舍得让她受一丝儿委屈啊。但这样又觉得对不住家人。左思右想,给老婆汇了一千元,然后,在火车站附近的“步云居”布鞋店,给爷爷、老爸老妈还有丁清远每人买了一双千层底布鞋,每双120元,我猜,他们这辈子也没穿过这么贵的布鞋。
寄了鞋,我又找了个公共话亭给老婆打电话,说了寄钱寄鞋的事儿,然后又说我接到紧急通知,得去东北采访。妻子说,能挣钱当然好,可是人家天天洗澡两回为的可是等你。听得我……唉!
为了不误小语的午饭以及针灸,我又打的返回怀柔,总共花了一百大多,但一点儿不心疼。
回到楼上时,小语正看一封信。没等我问呢,她说是小芳寄的,很欣慰的样子。
我说好好好,赶紧奔厨房,锅,已经让小语坐灶上了。这,比接到小芳的来信更让我欣慰。
吃午饭的时候,我一边给小语夹菜一边别有用心地问:“这次去河南你给林岩说了没有?”
小语淡淡地说:“有必要吗?我是我自己的事。”
我心里刚说了句“那最好”,意外地接到了胡长建的电话,说他今天中午和蔷薇到怀柔的“民济”医院去针灸了,在“老乡”饭店坐下了,请我一起吃便饭。我说吃过了,多谢多谢。
火车还是下午九点的,晚七点,我和小语直奔西客站。
出租车里正放一首歌,什么名儿不知道;从曲到调儿都不错,一个丫头唱得很好听,一声悠长的“回家回家,马上来到我身边”,听得我肠子都朝老家的方向弯了。正沉醉呢,那歌词忽然由汉语变成了英语,除了一个意思是“正在”的“just”,就什么也听不懂了。我这高中生在这时代跟前现在就是一个一清二白的文盲,就是一个大破铝锅,想补都不好补。
小语,脸色平静,左腕上玉镯子在车窗外刷刷扫描的灯影里,不间断地闪着幽幽的光泽。
第五十二章 美女割麦,说麦粒儿都是佛
6月3日
火车上,我们由黄昏而黑夜,再由黑夜而黎明,3日早上7点多,终于在新城火车站下了车,买了4日的返程票。
虽说我是第二次回老家,还戴着墨镜,但心情紧张得被揪掉面罩的劫匪那样。
简单对付了点儿早餐,我们按计划拦了辆出租车,出城向北,沿国道,一溜烟跑了四十多公里,下车。
阳光刺眼,热风逼汗。拽着小语躲到路边的大杨树下,让她戴上那顶白色的宽沿太阳帽,我也弄副墨镜按到脸上。
公路上,除了坦克车,凡是带轮子的车都在跑来跑去的为麦收奔忙。
四野,全是平展展金晃晃的麦田,麦田上面,热腾腾的地气心电图一样乱闪。一台一台的收割机,如巨兽奔突,肆意吞噬着香甜的麦杆儿麦穗儿,隆隆声混在尘烟中,浓郁的麦粒儿的气息四散开来,像少女的红晕格外诱人。
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在老家以外的地方呼吸麦收时的空气,因为一个女人。
“我们去那个村子吧?”小语指着西面不远一个浸在浓绿中的村落说。
我应声拎起不算重的旅行包,下国道,沿一条乡间公路冲东边的村子走去。
路上,行人不多,机动三轮车倒是突突不绝,车厢里,满是从联合收割机上接下的麦粒儿。让小语吃惊的是,开机动三轮车的有好几个竟然是妇女。她说:“我认为女人使用的车应该只有两种,一种是自行车,另一种是小轿车。”
我说:“这会儿男人外出打工,女人不开车也没办法。以前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现在是小娘子替夫开车。”
正白话呢,小山打来了电话,说我写太奶奶的那篇文章得了民生时报5月份的优稿,奖金一千块呢。真他哥的不错嘛,呵呵。
村口。一幢小红楼。楼侧一桐树,树身傍一白裙少妇,正有一眼没一眼地乱看,脚边,斜卧黑狗一只。
这少妇当然没法和小语比,但仍然算上得可人意:眼睛黑而亮,身材凸而凹,风情几万种是没有,但几十种还是有的,呵呵,在农村,算是人尖儿了。
越走越近,黑狗支起前腿,嘴里发出威胁的低呜。
女人冲我一笑,短斥了一声“狗”,狗哼唧了一声,垂尾耷耳地卧倒,委屈了。
我一嘴普通话答碴儿:“你好,我们是北京的记者,体验麦收生活,想找个地方先住下,能帮个忙吗?”
那女人笑盈盈地眼波一乍:“贵客啊,那就住俺家吧,就我自家(己),一个院子两层楼。”说完,她一指身后的红砖楼。
我们道了谢,刚要过去——
“嫂得嫂得,叫我帮忙不?”
摩托车的突突声还没消失,一个男人的声音就喊过来了。
回头,一个精壮小伙子已经支好了摩托车,用手掂着汗渍渍的褂子,露着胸脯,一下一下地扇着。
女人一瞪他:“给你说过多少回啦,少答理我!”
那男人打量我们一眼,丧气地噢了一声,磨头骑摩托走了。
这女人家的院子果然肃静,四四方方的,院中间是一棵巨伞状的洋槐树,南墙,是几株北方很少见的香蕉,正长得霸气十足。
女人说她叫阿兰,28岁了。她丈夫叫运动,在广州搞装璜,寄了六百块钱叫收麦用,可还没挨着收割机。她半是失意半是炫耀地说叨着家里的一切:地板砖,冰箱,侧房的卫生间,楼顶的热水器,说他们家跟城里人的没啥区别。是的,至少比我老城里的房子强。
这女人真的讨人喜欢,她的嗒嗒而行的红色凉拖鞋硬是让我觉得暖。
女人说二楼一直闲着也没整床,一楼的西间就是平常招待亲戚的,让我们睡。
这时,小语的包里的手机响了,小语接电话,“谢谢”没少说,末了又说了句“我不喜欢别人管我”就挂了。不用说,是林岩的。
看看天,小语有点急了,问她们家有镰刀吗,阿兰说这会儿谁还用镰镙麦啊。说完又一拍手,说可能就她老公公用吧,因为他年年都用麦秸织草苫子。说完,就领我们去西地。
出村子没走多远,就看到一个老头儿正弯腰用镰刀割麦,还剩下不大的一块小麦。四周,全是收过的光秃秃的麦茬地。
走到地头,阿兰伸腿踩住一个麦扑子(成捆的麦),大声喊了一声“大”(爹),老人回过头来——一张和善的面孔。
阿兰把我们还有我们的想法说给老汉。
老汉很勉强地笑了笑,说了句“欢迎啊,难得哩”,把镰刀递给我,把头上的草帽也递给了我。
剩下的小麦还有六七茏吧,五六十米长的地身,加一块儿比三间房子大不了多少。
我弯下腰做示范。阳光把我的脖子割得很疼。我抬头问小语:“怕晒吗你,别把你这温室里的花烤成仙人掌了?”
小语也不说话,从我手里抽了镰刀,把腰弯下,抓紧麦棵,把镰刀放平,开始学我的姿势割麦。
我在她身后一步不离地看着,护着,不时地提醒她慢点儿再慢点儿。
小语割麦有气无力的,麦茬在脚下发出迟缓的叭叭声,飞起的麦锈呛得她不时咳嗽,连玉镯都有些灰扑扑的了。
一茏麦割到一少半,我口渴得厉害,也不忍让小语割了,就催她去地头喝口水。
小语嗯了一声,稍停,“哎呀”一声,慢慢地把腰撑起来,左右拧了几下,回头,一脸苦笑和汗迹。
我们快步到地头的一棵泡桐树下乘凉。一只黑背白腹的喜鹊扑拉拉从桐树上飞起。
阿兰真不错,从地那头匆忙而来把我们的纯净水送了过来,直埋怨我们俩享福享够了,就匆匆地回村了。
小语一口气喝下半瓶水,轻轻地喘。
一阵风吹来,她稍稍掂起裙幅,微闭了眼,享受地轻轻长长地啊了一声,把纯净水递给我。
噙住瓶口我喝了一口水,笑了一下,感觉像是间接吻了小语一下。然后不经意地掀起汗衫兜着风乘凉。
小语用鼻子哼了一下,说你脱了不更凉快吗。
我赶紧又放下,大谈风雅:“这风可是上帝对劳动人民的褒奖呢,但不出汗就没法儿领奖。这会儿,到处都是空调,现代人出汗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不过,恐怕没多少人知道,出汗可以避免得那风湿性关节炎。你今天这一出汗,顶你跟桂姐作多少回美容呢。”
小语说“又贫上了”,然后感慨地说:“看来,吃麦真的不容易,每一棵小麦都要被镰刀割下来……我觉得,每一粒小麦都像一滴汗,然后在土里打个滚儿。”
我连连叫好:“好好,每一粒小麦都像一滴汗在土里打个滚儿,这绝对是诗一样的语言,回去之后你一定要写篇文章!你小脑壳儿不简单,真的应该好好写写文章,当个美女作家多好啊。”
“没心情。”小语抓起靠在树身上的镰刀:“我还觉得小麦是一种佛,人人都从他那儿得到了平安与幸福,但没有一个人膜拜它。”
“是啊,人人都以为小麦生来就是供人类吃的,其实人家是为了繁殖后代。”
“你这话我爱听。”小语说完,重又弯腰割麦。
这丫头真犟。
第五十三章 我对另一个女人抛了个坏心眼儿
我无奈地抬头看看天,云彩,一块儿一块儿,毛毛萦萦,也不知是叫卷积去还是什么云。上初中时就学过《看云识天气》这课文,这会儿年龄都能当初中的校长了还是没学会。
几茏麦我们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才完事儿,虽然小语一直在卖力地割,但大部分还是我割的,每隔几分钟我就把镰刀争过来,我可不想累着她。
阳光毒得后娘一样,抽得我皮肤都有异味儿了,倒是没觉得多累。小语就惨了,盔歪甲斜,累得都站不直了,白裙子也快成灰裙子了。不过,精神却出奇地好,真是闹不懂她。
早就饿了,赶到老汉家我就直奔厨房。阿兰已经做了猪肉炖粉条,葱段儿姜片儿可没少放,香哪。
我和小语一人一碗菜一个馒头,比在北京的几菜一汤吃得还利索。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信夫!
阿兰看得是眉开眼笑,老汉却是心事重重的,劝我们多吃时,笑勉强挂在脸上,像他们家墙上贴着的已经耷拉下一个角儿的2001年的年历。
12点多一点儿,都快吃完了,接到蔷薇一个电话,问我在哪儿,要让我请她吃饭。我说我在外面采访呢,胡老板这么有钱你还来熬我的骨油。她说他忙去了,她一个人去怀柔针灸的,这会儿没人问了。这小妞儿,难得能想起我来,要是我这会儿在怀柔还真得请她吃饭呢。
小语淡淡地问谁打的,我说是胡老板的女保姆,也是他侄女,该叫我叔叔的。
饭后,小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拿着阿兰给她备的红裙子就进了洗澡间了。
坐在树阴下,听着洗澡间传来的哗哗的水声,抠摸着洋槐树粗糙得像鳄鱼皮一样的树皮,心里就酸酸甜甜,不可抑止。
“哎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