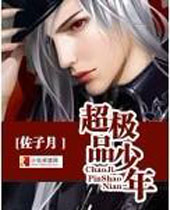极品男保姆-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走到拐往工地的一个路口,树下,一个女人站着,穿着像征纯洁的白裙子。
她在看我。
我刚要拐过去,那女人忽然双臂像个天使那样一展:“大哥,理发吗?”声音软得晒热的泥巴一样,接近普通话,好像是东北人。
我下了车,我明白她是干么的。来北京一个多月了,终于遇上了。
真他哥的暗娼浮动月黄昏啊。
我笑:“等我病好了去找你。”
“你有什么病啊?”女人赶紧把抓我车把的手抽开。
“还没出结果,低烧不退,浑身无力,感冒都大半年了也不见好……”我咳了一下。
“娘哎,艾滋病!”女人大呼小叫地逃开,宽大的裙幅一闪一闪的像撕碎的白纸。
宿舍里,胖子几个人正在大喳呼小叫地打扑克。阿江正在坐在小山的床上翻一本书。
够热的,刚进去我的汗唧儿一下就出来了。
我讲刚才的艳遇,四喜儿说这不稀罕,只要有工地,撑不多长时间就得有理发店呆(在)旁边开。说上一回在东城的海运仓危改工地有一个开理发店的鸡婆,除了怕花钱的,工地上的几十个男人让那一个娘们儿玩了一遍,不知道吸了我们多少血汗钱。胖子叭叭地狠拍着四喜儿的瘦胯,说他这个“吸”字用得真得真好真过瘾。
这时,花狗手里滴溜着一瓶啤酒进来了,给我招呼了一下,接着就大声小气地问屋里的几个人:“哪个不要熊脸嘞,呆工地外边挂嘞那个木牌子上胡吊画?”
三喜笑唧笑唧地问画嘞啥。
“把‘禁止入内’的‘内’字改成‘肉’啦!”
众人大笑。
花狗说谁要是再乱画扎,抓住喽罚款一百。说完,就喊上阿东喝酒去了。
胖子杠(激)我:“大作家,再讲个酸笑话,滋要你一来就显不着我啦。”
几个人也哄场儿。
于是我就讲了一个从书上看的笑话:“这事儿发生在黄河岸边。说一个女人不识字,丈夫来信,只好请堂兄替她看。当时,堂兄正在船上。而当地的规距很怪,男人上船光腚不穿衣。当时,那个堂兄啊来不及穿衣,只好一手捂住下面一手拿着信念给弟妹听……”
几个人开始笑,呼呼的风扇叶子将灯泡旋得一明一暗,胖子的眼珠子也跟着一闪一闪的。
“可是,当时有风,信纸一掀一掀的,堂兄读得不顺当。女人急了,说,哥,我给你捂住下边你专心念吧。那个男人同意了,可是,不知道咋回事儿,越念越慢。这时候女人急了,说:哥,你快点念吧,我快捂不住啦。”
几个人乐得在席上打滚儿,说我真会讲故事,不是直呼拉地贱,还过瘾。
这时,胖子用手背在眼上横了一下笑出来的泪,然后照四喜大腿上猛一拧,说他啥时候都没讲过一个故事,长了两个驴耳朵就知道白听,这一回要是再不讲,今黑喽别打登(算)睡觉。
四喜看了看三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我就讲个吧,这不算故事,是去年我在公交车上碰到的一个事儿。
大家都支楞着耳朵催他赶紧讲。
“那是去年夏天,那个时候我还呆海淀白颐路一个工地上干活儿。当时老板叫我去买钉,车上人稀(挺)多,挤嘞很,当时我给(和)一个城里嘞小闺女挤边挤边嘞,她穿嘞可少,胸嘴儿(脯)露半拉,闻得真香啊,我拿眼一瞅,乖乖,我都看见她乳房啦都……”四喜咽了一口唾沫。
呵呵,大家都在咽唾沫,包括我,不过,咽完唾沫之后,一个念头就忽地闪了出来,心里掠过一阵狂喜。
“当时,我都想用手去摸摸啦……”四喜儿的眉儿挑得都起皱儿了。
“你咋不摸啊傻种?”瘦子的嘴都快罩到四喜脸上了。
“你才傻种哩,摸罢人家不打烂你才怪嘞。”
胖子像个哲学家思考之后那样地咦了一声:“这法儿还真不孬哩,花狗有钱能打炮,咱没钱坐坐公交车几(去),花几块钱饱饱眼福儿不也稀得(挺好)啊?”
“来(往)马路边一坐,看人家穿裙得嘞也中,我都看见过多少回啦,白裤头红裤头都有哩。”三喜儿眼珠子也贼呼啦地亮。
“那滋只能撑死眼饿死吊啊同志们。”瘦子唉唉叹叹地一副菩萨相。
三喜叭地打了一下手背,把一只死蚊子咯捻了地下,得意洋洋地说:“不过,明儿个俺媳妇儿都(就)来了,菜市场租好房子啦,她卖菜,我蹬三轮儿,享福去喽。”
四喜怯怯问在菜市场哪个地方,三喜瞪了他一眼,说你瞎打听啥。
四喜儿一弯脖子,闷了。
胖子乐了:“三喜儿,你弟弟问你你吓恁很咋?是不是怕兔子去吃窝边草啊?”
又是一阵大笑。
三喜恼了,爬起来照胖子肚子上就是一脚:“日恁姨你瞎呱唧(说)啥!”
胖子一看三喜儿真恼了,陪了一个笑,左右扭着脖子说,来来,谁打牌。
第六十一章 性压抑,压出了什么?
回到楼上时已经十点了。小语室内的灯还亮着。我大声说了声“晚上好”,就钻进我的卧室打开了电脑。我很亢奋:四喜在公交车偷看女人衣内风光的做法让我突然有了写民工性压抑的亮点儿。我决定编写一个民工公交车上偷窥的新闻,人名嘛,随便诌一个就是了。在我们老家,我这就叫瞎话篓子钻天棍。
故事都会编,半真半假的假新闻更容易。我把键盘敲得叭嗒叭嗒鸡叨米似的。
等我口渴得厉害去接水时才知道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也敲快两千字了,但忘了站桩了。没办法呀。
一边喝水一边想稿子的结尾,最后,愁了:虽然可以编出这个“李大中”在公交车上如何多次偷窥女人情节曲折的“新闻”,但没有高潮部分,如果“李大中”不被抓住,我就不能说我采访过这个“李大中”啊?可是,要是人被抓了,但我又说让哪个派出所抓了呢?新闻的几个“W”可不能再虚构了啊?
空调滋滋地吐着冷气,我正捏着自己的脖子筋发大愁,手机忽然响了;把我吓一跳,一看号码,是个生号,一接,一个女人的哭腔儿就来了,我更给吓着了。
我说谁啊你是,是不是失恋了打错电话了。
对方说我是鲜花,她的连哭带说她和小山出去玩;被几个联防队员给撞见了;因为没带身份证,就说他们一个卖一个嫖,给带到平安派出所去了。鲜花哭得啡儿啡地,说她不敢给哥说,怕哥打她,这才找我求救。
哎呀,这下我真的吓坏了,早在来北京之前,就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有一对打工的男女出去谈恋爱,也是因为没带身份证,让联防队的给撞上了,两人吓得跑,结果男的掉水沟里给淹死了。北京的联防队员给人的印像比人民警察还有执法权呢。
我赶紧给陈述打电话,陈述醉熏熏地说他这会儿刚从后海泡完吧出来,他的翅儿还没大到能伸到柔性去,管不了;还说以后你少给民工来往,这帮孙子净给我们做那不长脸的事儿。我说滚你丫的,又给胡兴焦打手机,半天没人接,刚要挂,听到蔷薇喂了一声,她娇滴滴且惊喜地说你怎么打电话来了呀?我没心逗她,说胡老板呢,她说跟陈述一块儿喝醉了,不等我说什么,她又说,好叔叔,给我讲个故事嘛,想听你讲呢。我说今天不行,得救人呢。
这可咋办呢?看看表,已经快十二点了。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桂姐。
虽然小语的卧室里还亮着灯,但敲门的时候还是很难为情。
刚敲了一下,小语口气清晰地问我有什么事儿。难道她还没睡呀?
我隔着门简短说了小山的事儿,小语说你稍等一下。
我在门外急得转磨磨。
过了能有几分钟,我听到小语说,没事儿了,人放了,你睡吧。我也要睡了。
我撂下一句“多谢了啊活菩萨”,真没想到小语办事儿这么利索。
6月7日
昨夜熬得有点过了,吃早饭的时候眼还酸哪。
早饭后,小语刚走小山就来了,进门就拽住我的手,就像被解放的百姓遇到解放军一样,都不知道怎么谢我了,眼泪,下来了。
他说我真厉害,要不是我他的名声就全完了。
我问小山:“昨天夜里咋回事儿?”
小山有点难为情地吭哧说:“……我本来也不太喜欢鲜花,可是……”
“可是,你喜欢她身体是吗?”我替他说了。
小山点头,脸红了。
这小子也是性压抑了?我得打听打听,说不定能捞点素材呢。我捞素材是不是有点六亲不认了?
我装作不在意地凿了一句:“现在还是童男子吗?”
小山摇了摇头,脸更红了。
“献身多长时间了啊?”
“嗯……昨儿个夜里9点之前还是呢。”小山把头低得下巴都快戳住胸脯了,“往后,我再也不出去了。”
“就怕你知道女人味儿之后刹不住车啊……”我笑着拍了拍小山,“没事儿,只要注意别造出第二代打工仔就成,去买盒儿避孕套儿吧。”
小山看了看我,咧嘴笑了一下,偷偷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小山走了之后,我给自己编的《性压抑,让他成为公交车上的偷窥狂》这篇文章想个好结尾,桂姐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他表弟破了一个案子,问我能不能帮忙报道一下,说他们所有宣传任务。本不想答应,但昨天夜里人家刚帮过自己,过河拆桥也不能拆这么快,万一过了河之后有事儿再回来呢。所以,凡是过河就拆桥的都是傻蛋,而只有确定此生决不再过桥这边儿而再拆桥的才是智者。呵呵。再者,凡是生理正常的人都对强奸这种案子比较感兴趣儿。
所长叫刘可,亲自开车把我接到了派出所。刘可这人很直爽也很健谈,说他刚上任才一个月,想露露脸儿。我这人做事儿有分寸,做不到的我决不先说出去,我说我尽量帮忙吧,然后我顺嘴儿问是个什么案子,刘可说是个强奸案,一个河北的民工干的。我一听心里猛一激动:民工,这个嫌疑人竟然是个民工!这下我的新闻有戏了!
派出所。心里猫抓狗挠地听丁所长介绍完了民警的办案经过,我又急不可待地要求看一下卷宗。
我看得很细,想挖出这个叫民工强奸女人是不是和性压抑有关。
看完卷已是上午11点半了,不太理想,卷宗里说的主要是作案的经过,发映不出性压抑,但这个人是中专学历,而且结过婚,却又干出了强奸的勾当,应该大有文章。
我想见见嫌疑人,中午只好在派出所吃饭。我给小语打电话,说了桂姐和案子的事儿,让她中午在公司吃饭。小语淡淡地说“你不要管我了”就挂了。
小语的语气让我的心闷了几闷。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了和这个刘所长拉拉关系,我真的不能光围着小语一个人转了。最主要的是,小语,并不是我的什么人啊。
下午一点半,在两个民警的监视下,我见到了那个涉嫌强奸的民工。
我把录音笔打开放在桌子上。
走进审讯室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他一瘸一拐地进来,很自觉地蹲下,顿时矮了很多。人如果不能自由站着,那基本上就是完了。
这男人很年轻,二十五六岁吧,长剑眉,黑眼睛,和小山一样,都是很帅的小伙儿。
我的态度很温和。根据卷宗的内容,我挑主要的问他。
“这卷上显示的是你怎么强奸的那个女人,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强奸她?因为我看得出,她和你认识,你就不怕她报案吗?”
那男人恨恨地:“不怕。我霍出去了。”
“你恨她?”
男人点头:“我恨不能杀死她。”
“为什么?”
男人一咬着牙就把泪咬出来了:“她毁了我一生,她都四十二了,我才二十三。”
“为什么恨她?”我重复了一遍。
第六十二章 极乐极疼的呻吟没有区别,并可救命
男人迟疑着,不想说。
一个民警不耐烦地拿眼剔他:“痛快点儿。”
那男人于是开始说:“我老家是农村的,中专毕业找不到工作,前年来北京打工,主要是修管道……”
“你结婚多久了?”我插了一句,没有人知道我的用意:像这种年轻男人,结婚时间越短,忽地离开女人不性压抑那才是有病呢。
男人:“快一年了。去年夏天,我接了一个电话,就去那户人家修水管,我就这样认识了她……”
男人说,他第一次进那个女人的家时,根本没看出女人已经四十多了,比他家里的女人俊多了。她的家更是像戏台上的宫殿一样。他说那个女人对他真好,第一回修水管就多给了他50块钱。打那一回之后,她家的水管就经常出毛病,直到有一天,他从那个女人的眼里看出了欲望,他们俩在上面是吊灯下面是红地毯的沙发上发生了第一次关系。
说到这里,我又插了一句:“在和这个女人发生第一次关系之前,你有多久没碰女人了?”
他的喉结上下移动了几遭,像乐手的手指划过小提琴的琴腹:“两三个月吧……你问这干什么呀?”
我说没事儿,你接着说吧。
他接着说道:“有了第一回以后就经常发生了,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我经常把这个骚货干得哼哼叫……”这男人说到这里,脸上有了一种征服者的得意表情,这决不是一个嫌疑人应有和应持有的表情。
屋里所有的人都在听,兴趣儿大了。
“你喜欢她的肉体是吗?”
男人先是点头,忽又疑惑地反问我:“这个,好像和案情没有关系吧?”
我笑笑,说你接着说下面的事情吧。
“可是,有一回,到他家之后,我刚进去,他男人就从国外回来了……”
我知道,他说的“我刚进去”是指他的尘根刚进入女人的湿滑身体内部,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果然,一个结过婚离开妻子的男人不但最易性压抑,也最易性觉醒的啊。
“那个和我多次上床的女人就马上变了脸,一把挠破了我的脸,骂我是强奸……我不顾一切地跳窗逃跑摔断了右腿,养了半年才好。”
这时,我才发现,这个男人的前额上有两道若有若无的暗红色的伤疤,也明白他为什么会瘸着腿进来了。
“那你为什么又再次去强奸这个女人?”我追问,像用枪逼一只兔子主动从窝里举着两只前爪子出来。
“我恨这个女人,她答应让我进入北京的,答应让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可是,到那时我才明白,她只是在享受我的身体,压榨我的青春,而不是真的喜欢我……”
“你要求挺高嘛,有北京女人让你占着便宜你就算到天上了。”一个民警很反感地插了一句。
“我不是猪,我也有感情。”那男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