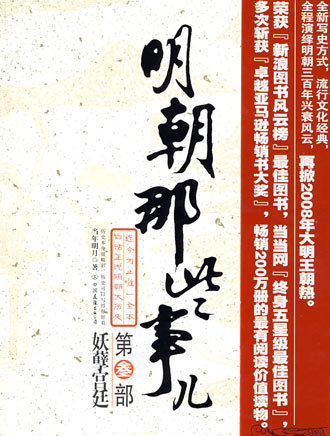北京爷们儿-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力、卖艺的把势匠、以及小商小贩,要是住在城墙外又不是当地的菜农的话基本上就属于盲流了。而大杂院也是崇文、宣武的特产,北城出现大杂院则是知青返后的事了。解放后市民的居住格局虽然有所改观,但南北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一直存在,北城人一直把南城人看作半个乡巴佬。我们家就在南城,而且在护城河外,如此算来就属于四分之三个乡巴佬了。
南北城的差距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群家伙同样耷拉着眼角看人,他们算不得正经北京人,却小母牛坐飞机,牛到天上去了。这些人是军队大院的子弟,动不动就挥着军帽吓唬人的家伙,一般都是成群结伙的,打起架来成编制的上。在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个军队大院,大楼特气派,据说用料是修大会堂剩下的。那里住的孩子一般都穿四个兜的军便服,把我们住的排子房叫鸽子窝,很少和我们交往,打群架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了。
北京爷们儿全文(6)
我家住的排子房规模相当大,方圆有几百米,人口密度更是高得出奇,少说也有几千户人家。住在排子房里的大多是附近小工厂的工人、建筑公司的壮工,职业最好的是第一排住的几家小学老师。老师家平时不太和我们走动,只有收水电费的时候才打招呼,其他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大家最瞧不起任人不理的张老师,他自己傲得像只猴,可儿子是傻子,大鼻涕总在腮帮子上挂着,忒儿搂起来跟抻面似的特别恶心,我们都管他叫豆子。
其实傻人也有傻人的妙处,豆子人虽傻,可做起事来却非常执着,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儿。有一次我上学时看见他蹲在家门口洗衣服,拽着衣裳领子玩命地搓。可放学回来人家还没洗完呢,最可笑的是那个衣领子已经搓出窟窿来了。小时候我们变着法地叫豆子为我们干活儿,什么洗袜子、跑腿儿、买东西、给二头家的狗望风(那阵子流行打狗队),这傻家伙兢兢业业,比劳模自觉多了。有一次玻璃球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我们便找豆子来摸,他脱鞋就下去摸,结果一口气摸上来三个球,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个。
狼骚儿家就在前排,他爸爸是锅炉工,鼻子边总有一道黑印。每到冬天他爸爸就会用自行车往家里驮烟煤块儿,街坊们没煤了就会到他们家去搬。单位的烟煤没掺土,蓝火苗半尺高,烧的时间还特别长。为这事我的父辈们没少和煤厂工作的街坊们拌嘴,他们说掺土是国家规定,要不蜂窝煤做不出来。大人们可不管那一套,有几个聪明便放出风来,五分钱收购一大块烟煤,于是到煤场去偷煤成了胡同孩子们冬天的一项游戏。本来我和狼骚儿并不是很熟,但上学后我们在一个班,街里街坊的不久便混得很瓷了。狼骚儿除了尿炕外也没别的大毛病,这小子鬼点子挺多,放屁都带调儿。
二头家比较远,与我们那趟街足足隔了四五排房子。我爸爸说他们家根儿上可能跟水泊梁山有点儿关系,几乎每代人都会被判上一、两个。二头的父亲倒是个老实人,见了人不笑不说话,可他弟弟大竿儿却是我们这一带最出名的痞子。据说他的成名作是在沙子口和丰台铁路局宿舍的一伙子弟约架,大竿儿挨了三管儿叉还在浴血奋战,对头被他的声势吓晕,当时就认栽了。那回大竿儿身上缝了三十多针,人家根本不稀罕到医院去拆线,几天后自己拿着把剪子就把线头剪了。后来他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走,我们都以为这家伙养了条蜈蚣呢。二头是老二,家里还有一兄一妹,爹亲叔大,三个孩子的性格都随了大竿儿,没一个踏实的。他哥哥大头四岁时就拿煤球把同伴的脑袋打漏了,妹妹卫宁虽然长得文静,可说起话来像喝了镪水,二头本人就更别提了。。
二头家是这一带的刺头,警察想起他们家来头都疼,可他们和我家的关系不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亲戚呢。其实这事多少有些无奈,压缩定量那几年我奶奶接济给他家十斤白面,从此他们便认准了我家是好人,逢年过节肯定提着点心匣子来做客。到了我们这一辈儿,都成了发小儿,关系就更不一般了。有一段时间,二头的爸爸老出差,二头就跟粘在我们家似的,吃喝不算,一高兴就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还有个儿时的玩伴也得提一下——山林。山林从小就特英俊,星眉朗目,齿白唇红,爱人肉长得满脸都是。据说在托儿所里哪个阿姨都喜欢他,特别是怀了孕的阿姨天天把山林抱在自己怀里,就盼着生个跟他一样的漂亮儿子。但他有一个地方不好看,嘴角边有一个小###,又黑有深,笑起来时像个酒窝。但山林笑的时候很少,平常从远处看,这个小坑就跟脸上长了个痦子似的,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那###就出奇的凶狠。
山林的家境是我们几家里最惨的,据说他们家祖上是地主,解放时被镇压了。那时候四类分子的子女找工作比母鸡打鸣都难,山林的爸爸在60年代就蹬起了三轮,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小腿肚子梆梆硬,像挂了两个棕色的铁球,喝起酒来就跟喝白开水似的。那时私人蹬三轮属于投机倒把,他父亲天不亮就出去找活儿干,小偷似的东溜西窜,惟恐碰上多管闲事的老太太。后来红卫兵横空出世,山林父亲再精也没这帮孩子精神头大,他们家常常揭不开锅,文革没两年山林他妈就死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饿死的,却没人敢说。我们一直没弄清楚山林这家伙为什么那样傲,他从不拿正眼看人,嘴里最常说的是:“全是傻逼!”
山林和我最谈得来,前几年他在和别人飙车时被撞死了,后事都是我打点的。如果狼骚儿还算是活人的话,他是我们哥儿几个里最短命的。
我上的那所小学离家不远,走着也不到十分钟。很多人年纪大了都掩饰不住对母校的感情,可我毕业后就再没回去过,其原因还是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不招人带见,上五年级时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
我们这几个人里最爱惹事的是二头,他从小就有暴力倾向,而且大多数情况不是因为自己。
有一次我在家写作业,二头不声不吭地溜了进来。他是家里的常客,谁也没拿他当回事,二头坐在我后面的床上,屁股跟开水烫了似的,老欠着身子往外看。我家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算是不错的,三口人住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还外加一个小厨房,那天我老爸正在厨房里做饭。“你看什么?屁股上长蛆啦?”我实在看不得他魂不守舍的劲头,作业根本写不下去了。
北京爷们儿全文(7)
“你妈今天回来吗?”二头问。
“不知道。”那时我妈在通县上班,经常不回来。
“我想住你们家。”二头又向外看了一眼。
“你家来客人啦?”
“我把一个小子打开瓢了。”二头生怕别人听见,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我也情不自禁地看了眼窗外:“谁呀?”当时我们在学校里也打过架,但那大多是同学间半玩闹的事,头天打完,第二天又凑在一起了。就连我和二头都对捶过几回,鼻青脸肿地回了家,发誓不再和对方来往,可没三天又一块儿下河游泳了。但把别人打开瓢的事还是头一次碰上,我当时也有些慌了。
“就是东边楼上住的,比咱大一届,在初中部。他老在咱们教室门口晃悠,你应该认识?脑袋上有两个旋的。”二头惶恐不安地掰扯着自己的手。
我琢磨了半天也没印象。
“咳。”二头嗔怪地摇摇头:“反正是把他开了。”
“为什么?”
“丫仗着自己个子大,欺负狼骚儿,我就给了他一砖头。”二头拼命搓自己的手,一条条黑泥都小虫子似的给搓了下来,二头执着地搓着,似乎手搓干净刚才的事便与他无关了。“我没使劲,他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就一下!”他双手比画个圈儿:“砖头就这么一小点儿,他脑袋就漏了。你说丫不会找派出所吧?”
“听说现在打架就送工读学校,远着呢,一个礼拜才回一次家。”我惊慌地把窗帘拉上了。“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二头倒在床上,眼睛望着房顶发呆。“没准我哈巴(爸爸)正找我呢?”
“那小子死没死?”我问。
二头鼻子里哼哼了几声:“死不了,丫一边跑还一边骂我呢。”
“要不你去少林寺吧?”当时电影《少林寺》特流行,社会上传说犯了罪出家当和尚就可以免灾。
“少林寺在哪儿?”二头一直喜欢打打杀杀的东西,总拿着根棍子在学校操场上耍咕。“可当和尚不能吃肉。”
“听说有带发修行的,还能娶媳妇呢。”
二头听到这儿,腾地坐了起来:“少林寺远不远?怎么走?”
我仰头想了想:“听说是嵩山,要不我去问问我爸。”正说着,门口突然传来纷乱的吵闹声,我和二头立刻竖直了耳朵。
“就这儿吗?你要敢说瞎话我就找你们老师去!”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气哼哼地问。
我们突然听见了狼骚儿的声音:“就这儿,他保证在。”
女人突然闷声吼起来:“李二头,你给我出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家我都去过了。打了人有种别跑哇,整个一个三青子……”
这时在厨房做饭的父亲推门走进来:“你们俩惹事了吧?”
二头赶紧说:“没东子的事,是我把人打了。”
父亲无奈地看了二头一眼:“你小子是不是吃枪药长大的?这趟街就数你能折腾,三天两头地给你爸惹事,真要走你叔那条路哇?”
二头盯着自己的脚不说话。
中年女人在街口骂得更厉害了:“李二头你个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老老实实出来,还等我去揪你呀?今天你小子要是不出来,我骂你八辈儿祖宗……”
父亲拽住二头的脖领子:“走吧?真等人家来揪你呀?”
二头看看我:“别忘了给小欢子喂食。”小欢子是他养的一条板凳狗,好几次打狗队来都幸免于难,大人们都说这条狗上辈子肯定是大官。
父亲扑哧一声笑了:“走吧,你当不了烈士。”
二头像只被拔掉钳子的螃蟹,他躲在父亲后面,还时不时地看看我。不知怎么,我当时竟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到了手指上,指尖已经微微有些颤抖了。我不由自主地抓住裤腿儿,使劲捻,手指都捻热了,好象不这样就得找个东西打几下。
我们走出胡同口,就见狼骚儿正被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薅着脖领子,女人后面有个獐头鼠目的孩子,脑袋上包了块白布,似乎刚哭过,脸上是一道儿一道儿的黑印儿。狼骚儿灰头土脸的,眼睛不住地向上翻。他嘴里哼哼唧唧地说:“我真不认识他们家是哪个门,这不是二头的家。”那女人突然扯着嗓子又喊起来:“李二头,你个小噶畚儿的,有种打人,没种出来,是你妈养的你就给我出来!”
“行啦,大姐,歇会儿,歇会儿。”父亲笑呵呵地走过去:“哪儿那么大火气,也不怕伤了身子。”
女人立时不说话了,她瞪圆眼睛,眼珠车轱辘似的打量起父亲来,也许是父亲还算长得气派,女人竟嗽了一下嗓子。后来她看见了我和二头,奇怪的是她一眼就盯上了二头,她指着二头道:“这就是李二头吧,瞧你那三角眼就不像个好东西。”她转过脸问父亲:“他跟您什么关系?”
“他是我侄子。怎么啦?两个孩子掐起来啦?”父亲拉过被打的孩子,掰着脑袋看了一阵儿:“还疼不疼?多大口子?”父亲顺手拍了几下他的肩膀,回头瞪着二头道:“你这小兔崽子,手上就是没轻没重,你看看,还不向阿姨陪不是?”
二头跟木桩子似的站在那儿,他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地面。
“瞧他一脸横肉的,长大了也不是个好东西。”女人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家孩子多老实,你凭什么欺负他?把我们孩子打成这样,你还有点儿人心没有?”她越说越激动,身子竟向二头靠了过去。
父亲赶紧过去用身体挡住了女人的去路:“不过是小孩儿打架,大人上手不就成护犊子了吗?”说着,他凶巴巴地对二头发起了狠:“怎么回事?你怎么动手打人哪?人家怎么招你啦?”
北京爷们儿全文(8)
二头楞瞌瞌地一手指着狼骚儿,一手指着挨打的小子:“他欺负他。”
父亲故作郑重地问狼骚儿:“是吗?二头是不是说瞎话?”
狼骚儿回头瞪了挨打者一眼:“我在厕所里撒尿,他说我跟他犯照(挑衅的对视)来着,要打我……”
“胡说!”中年妇女横着蹦了起来,腰上的肉呼呼直颤,她夸张地抡着胳膊,漫天都是肥大的膀臂。女人大叫道:“照你们这么说我们家孩子成流氓了,我们挨了打倒成活该啦……”
此时胡同口已经聚集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大家说什么的都有,有两个起哄驾秧子竟说二头打得轻了。眼看中年女人就要躺下撒泼了,父亲赶紧上去劝住她:“大姐、大姐,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他回手给了二头后脑勺一巴掌:“狼骚儿没动手,你拔什么横?就你能葛儿。”然后他从口袋掏出十块钱,塞给中年女人。“行了,您别跟孩子一般见识,这是医药费。您放心,呆会儿我去找他爸爸,非好好揍这臭小子一顿不可!”
女人看见这张大团结,脸色立刻缓和下来。“您不知道,他爸爸是技术员,咱不能跟一般的家庭比,我们特重视孩子的教育。现在的学校里什么人都有……”
父亲赶紧笑着说:“是、是,您的孩子以后能当工程师。”
女人听了这话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她挤眉弄眼地说:“今儿是冲您,要不我非给他弄派出所去不可,胡同里的孩子就没好样的!”
此言一出,还没等父亲说话,看热闹的邻居先骂了起来。“嘿,你说什么哪?找死啊?”“胡同里全是大流氓,你晚上回家有本事别从这儿走。”“就她爷们儿,我认识,一身咸带鱼味儿,还技术员呢!”“弄个橛子把她那崽子的屁眼儿堵上!”“你们家不就住四楼上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