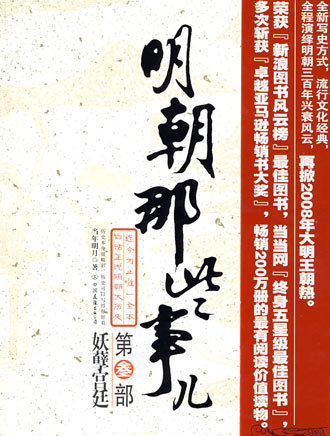北京爷们儿-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怎么了?怎么了你还不清楚?你跟他们不是一类人,老跟他们混在一起早晚得把你毁了。前一阵子你们还敢打高年级的学生,这样下去还了得?”班主任面目通红,嘴唇颤抖。她的手向指着外面,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我顺着她的手望去,小鸟已经给她吓跑了,窗外是淡淡青天,操场中上体育课的高年级学生正在踢足球。“他们?您说的是谁呀?”我壮着胆子问她。
“山林、二头他们,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能学到什么?”老师无奈地摇头。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我老老实实的说。
老师叹口气,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知道你们从小就在一起,可这并不能成为不学好的理由。按你的成绩将来是要考大学的,他们呢?他们——”班主任歪着头想了想措辞。“他们将来的事就不说了,最近我收到了不少家长、同学反应的意见。”她指了指自己的抽屉。“他们在外面成帮结伙地打架,连高年级的同学都敢打,还到别的学校截女生。我担心这里面也有你的事。”
我使劲梗了下脖子,打架常有,截女生的事不清楚。“谁说的?”
“谁说的你别管。”班主任瞪了我一眼。
“有人就是爱扎针儿,没劲。”我小声嘀咕,眼珠子一个劲地往上翻。
“呵!你还挺不服气?什么叫扎针儿?那是向老师反应问题。”班主任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豁出去了,反正脸已经撕破了:“保证是大院里的孩子打的小报告,当官的毛病还遗传吗?”
班主任被气得原地转了一圈儿,她揍我的心都有了,手指哆哆嗦嗦地没地方搁:“你脑袋里尽是些什么东西?明天把你父亲请来,学习委员先让精卫代理。”我转身就走。“站住。”班主任大声喝着,她走到我身后:“我这是为了你好,将来你长大了就会感谢我了,现在的社会风气太乱。你是要考大学的,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成为有作为的人,看看你们家那片排子房,有出息的都是考大学考走的,总共才几个?可考走了人家就不回来,这是为什么你得好好想想。”
“有没有作为管什么用?”我转身问她。
“年纪轻轻怎么学会玩世不恭了?”班主任的调门又提了起来。
二
扬名立腕儿
到初二时我们仗着大头的淫威和小哥儿几个的不懈努力,在初中部呼风唤雨了。那时学校里形成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的同学见了我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要主动点头,毕业后班主任听说这事后惊得差点背过气去。
第二学期,狼骚儿突然变得阔绰起来,隔三差五地请客吃饭,十块把块的从不皱眉。这小子还把我们的烟给承包了,那时年轻人常抽的烟是凤凰和友谊,叼着凤凰烟在街上溜达,就跟近几年揣着万宝路在女朋友面前显白似的。再后来他竟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块板儿砖(国内最早的录音机)。
有一次他特神秘地把我们集中在附近工地的水泥管子里。“你要拉屎也得找个干净点的地方吧?”二头看看水泥管子附近的一滩滩大便痛苦地说。我也特不满意:“有陪绑的,还有陪拉的哪?你恶心不恶心?”狼骚儿神秘地拍了下自己的书包。“给你们弄点新鲜的看。”
“你也有新鲜的?”我指着他的鼻子骂道。“这狗东西上回在这儿拣了一个用过的避孕套,还腆着脸的给我看呢。你呀!顶多弄两本手抄本,《少女的回忆》我早就看了,你要拿不出新鲜的可不行。”
“这回可是好东西,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才弄来吗?”说着狼骚儿摆好板儿砖,从口袋里套出一盒磁带。“瞅瞅,邓丽君。”我们几互相看了一眼,磁带上的字是手写的,一看就知道是翻录的。二头疑惑地说道:“邓丽君唱的不都是黄歌吗?”山林腮帮子上的###抖了一下,他不耐烦地挥挥手:“什么黄不黄的,听听再说。”
磁带效果不好,刺刺拉拉的,我们只好挨个把板儿砖举在耳朵旁边听。那是邓丽君早期的几首歌,什么《夜来香》、《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几首已经忘了。
北京爷们儿全文(14)
邓丽君是那个时代的魔女,她用女人特有的雌性特征折服了所有男人,大老爷们儿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大多是从她的声音里才清楚女人的真正含义。
当邓丽君柔美似水的声音第一次叩响我们心弦的时候,我竟觉得世界的另一扇门突然打开了,于是紧张得满脸肿胀,手心全是汗。那穿透力极强的声音顽强地从破磁带里钻出来,像无数根绣花针,不时地刺穿着我的脚心,我竟感到自己的身体随着那幽怨而略带凄凉的旋律,飘到了不知名的远方,那温柔的感觉叫人难以形容。那时我不自觉地想起了精卫。
其实刚上初二时,我和精卫的冷战就开始了,别人的早恋不过是小儿科的玩笑,可轮到我们时,我俩却把它演绎成了另一种惊心动魄。
自从我们分手后,就像盖房缺了根主梁,我怎么也不能把自己整个架起来。可笑的是我老人家屡建屡塌,屡塌屡建,就是不死心。
精卫和我是初中的同桌,后来第一次听到《同桌的你》时,眼泪差点流下来。当年她是个快乐的女孩,脸上总浮现着天然的笑容,皮肤黝黑而光滑似锦,两个浅浅的棕黑色酒窝嵌在油滑发亮的皮肤上,别提多动人了。精卫是天生的尤物,她总能成为人们视线的中心,那苗条的身材、欢快的步履,明媚得像阳光般的微笑,无时无刻不在我心中荡漾。更让我气恼的是,一旦我们相遇就会生出许多不愉快来,甚至反目成仇。
大约是初一时的体育课上,体育老师让我们走队列,女生在前男生在后。我走着走着,一斜眼发现前排队列里,有两条黑油油的辫子在阳光下闪着亮,它们随着队列的前进晃来晃去,马尾巴似的发梢活泼可爱,生机四射,又透着股倔强。我忽然对那两条长辫子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强烈地预感到自己和这两条辫子有某种联系,而心在那一刻突然不知所在了。两条辫子似乎拴住了我的目光,不知不觉中我走错了步点,连踩了好几脚前面同学的鞋后跟。体育老师怒气冲冲地踹了我屁股一脚:“看什么哪你?”
从此我的视线就再没有如此清晰而专注地凝视过其他东西。
每节课我都有意无意地瞟她几眼,她的笑如草尖上欢快的晨风,她紫红的嘴唇异常鲜艳,这辈子也不用买口红了。有几次我正提着笔发呆时,竟看到女孩儿正在看着自己,天生的一双笑眼似乎向我挤了挤。
这就是精卫,一个曾让我梦绕魂牵过的名字,当时很多同学常拿这个名字开玩笑,狼骚儿则干脆叫她味精。可我却知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红嘴的小神鸟儿有着令人发指的坚强。
精卫很出色,一直是三好生和干部的当然人选。她不仅成绩好而且还特招人待见,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她的“美谈”被老师、同学四处传扬着。我的爱人肉估计是长在脚后跟上了,成绩虽然不错,却一直不稳定,偶尔还和山林他们闹出些新闻来!老师们想起我来就烦。他们将我安排在精卫身边,多少也有点以善抑恶的味道。精卫和同学们的关系都挺好,却偏偏经常和我常吵嘴。年代久远了,现在也记不起因为什么吵,反正好玩儿得很。
“起立!”
有次数学数学老师进屋,大家像平时一样离楞歪邪地扭在当地,数学老师为人随和,学生们自然登鼻子上脸,狼骚儿还趁机伸了个懒腰。
“行了。”面对这场面,老师早就麻木了,可他还是是想说几句:“自行车轱辘不圆得拿隆,你们都欠拿拿隆。坐下,坐下。”
“轰!”的一声,教室里像涌进一群苍蝇,老师话音未落就坐下了四五个,似乎再站片刻就会有人横尸当场了。我习惯性地一伸腿便狠狠坐下去,屁股刚撅到一半就知道大祸临头了。可我的腿已经撑不住了,于是屁股如断了线的风筝,撞在楼板上。太狠了,我觉得嗓子眼里冒了股青烟,眼珠子蹲得上下直跳。
连数学老师也跟着笑起来,教室里跑进来只黑猩猩,顿时炸开了窝。有几个同学做着鬼脸跑过来,嬉皮笑脸地查看我摔坏没有,有人甚至拉住我的脚使劲往上抬,似乎我已经半死了。我单手撑地一扭腰就跳了起来,像足球裁判似的,弓着身子四下张望。开始我以为是二头的恶作剧,可这家伙早笑得不能自制了。教室里只有精卫没乐,她手举课本幸灾乐祸地瞟了我几眼,意洋洋地翻了翻白眼。我立刻想起,前几天曾将精卫的辫子系在椅子上。那次精卫给气哭了,这回轮到自己,也只好认栽。我们就这样相互捉弄,无论闹得多厉害,也从没急过眼。
那年去颐和园春游,我们被同学们起着哄地拥到同一条船上。
春光明媚,天空象刚刚用筛子过滤过,清澈如兰。湖水碧绿、几朵白云压在低低的小山丘上,满山都是亭台楼榭。那时的颐和园比较简洁,厅堂的大漆墙面还有不少破损,看起来颇是古朴。
“从没有听说过你会划船。”精卫极不信任地把桨递给我。
“划船有什么难的?是人就会。”
后来我再不敢动过船桨了,好在船桨已经没什么大用场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何每桨下去都会溅起那么大水花,变换了好几个姿势都不管用,船还没到湖心大家就淋成了落汤鸡。
“卿卿我命,悠悠君手!”精卫一边擦脸上的水,一边弯着腰过来抢我的船桨。“你真行!让小女子划几下好吗?”
“反正我老不会游泳,你们掉下去与我无关。”我嘴里不服,可还是老老实实地让开了。我忽然觉得意犹未尽:“看你下回还敢不敢撤我的椅子?”
北京爷们儿全文(15)
“你别美,我会游泳。”精卫歪着眼看我。
“对!把他推下去。”另外几个同学扑过来七手八脚地拽我,我赶紧趴在船舱里求饶。咳!现在我已经三十多了,还是个旱鸭子。说来可笑,我这样的笨蛋居然在轮船上干了两年多,老天爷真是不长眼。
此后精卫再没撤过我的椅子,但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故事,捉弄和提防捉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实在想不出新花样,大家便相约出去,看电影、滑旱冰,逛公园。每到周末,我们都像要丢了魂似的在课堂上默默对视,一天的分别似乎相隔万世。
暑假前夕我偷偷写了张字条,塞到她文具盒里,大意是约她去天坛,单独的。我明明看到她发现了字条,可精卫没有任何表示,她一直在低头玩儿铅笔。而我则像长了虱子的公猴,抓耳挠腮,浑身刺痒。那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失眠了,闭上眼就是精卫怒目横眉的训斥,后半夜还没睡着。
第二天我决定碰碰运气,在约定时间赶到公园门口。很远我就看见精卫了,她正躲大门阴影里看书呢。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上前拉住她就往天坛里跑。在公园转了很久,我居然没说出一句整话来。一直走进那片核桃林,我才意识到该说点儿什么:“我给你摘个核桃吧!”此时我终于找到交流对象,一口气连摘了四五个核桃。“小心!”精卫本想拉住我,可我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动作出奇的快。“看看。”我一手攥着两个核桃,傻乎乎地跑回来。
“你跳得真高!怎么运动会的时候你不上?”
我咽了两口唾沫,赶紧转移话题道:“我问你,为什么这儿的核桃是绿的?见过绿核桃吗?”
精卫仰头想了好久,最后不得不说:“我不知道。”
“也有你不知道的事?”我纵着鼻子,嘿嘿笑几声:“告诉你吧,这核桃没熟。傻蛋!”我扶着树干,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精卫没搭理我,她气恼地向前走去,脖梗子都气红了。我赶紧收拢笑容,哈巴狗似的在后面跟着。
天坛的树林是北京市内最大的林区,树木以松柏为主,长绿如翠,林子是又密又深,几搂粗的大树到处都是。那年北京的夏天出奇的干旱,已经一个多月没下雨了,地上到处是旱死的枯草,密密麻麻的松枝上挂满尘土,树林呈现一片雾状的青色。每走一步,尘埃都会“朴朴”地冒起来,即使在林间小坐,也会感到呛鼻子的土味儿。鸟鸣阵阵,一群群大鸟在天空盘旋;凉风渺渺,它轻柔地于林间穿行,像任性而柔弱的头发在额上舞蹈。
我们走累了,便背对着背默默坐在一块大青石上,以前我总盼着能单独和她出来玩儿,可凑在一起又实在想不起该说什么。我轻轻地把腰向后移了移,精卫没动,我们的后背靠在了一处。虽然隔着衣服,可我依然能感觉到她“咚咚”的心跳。那时我激动得有些坐不住了,手心冒汗,身体膨胀,紧紧的内裤里居然有点儿阴湿的感觉。
在林子里几乎看不到天空,我仰头盯着树叶间溜过来的阳光,那一点点地跤跃着的光茫是纯白色的,稍稍闭目,眼前立刻出现一大片紫红色,它由浅到深,慢慢的也变成了花的。渐渐我的神志有些恍惚了。不久,隐隐感到有点什么东西在动。不,那绝不在身上,好象是身下那块石头在动,那似有似无的感觉像来自大地深处的暗示。后来我认定,可能是同步的心跳产生的共鸣。
二头他们没少拿我和精卫的事开玩笑,二头甚至说我是专门拉三好生下水的流氓。可凭心而论,在和精卫的几年交往中,我连她的手都没敢拉过一下。
刚上初二我就觉得精卫一直闷闷不乐,问了几次她都懒得开口。后来我又几次约她出去玩儿,精卫都没答应,如此一来我的情绪也逐渐低落了。不久狼骚儿偷偷找到了我,他煞有介事地说道:“嘿,你知道吗?精卫不是什么好鸟。”
“你是好鸟?”看着他表情丰富的脸,真想揍这小子一顿。有时狼骚儿的德行实在叫人恶心,可这家伙偏偏什么都清楚,可能他的耳朵的构造有常人吧?
“我本来就不是好鸟。可我看透了,尖子生脑子里更复杂。咱班就你们俩学习好,怎么样?一对儿坏种。”狼骚儿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脑袋嗡了一声,是不是我们在天坛的事被人知道了。可转念一想,知道又怎么了?我们又没干什么。“你丫就恨天下不乱,人家惹你啦?”
“人家哪稀罕惹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