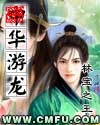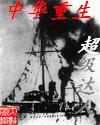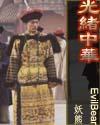中华野史-第1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话说元封元年,武帝东封泰山,北巡朔方,周行一万八千里。所过之处,颁给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金钱不下万万,皆由大农令桑弘羊供给,并无缺乏。说起桑弘羊,乃洛阳贾人之子,年十三,入资为郎,得事武帝。弘羊自少善于计算,数向武帝言利,甚得信任,至是拜为搜粟都尉,代孔仅领大农令,管理天下盐铁。弘羊因见国家每年收入虽多,而出款亦复不少,出入相抵,并无赢余。若有意外费用,一时无从筹措,必须预为打算,增加收入,方可应急。但是筹款方法,无非取诸民间,如算舟车,告缗钱,专卖盐铁等,皆见施行。若再加税抽捐,不但小民罗掘已穷,国家所获无几,而且专靠搜刮,也不是理财手段。弘羊沉思数日,得了一法。他本生长商家,熟识贸易,便想替国家经营商业,借获厚利,却立一种美名,谓之均输平准。其法于各地设立均输官,令各州郡将所收租税并其运费,全数缴纳于均输官,均输官将款购买本地出产货物,按照平日商贾所贩运之种类运送入京,交与大农,是为均输。大农尽括天下货物,视其价之贵贱,贵时发卖,贱时收买,如此则富商大贾无从牟利,物价不至腾贵,故曰“平准”。桑弘羊既将此法奏准武帝施行,又请令人民得纳粟补官并赎罪,武帝亦即依从。果然行了一年,人民所纳之粟,不计其数,太仓及甘泉仓皆满,边塞亦有余谷。而均输所得之帛,不下五百万匹,人民并未加赋,国用却甚充足,武帝乃得任意挥霍。今因有司说是封禅之后,天报德星,遂想到桑弘羊理财之功,下诏赐爵左庶长,黄金二百斤。
武帝自行封禅之后,天久不雨,因命百官祈雨。此时卜式失宠,被贬为太子太傅,见桑弘羊专替武帝谋利,居然受赏,心中不悦。乃私向旁人说道“县官但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遣吏日坐市中,开列店肆,贩卖货物以求利,真属不成事体。
据吾之见,惟有将弘羊烹死,天方下雨。”读者须知国家经营产业所得收入,比起加捐抽税强取于民,尚算善策,不过在当日事属创举,故卜式见为奇异,而后世言利,必称桑弘。可见桑弘羊、孔仅,究是善于理财,卜式之言,实属过激。
是年各地不过小旱,收成尚无大害,到了次年春日,正值田家下种时候,雨水又复缺少。武帝颇以为虑。一日,忽报公孙卿候神回京,武帝召入问之。公孙卿说在东莱山上,亲见神人,神人似言欲见天子,故特赶回报信。武帝听了,不胜欢喜,立即命驾东游。行至缑氏县,拜公孙卿为中大夫,一路趱程到了东莱。武帝沐浴斋戒,住宿山下,分遣近侍,遍往山中寻觅,但有影响,立即报知。武帝住了数日,近侍陆续回报,据说高岩峻岭,深林穷谷,到处搜寻,毫无闻见,但见有大人足迹而已。武帝不信,亲自命驾入山巡行一周,神人究竟杳然,便向公孙卿详细诘问。公孙卿一口执定前语,说是千真万真,武帝被他迷惑,未肯罢休,复命方士千余人,分路前往寻仙采药。
武帝此次东游,一路上兴高采烈,以为公孙卿敢为此言,必有几分把握,不料仍是落空,意中大觉懊丧。此时方想到自己出行无名,若使人民知是求仙不遇,岂不传为笑柄?便欲借个题目,遮掩过去,恰好闻说东莱附近有万里沙神祠,甚是灵应,因记起人民正在苦旱,不如借祈雨为名,见得此行是为民事。遂遣从官前往祈雨,自己由东莱起程,顺路致祭泰山。祭事既毕,将回长安,武帝忽又念及黄河决口尚未塞好,本年雨量稀少,河水不致泛溢,曾令汲仁、郭昌带领人夫数万兴工堵塞,不知能否成功,且趁便亲往看视一番。武帝想定,即命起驾直往瓠子,亲临黄河决口。
说起黄河之患,历代史不绝书,其实并非不能防范之天灾。
特因后世治水之人,只知筑堤堵塞,不肯依照水性,为一劳永逸之计。甚乃壅遏水势,以邻为壑,致河患至今不息,真可慨叹。昔日大禹治水,将北渎疏为九河。借杀水势,深合治水原理。经历夏商周三代,为时一千余年,黄河并无水患。自春秋时代,齐桓称霸,侵占河道以广民居,九河遂并合为一,下流已受阻碍。又兼近河各国,但图己国利益,或掘鸿沟以开水利,或筑堤障以防水害,尽将河边空地占领,河流不得疏畅。到了周定王五年,河始由宿胥口泛决,东移漯川,复由长寿津别流至成平,复合于禹故道,是为黄河河道迁移之第一次。
及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又由顿丘西北移向东南,流入渤海。
是年夏日,河决濮阳瓠子口东南注于巨野,通入淮泗,被灾之地,共有十六郡。河决之际,但听得一声响亮,天崩地塌,附近居民皆见有一蛟龙,由决口中飞出,后随龙子九个,直入河中,沿海逆上,喷沫流波,直达数十里之远。武帝使汲黯、郑当时前往塞之,屡塞屡坏,只得罢手。自此之后,山东连年水患不息,梁楚之地被害尤甚,故武帝又命汲黯之弟汲仁同郭昌继续其事。武帝行至瓠子,汲仁、郭昌闻知车驾到来,连忙向前迎接。二人见了武帝,备言河工重大,材料缺乏,只因塞河须用薪柴,此时正值东郡烧草,薪柴甚少,不得已伐取淇园之竹,中填土石,以塞决口,名之为揵。武帝遣使沉白马玉璧于河以祭河神,又命群臣自将军以下,亲自负薪,置于岸旁。武帝心忧河工不成,乃作歌二章。其词道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巳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
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令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返兮水维缓。
河汤汤兮激潺泼,北渡回兮迅流难。
搴长茭兮湛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揵石苗,宣防塞兮万福来。
当日塞河一班人夫,见天子御驾亲临,官吏亦帮同作工,大众愈加努力。果然人多手众,不久便将决口堵塞,建筑一宫于其上,名曰“宣防”。于是引河北行,复禹故道,梁楚之地,遂无水灾。武帝回到长安,想起公孙卿连年候神,并无效验。
听其言语,不是某处降真,便是某山显圣,说得天花乱坠,反累我往来奔走,何曾有些影响,因此发怒,召到公孙卿,严加责备。公孙卿被责,心恐武帝诛之,乃又想得一策,托大将军卫青代向武帝说道“仙人本来可见,无如陛下车驾往来匆促,所以不能相值。今陛下可建筑宫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等物于其上,仙人当可招致。且仙人性好楼居,非极高显,不肯下降。”武帝依言,遂命有司就上林建筑飞廉观,就甘泉建筑益延寿观,各高四十丈。飞廉乃神禽之名,能致风气,其状雀头鹿身蛇尾,头上有角,身有斑纹如豹。武帝命以铜铸其形,置之观上,因以为名。又于甘泉筑台,名为通天台,亦曰“望仙台”,台高三十丈,望见长安城。待到台观既成,武帝使公孙卿设置供具,望候神仙,公孙卿借此竟得免责。
是年夏日天下大旱,武帝甚是忧虑。公孙卿见了,又想设法逢迎,因进说道“昔日黄帝封禅,天旱三年,因欲干燥所封之土,不足为忧。”武帝听说,便将愁怀放下,一意大兴土木,增广宫室,并遣人就泰山下建筑明堂,又更置甘泉宫前殿。
一日忽有人报说,甘泉宫斋房,生一奇异之物。武帝闻报,立即亲往观看。未知甘泉宫出生何物,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一回 袭辽东小国启衅 定朝鲜两将无功
话说元封二年夏六月,有芝生于甘泉斋房,九茎连叶。武帝以为祥瑞,下诏大赦天下。一日忽报朝鲜起兵攻杀辽东都尉涉何。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率兵讨之。说起朝鲜,自从周武王封与箕子,传国四十余世。当战国之时,属于燕国,汉初以其地僻远难守,修复辽东边塞,至(氵具)水为界,及燕王卢绾,弃国逃入匈奴,有燕人卫满,聚众千余人,东走出塞,度(氵具)水,居秦故空地,降服诸夷,并燕齐亡命之徒,自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惠帝吕后之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见卫满强盛,与之立约,使为外臣,禁约塞外蛮夷,勿得侵犯边境。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者,不得阻止。于是卫满借其兵威财力,征服近旁小邑,地方数千里。传至其孙右渠,既未入朝中国,又多诱致亡命汉人。至是有真番辰韩国,欲上书入见武帝,复被右渠阻遏不通。武帝闻知,乃使涉何往使朝鲜,责备右渠。右渠不肯奉诏。涉何见其倔强,心怀愤怒。及至回国,右渠使其裨王,一路护送。到了(氵具)水边界,涉何暗嘱御者,出其不意,刺死裨王,即渡(氵具)水,驰入边塞。还报武帝,说是杀了朝鲜将官。武帝闻说甚喜,不加细问,便拜涉何为辽东东部都尉。
朝鲜人见其裨王被杀,报知右渠,右渠大怒。正在无从发泄,忽闻涉何为辽东东部都尉,相隔不过一水,遂遣将领兵,乘其不备,袭攻辽东,竟将涉何杀死。武帝大怒,募集天下死罪囚徒,充当兵卒。令杨仆、荀彘带领,往讨朝鲜。朝鲜王右渠得报,急分派将士固守险要地方,以防汉兵到来。
杨仆、荀彘二将奉命,各率人马五万,分道出征。杨仆由齐地乘船,东渡渤海,荀彘却由辽东迸发,约定会攻朝鲜京城。
杨仆水道行程较速,自领兵队七千,先渡渤海,到了列口地方。
照约应在此处等候苟彘,一同进兵。杨仆自恃前功,冒险轻进,也不等后队到齐,独率七千人,直到王险城下,传令攻城。朝鲜王卫右渠,早有预备。闻知汉兵到来,遣人出外探听。据回报说只有七千人马,卫右渠见汉兵甚少,遂命大开城门,出兵迎敌。两下交战一阵,汉兵寡不敌众,死伤大半,其余四散逃生。杨仆战败,与部众相失,落荒而走。逃至深山之中,藏匿十余日,渐渐收集败卒。计算三停人马,折了两停。杨仆遭此大败,只得退兵,静待荀彘到来。谁知荀彘兵到(氵具)水,遇见朝鲜兵队,阻住去路,彼此相持多日,胜负尚未能决。
武帝见二将未能成功,心想朝鲜小国,不值得劳动大兵。
且恐师出无功,反被蛮夷看轻,不如乘此兵威,遣使谕令求和,便可息事。乃遣卫山为使,往谕右渠,晓以利害。右渠一见使者,顿首谢罪,说是自己早欲求和,但恐汉将用计诱杀。今见使节,情愿归附,即令太子随同使者入朝谢罪,并献马五千匹,又送到许多粮食,犒赏兵士。卫山既与右渠约定,克期带领太子起程,右渠遣众万余人,各持兵器,护送太子。将渡(氵具)水,卫山见朝鲜兵容甚盛,疑其中途为变,便与荀彘商议,二人意见相同。乃向朝鲜太子说道“太子既已归降,宜令从人勿持兵器。”太子听说,亦疑汉将与使者有诈,于是不渡(氵具)水,自引人众回去。卫山见事不成,只得回报武帝。武帝怒其失计,立将卫山斩首,一面遣人催促二将进兵。
荀彘奉到武帝命令,督宰军队,奋勇杀败敌兵,渡过(氵具)水,一路杀到王险城下,遣人约会杨仆一同攻城。此时杨仆后队亦已到齐,闻信立即拔营前进,到了王险城南驻扎。荀彘早巳率同部下,围住西北两面,进力攻打,望见杨仆兵到,又遣人催促进兵。杨仆心想荀彘久为侍中,素得武帝亲幸,所部将士皆燕代人,生性强悍,又兼乘胜而来,其气甚骄,以为朝鲜即日便可荡平,所以拼命攻打。我部卒皆齐人,浮海东行,遇着风波,已受损失,先与右渠战得大败,挫了锐气,军心恐惧,自己也觉惭愧。因记起前次与路博德围攻番禺,出尽死力,欲占首功,结果反被路博德坐享现成。如今何不也学路博德,一任荀彘急攻,我只安坐待降,岂非善策。杨仆想罢,遂向来人含胡答应,吩咐将士,就城下排阵,摇旗呐喊,虚张声势,并不实力攻击。因此荀彘独力围攻数月,尚未能将城池打破。
当日王险城中被围日久,朝鲜王右渠一意固守,却有一班大臣路人、韩阴、王唊等,心恐城池失守,自己身家不保,私自会议,意欲投降汉军。因见荀彘兵队凶猛,恐其不肯纳降,杨仆来势和平,想是容易说话,遂遣人出城径赴杨仆军中,说明来意。杨仆大喜,立允其请,彼此商议降约,使者往返数次,尚未决定。荀彘又遣人来与杨仆订期协助攻城,杨仆一心希望受了朝鲜之降,更无心事进兵。荀彘一连来约数次,杨仆只是按兵不动。荀彘见杨仆不肯如约,不免动怒,又不知他是何意思,遣人打听,方知杨仆与朝鲜约降。荀彘便也遣人招降朝鲜,意在独占大功,不与杨仆共事,因此二将不睦。朝鲜人见汉将彼此争功,也就心存观望,不肯便来投降。
事为武帝所闻,心想将帅不和,必致误事,遂召到前济南太守公孙遂,命其前往军中,决定和战,并许以便宜从事。公孙遂奉命行到朝鲜,先至荀彘军营,见了荀彘,问以军情。荀彘道“朝鲜当破久矣,所以未破者,只因屡次与楼船将军约期会攻,楼船将军不肯进兵,以致误了军事。据愚见推测,楼船将军初与敌人交战大败,已犯失军之罪;今又与朝鲜私自和好,却不见朝鲜到来投降,谅系有心反叛,若不急行设法,恐其密与朝鲜通谋,共灭吾军。”公孙遂听说,十分相信,遂亦不向杨仆问明,竟与荀彘议定一计,遣人持节往召杨仆,速到左将军军营会议军事。杨仆与荀彘生有意见,本不肯到他营中,今因使者相请,坦然到来。谁知公孙遂一见杨仆,即喝令荀彘部下,将杨仆拘执,软禁军中,一面遣人持节晓谕杨仆部下,统归荀彘率领。杨仆部下见了使节,以为使者奉诏行事,谁敢不服。公孙遂事毕,辞别荀彘,回京复命。
荀彘既兼统两军,便下令将王险城四面围住,日夜架起云梯攻打,朝鲜大臣路人、韩阴、王唊等,见事势不佳,相率出城投降。过了一时,尼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