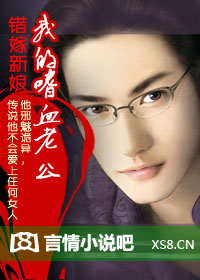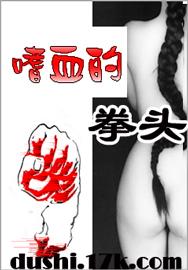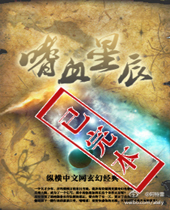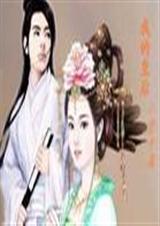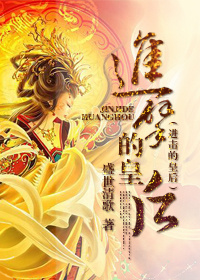嗜血的皇冠--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秀挣开刘良的手,眼盯贼首不放,大声道,“大丈夫是否应当言而有信?”
贼首遭此没来由地一问,颇觉诧异,道,“这是自然。”
刘秀道,“那么敢问,既然你已答应全了我们性命,却为何又出尔反尔?”
贼首道,“此话怎讲?”
刘秀道,“你们将车马悉数抢走,留我们在这荒郊雪地,无水无食,无火取暖,无衣御寒,不出半日,非冻死便饿死。君虽不杀我们,却胜似杀了我们。”
贼人斥道,“小子大胆!”便要来殴打刘秀。贼首止住,沉吟片刻,道,“少年所言有理,我等只求财物,岂可妄害人命,多造冤孽!且留下两车,令其可以前行。”
贼人无奈何,只得依了贼首,又对刘秀嚷道,“还不多谢头领!”
刘秀站得笔直,双唇紧闭,一言不发。刘良急忙拉扯刘秀的衣袖,示意他道个谢,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刘秀只是不理。
贼首奇道,“少年人,为何不愿道谢?”
刘秀道,“本为我物,复还与我,为何要谢?”
贼首哈哈大笑,拍掌叫道,“好胆气。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刘秀道,“从沛国来,回南阳去。”
贼首点点头,道,“说到南阳,我可有一人认识。”
刘秀道,“敢问何人?”
贼首道,“你等既是南阳人,想必一定听过我的朋友刘伯升。”
刘秀大惊,道,“莫非是大汉宗室、高祖之后刘伯升?”
贼首肃然道,“正是此人。我的朋友刘伯升,性情刚毅,慷慨激昂。自王莽篡汉,怀复社稷之虑,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豪杰以此争相投奔。大英雄固当如是哉。”说话间,一脸的景仰向往之情。
刘秀道,“实不相瞒,刘伯升正是某之长兄。”又介绍刘良道,“此乃某之叔父,因朝廷罢免诸刘,此番以萧令致仕返乡。”
贼首慌忙下马,向刘良拜倒,连连请罪。
刘良连忙扶起,道,“这怎么敢当。还没请教英雄尊姓大名。”
贼首道,“我等迫于生计,这才干了劫道的营生。岂可再报姓名,以辱父母。”
刘良道,“听英雄方才所言,想来和伯升相交已久。”
贼首窘迫起来,尴尬笑道,“真人面前,不敢假话。我和刘伯升实不相识。只为他广交豪杰,威名远扬,是以无论识与不识,都习惯称呼他为我的朋友刘伯升,以显亲热之意。”又指了指刘秀道,“这位小兄弟遇事镇定,气度非凡,不愧为刘伯升之弟,日后必定也是英雄。”说完,又命手下将财物复归原位。
刘良象征性地客套了两句,道,“无碍,无碍,尽管拿去。”贼首自然不肯,又道,“前方也不太平,请许我等护送。”于是护送刘良一家,直至进入南阳境内,这才告别回返。一路之上,贼首终不愿透露自己姓名。
经此一番死里逃生,刘良不免暗呼幸运,虽然对刘秀方才的表现印象深刻,可还是忍不住又教训起刘秀,道,“你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味逞勇,不知利害。今日只是侥幸,日后还是别惹事为宜。”
刘秀含糊应了一声,并不反驳。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可谓是又喜又狂。喜的是,数年不见,长兄刘縯居然已经折服群雄,威震一方,让他倍感骄傲。狂的是,他不断自问:难道我真的可以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刘良说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才有胆和贼首叫板,刘秀心里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当深陷贼人包围之时,他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信心,认为自己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死掉。他心里的那个秘密告诉他,别说是面对数十名贼人,即便是面对数万名贼人,他也照样可以逢凶化吉,安然无恙。
光武皇帝卷一“努力”NO。3:
陌生的故乡
刘秀再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注①),见到了久违的家人(注②)。说起来,南阳郡蔡阳县舂陵乡虽然是刘秀的故乡,但刘秀对这里的了解却并不多。他出生在济阳,后来因为父亲的职务调动,跟着再迁移到了南顿,父亲死后,又跟随叔父刘良到了萧县。在他十六年的生命里,真正在故乡度过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年,对于故乡,他是情感上的亲切、事实上的陌生。
第3节
这次刘秀和叔父刘良回来故乡,看情形是要长住了。既然要长住,自然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考虑。对刘秀这个暂时还没有能力自立的半大孩子来说,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跟着谁过?是继续跟着叔父刘良还是回自己家?
选择权并不在刘秀的手中。按照刘良的意思,是愿意继续抚养刘秀的,刘秀对他来说,和亲生儿子已经没有区别。但刘秀的长兄刘縯坚决不肯同意,执意将刘秀接回。此时的刘縯,已经代替他死去的父亲,扛过了家庭的重担,担当起了长子的责任——赚钱养家、孝敬寡母、照顾弟妹。
从刘秀的个人情感来说,他自然也希望回到自己家中,和母亲及兄长姐妹朝夕相处、一起过活。而刘縯坚持要把刘秀留在自己身边,无疑也让刘秀倍感温暖。换个兄长,也许就顺水推舟,把他丢给叔父刘良,免得再给自己多添一个负担。
刘秀回家没几天,便已经敏感地觉察到,自己家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
俗话说,皇帝也有几门穷亲戚。刘秀一家,应该可以算得上是这些穷亲戚中的一门了。如我们所知,到了刘秀这一代,和皇室的血脉已经非常疏远。从刘秀的太爷开始,便已经失去爵位,主要收入只能来自做官的俸禄。从太爷郁林太守刘外,到祖父巨鹿都尉刘回,再到父亲南顿令刘钦,官越来越小,俸禄自然也是越来越少。父亲刘钦之死,对刘秀一家的财政状况可谓是一次致命打击。首先是失去了每年固定的千石左右的俸禄收入,而更重要的是,刘钦的葬礼,几乎将他全家多年的积蓄尽数搭了进去。
西汉时期,流行厚葬,又有攀比之风。崔寔《政论》云:“天下跂慕,耻不相逮。”恶性攀比之下,最终导致“虚地上以实地下”,《盐铁论…散不足》云:“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崔寔《政论》云:“竭家尽业,甘心而不恨。”
刘钦的葬礼,使得刘秀一家元气大伤。到了刘秀这一代,无人仕宦,收入只能来自老家的田地。其田地规模史无明文,但想来也不会太多。
只要量入为出,日子总归是过得下去的。毕竟,比他们家境更差的多了去了。然而,偏偏当家人刘縯又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主,日子自然是一天一天地窘迫下来。
是的,早在刘秀回故乡之前,刘伯升就以“我的朋友”名闻遐迩,威震南阳及周围郡县。但不厚道地说一声,他这点名声,就和宋江一样,大半还都是靠钱砸出来的。
和宋江不同,刘縯乃是胸怀大志之人。自从王莽篡汉,他便立誓要夺回高祖打下的天下,恢复大汉江山,于是广交豪杰,大养宾客,以待他日之用。
广交豪杰,大养宾客,离不开“信”,离不开“义”,更离不开钱,而且是大量的钱。《后汉书…郑太传》云:“郑太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以郑太之富,尚且食常不足,何况是刘縯这样的中衰之家。纵然刘縯苦苦支撑,但长日久之,只出不进,怕也只有倾身破产一途。
然而,就算是肿脸充胖子,刘縯也必须硬撑下去。更何况,早有相士说过,他的面相酷似当年的高祖刘邦,刘縯也因此心中暗喜,隐以刘邦自许。是以,虽然金钱捉襟见肘,刘縯非但不加收敛,反而是场面越铺越大。
那么,刘縯家养的这些宾客都是些什么人?吃白食的吗?吃完白食之后,是帮忙、帮闲,还是帮凶呢?
注①:
刘秀的谱系:
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长沙定王刘发——舂陵节侯刘买——郁林太守刘外——巨鹿都尉刘回——南顿令刘钦——刘秀。
关于刘秀这一宗刘姓支脉的渊源及迁移到南阳的经过:
汉景帝刘启生长沙定王刘发。汉武帝刘彻时,行推恩令,长沙定王刘发的次子刘买因而得封舂陵侯,封地为零陵郡泠道县舂陵乡。刘买之孙为考侯刘仁,获当时皇帝汉元帝恩准,率整个宗族(自舂陵侯刘买繁衍而下)于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迁移到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因改白水乡为舂陵乡。
注②
刘秀此时的家庭成员包括:母亲樊娴都,长兄刘縯,二哥刘仲,大姐刘黄、二姐刘元、妹妹刘伯姬。
光武皇帝卷一“努力”NO。4:
但使主人能醉客(一)
豢养宾客之风,由来已久。上溯两百多年,前有战国四公子,后有秦国吕不韦、嫪毐。及至汉际,此风尤盛,惟人数及规模不逮前朝,其最多者,只在千人左右①。同时,豢养宾客在汉代已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一些低级官员,乃至平头百姓也都有可能招纳宾客。
养客者众,于是便有了争夺客源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和那些势大财雄的王侯豪族比起来,刘縯无疑处于弱势地位,他要想以弱胜强,只能细分市场,不求天下宾客尽入我毂中,而是先以其中一类宾客为突破口。
刘縯选中的这一类宾客便是——亡人和逃犯。
亡人和逃犯,或为仇家追杀,或为国家通缉,一旦收留这些人做宾客,无异于惹火上身,弄不好,连主人自己都得跟着陷进去。所以,对于这群人,一般养客者总是敬而远之。
人弃我取,刘縯便先从这群人招揽起。况且,刘縯他豢养宾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造反。这群人既然连人都敢杀,难道还怕造反?
消息传开,亡命之徒纷纷来奔,刘縯“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不出几年,便聚集了数百之众。
看官问了,这天下不是还没大乱吗?哪来的这许多杀人之徒?
杀人者,或为复仇,春秋有复仇大义,延绵至汉,复仇之义不衰;或为任性使气,其时民风尚武,尚武则易于炫耀武力,一次口角,一次侮辱,一个眼神,都有可能导致命案的发生;或为抢夺财物,作奸犯科,不一而足。
杀人之徒众多,固然有杀人者的主观因素,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受到了国家的怂恿和鼓励。
一个国家,居然会怂恿和鼓励杀人的发生?然而,似乎还真的是确有其事,问题就出在汉代的频繁大赦上。
据杜钦《汉代大赦制度试释》统计:西汉大赦八十七次,平均两年半一次大赦。王莽一朝大赦九次,平均二十个月一次大赦。频繁的大赦,完全破坏了国家正常的司法秩序,使得法律的威严几成儿戏。
换而言之,如果阁下你杀了人,在西汉只需要逃亡两年半,在新朝只需要逃亡二十个月,然后便可以一切重新开始。如果当场被抓了现行,那算你倒霉。如果没有当场被抓,那就好办了,逃呗。可别说你逃都懒得逃,你还是得逃,你得给官府这个面子,不然,你杀了人照样在原籍大摇大摆地晃悠,官府想不抓你都不好意思。你这一逃,自然需要有个落脚的地方,能至少每天管顿饱饭,睡个好觉。嗯,听说南阳的刘縯不错,道上的人都称他为“我的朋友”,他那府上,号称是风能进,雨能进,官府不能进。伙食差点,床铺硬点,没问题,瞧咱这身体素质。哦,这位仁兄,你刚刚也杀了人,那好,同去,同去。于是同去。
话说回来,做宾客其实是一个相当轻松愉快的职业。他们并没有特定的义务,一般也不从事家务或者生产。而且,他们还保有随时离开的自由。在刘縯这里,碰见大赦,有些宾客便会选择离开,唯一的贡献便是帮助刘家消灭了不少粮食。对这些人,刘縯笑脸迎进,照样也是笑脸送出。而大多数宾客,却仍然会选择继续留下。
宾客被豢养久了,内心难免不安。所谓受人钱财,理当替人消灾。但主人家偏偏也没什么灾,而他们也不能暗中祈祷主人家遭个灾什么的,好让自己因此能一展身手。于是都憋着劲,就等着刘縯一声令下。
要的就是这效果。
但使主人能醉客(二)
刘縯提供给门客的待遇,自然不可能像战国四公子那般奢侈——平原君之门客,“刀剑室以珠玉饰之”;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然而数百门客的衣食住行,即使仅仅维持在一个温饱水准,其花费也是可想而知。
形势比人强,不管刘縯有多么虚荣,多在乎自己好客的名声,在现实面前都不得不低下他高傲的头颅,开始组织门客生产自救。
不过麻烦的是,门客们携带而来的,不仅有他们身上的命案,而且还有他们敏感的自尊。如果让门客象农夫那样在田间耕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无疑将会招致门客们的强烈愤怒,认为是对他们极大的侮辱。考虑到他们回应侮辱的方式,很明显此路不通。
从投入产出比来看,种田也并非一个很好的选择。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什么,经商来钱还是太慢?那你还不如去抢了。
没错,刘縯及其门客正打算去抢。他们多的就是暴力,有暴力,当然就要追求暴利。
第4节
他们首先瞄准的行当就是盗墓。西汉流行厚葬,每座稍有级别的坟墓,都好比是一家地下钱庄。从道德伦理上讲,盗墓未免有些下流,需要做通门客的思想工作。刘縯于是以郭解来举例,那可是汉武帝时最著名的游侠,无数江湖豪杰的偶像,也曾经靠盗墓来豢养宾客。门客们顿时没了声响,既然郭解都做过这事,可见这事并不丢人。
抢完死人,再来抢活人。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有道路的地方,就有人流,人流未必无痛,但却一定有钱。刘縯等人瞄准的第二个行当便是劫道。至于劫完道之后,顺便劫个色什么的,这种事情,咱们并不敢说一定没有。劫完道之后,遇见胆敢反抗的,顺便捅上那么几刀,这种事情,咱们也不敢说一定没有。
幼蒙师训,曰:远不赌,近不嫖。盗墓和劫道这两件事,当介于赌嫖之间,不宜太近,也不能太远。
太近,遭殃的大都是同乡之人,于心不安,且容易暴露行迹,传出去名声不好,既然要在本地长混,便不得不顾忌本地舆论。
也不能太远,差旅费用倒是其次,主要是不安全。各地皆有强宗豪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