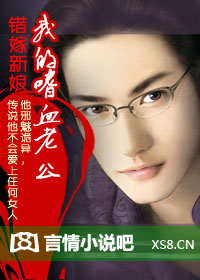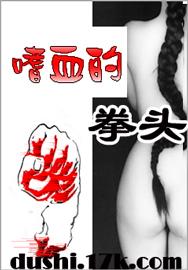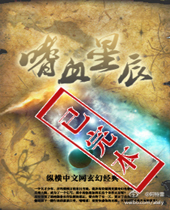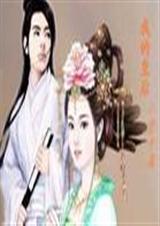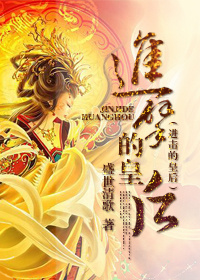嗜血的皇冠--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氏宗庙前的高台之上,环布烛火,亮如白昼。小孩最先赶到,接着便是妇人。而那些躲藏起来的刘氏子弟,也如幽灵般纷纷现身,偷摸着前来,既然刘秀花钱白请看戏,岂有不看之理。况且,对这些小地主和破落户来说,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庙前去看百戏,实在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凄美。
入夜时分,台下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精明的小贩在人群中往返穿梭,叫卖着玩意瓜果。
百戏,仿佛今日之杂技,为当时的重要娱乐。时辰到,音乐起,两人吹萧,一人奏茄,一人击鼓,百戏正式上演,虽然都是一些传统伎俩,譬如举鼎寻橦、吞刀吐火、飞丸跳剑等等,但仍是看得人提心吊胆,大叫过瘾。
迅哥儿当时也在场,其时盛况,先生后来在《社戏》一文中回忆道: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不过迅哥儿当时离开得早,后面的戏并未看到,今特此补记,聊慰先生之憾。
且说迅哥儿走后,惊险刺激的百戏很快也便耍罢,高台为之一空,久无动静,连乐队也停将下来。台下屏息静气,满怀期待地看向空台。百戏固然精彩,但只如正片前的加映,拳击里的垫赛,接下来,应该更有好戏。
良久,一侏儒携一少年登台。侏儒高冠华服,俨然权臣,少年燕衣充冕,分明天子。两人来到台中,侏儒向少年行礼敬酒,少年推辞不肯,侏儒按住少年,强灌之。少年挣扎不得,饮酒入腹,顿时七窍流血,倒地不起。全程如演默剧,只见动作,并无言语。
台下多有票友,禁不住窃窃私语,这是演的哪一出?怎么以前未曾见过?再往下一想,不由悚然,莫非是在暗讽王莽鸩杀孝平皇帝?
第二幕,侏儒携一小儿复出,闭小儿于黑屋之中,小儿号哭,侏儒关门不顾。
票友们明白过来,这回是在说王莽禁闭孺子刘婴之事。平帝崩,无子,王莽选年仅二岁的刘婴继嗣,号为孺子,自己则践祚居摄,做起了事实上的皇帝。至于刘婴,王莽则将他常年锁于暗室之中,禁见外人,即使是刘婴的乳母,也禁止和他说话。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刘婴只能成为白痴,及其长大,连六畜也不认识。
思及孺子刘婴的遭遇,台下颦蹙有出涕者。
第三幕,侏儒坐于高阶,着天子冠冕,数侏儒匍匐参拜。无疑义,此乃王莽篡汉称帝是也。
第四幕,高祖庙内,居中立有汉高祖刘邦之像,侏儒入,拔剑四面提击,斧坏户牖,桃汤、赭鞭鞭洒屋壁。侏儒又立于刘邦像前,吐口水于地,和高大的刘邦像一对比,侏儒显得极为轻佻滑稽。
不消问,这回说的是王莽毁坏刘邦庙。此本为去年之事,诸刘未曾亲历,并不以为恨,但经今日这么一番情景重现,顿觉祖宗受辱,其恨莫名,台下男儿,尽皆怒发冲冠,瓜果鸡蛋,酒浆杯盏,但凡趁手的,抓起便往台上狂扔。
侏儒一边躲避,一边朝台下鞠躬作揖,终于开口说话道,诸位息怒,何必拿我撒气。真王莽在长安,有种寻正主去。
还敢顶嘴!诸刘子弟目欲出血,纷纷拔剑,便要奔上台去,结果侏儒性命。
日期:2009…1…131:46:52
光武皇帝卷一“努力”NO。54
大风
且说刘氏子弟纷纷拔剑,眼看侏儒性命不保,但听一阵巨响传来,宗庙大门轰然打开。刘縯率三百宾客鱼贯而出,皆刀剑盔甲,威武挺拔,恍如神兵天降,立时震慑全场。
在某些时候,男人更需要打扮。刘縯及其宾客,舂陵城中寻常可见,每每蓬头垢面,不修边幅,怎么看都像是弱势群体。然而今天戎装这么一穿,却俨然一副铁军威仪,令人望而生畏、心胆俱裂。
刘縯跃上高台,睥睨四顾,有不可一世之概。众人不知刘縯用意何在,均不敢动弹。刘縯指着侏儒,厉声对台下说道,“俳优所言,何错之有?真王莽健在长安,诸君皆七尺男儿,不敢寻王莽复仇,却偏和一侏儒为难,羞也不羞?”
刘氏子弟默然。刘縯之威,不容轻犯;刘縯之言,无可辩驳。
刘縯声调愈高,接着又道,“我欲与诸君同起义兵,共复汉室,诸君皆亡匿,道‘伯升杀我’。今高祖江山沦丧,神庙被毁,诸君但坐视而已,全无羞耻。人而无耻,不死何为?人而忘祖,胡不遄死?”说完,怒目环视台下,咆哮道,“我岂杀诸君哉!我岂杀诸君哉!”
台下诸人面有羞愧之色,不能回应。刘縯站得虽高,但他的话拔得更高,寥寥几句,便已榨出了众人皮袍下暗藏的渺小。
刘縯停顿片刻,目光在一张张面庞上划过,冷笑道,“王莽矫托天命,篡汉称帝,可怜刘氏,无不苟且偷生,自甘为新朝的孝子贤孙。刘姓诸侯,厥角稽首,悉上玺绶,惟恐在后;更有称美颂德以求容媚者,岂不哀哉!我倒想问诸君一句:所谓高祖后裔,究是龙种欤?跳蚤欤?”
台下一片死寂,众人之头颅,越发低了下去,不敢和刘縯的眼神接触。那是怎样悲愤的眼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刘縯手指宗庙大门,再道,“前此,我已于高祖神像前立下大愿,不惜一死,必举义兵,誓杀王莽。刘氏之仇,终须有人报之;刘氏之耻,终须有人雪之。诸君从我则可,有不从我者,縯也不敢相强,但请入宗庙,跪于高祖灵前,亲口告知高祖。”
众人感泣涕零,热血沸腾,那是刘邦之血,那是皇族之血。再滋润的小日子,在家国大义面前,都显得可笑而不值一提。是的,必须挺身而出,为夺回刘氏失去的天下而战,即使明知凶多吉少,但大义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义也。
正当此时,台上的高祖像猛地站起。众人惊惧不安,以为高祖显灵,连忙拜倒。高祖像口未张,却分明有慷慨之歌。
歌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声掠过众人耳际,在远山回荡,而众人的灵魂,也随了这歌声,在空中飘扬。依稀间,他们来到祖先刘邦的身旁,见证和分享着他那不世之荣光。
此歌正是刘邦所创《大风歌》,刘氏子弟从小习唱,其内容和旋律,早已是深入骨髓,今日骤闻此歌,皆忼慨伤怀,不能自已,不觉大声跟着合唱起来。
高祖像再歌,歌云:“大风起兮云飞扬,贼子窃位兮家国丧;安得儿郎兮复家邦!”①歌声改慷慨为悲凉,易惆怅为寄望,众人感激泪下,复又合唱。
歌声未绝,高祖像忽卸去面具衣装,赫然乃是刘秀,着绛衣大冠,和刘縯的装扮一样。众人见刘秀也加入到刘縯的造反,皆惊道:“谨厚者亦复为之!”仿佛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心下大安。多年来一起成长的经验表明,但凡刘秀看准的事,一般都比较靠谱。
见众人已然臣服,刘縯拔刀大叫,“高祖有训:非刘氏不得称王。不然,天下共击之。诸君从我否?”
众人眼睛已血红,情绪已失控,闻言齐声回应:“愿从,愿从!”
刘縯举刀高呼:“大风,大风!”
众人随之皆拔刀剑,齐呼:“大风,大风!”
此处大风二字,虽脱胎自刘邦《大风歌》,但作为口号,却另有意思。此风,乃牝牡相诱谓之风,即性冲动之意,于是有风马牛不相及之说,即马和牛只对同类发情,不可能交媾在一起。所以癞蛤蟆只想吃天鹅之肉,并无意剥天鹅之衣。不知何时,此风渐渐由名词演化为动词,由性冲动变为性行动,于是成为一句类似于今天的日这一类的脏话。大风,大日也。
钱钟书先生道,无亵不笑。也就是说,所有的笑话之中,只有荤段子最可乐。借此句式,也可云,无脏不壮。只有话中带脏,气势才足够雄壮。是以刘縯大风一讲,刘氏子弟无不激昂。
看戏时习惯于叽叽喳喳的妇人们,闭上了嘴巴,惊慕地看着这一群风了的男人,发了情的男人。她们知道,她们的男人要去战斗了,为了祖先的荣誉,为了自身的尊严,从此寄身锋刃,浴血沙场,宁死不惜。眼下这点可怜的小生活,他们已经不再在乎,不再眷念。妇人们对此无法理解,她们来自火星,很难明白荣誉和尊严对于这些男人的重要性。
叔本华曾经刻薄地写道:女人的本质便是轻佻漂浮,目光短浅,毫无正义感,她们只能注意到眼前的事物,留恋的也只是这些,至于抽象的思想原则,固定的行为准则,坚定的信念,只是男人的专利,对女人则毫无吸引力可言。②然而,叔翁此说过于恶毒。君不见,在男人们铺天盖地的喊日之声中,妇人们也是热泪盈眶,备受感动。面对一群男人发风,你根本没法不感动。
夜已深,月明星稀,火光冲天。而这一夜,也是舂陵和宁静平凡告了别的一夜。事情就此定局,舂陵的刘氏子弟,将团结在一起,勇敢地迎接战斗。从此沙草晨牧,河冰夜渡;从此地阔天长,不知归路。
在众人欢呼喧嚣之时,刘秀悄然退至一旁,拉住我问,“这就造反了吗?”
我回答道,“莫非你嫌太快?”
“不,是嫌慢。”刘秀说完,又加重语气,几乎是在抱怨道,“岂止是慢,简直就是磨蹭。”
我无奈一笑,道,“然而,毕竟还是开始了,不是吗?”
“是啊,”刘秀叹道,“你会跟随我吗?一直到这路的尽头?”在他二十八岁的脸庞,流露出八十二岁的苍凉。
我只能点头,道,“不然,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刘秀释然下来,转身离去。我叫住刘秀,刘秀回头,等我说话。我想了想,最终说道,“文叔,努力!”
刘秀开心一笑,握紧拳头,道,“嗯,努力!”
①此处似乎存在一个没有避讳的BUG,按理刘秀是不能直接说“邦”字的。但实在找不到押韵兼达意之字,且先将就,有待高明。
②参见叔本华《论女人》一文。
第46节
日期:2009…01…1502:02:31
光武皇帝卷一“努力”NO。55
赤眉
刘秀兄弟起兵之时,他们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南阳,东方青徐二州的战事,同样吸引着他们的注意,樊崇武装正在那里牵制着王莽的主力部队,战事拖得越久,对他们来说便越有利。
本年四月,新朝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精兵十万,正式开拔青徐二州,力求毕斯功于一役,彻底解决樊崇武装。王莽亲自为二人壮行,送之都门之外,时天降暴雨,水漫征衣。见此不祥之兆,有长老暗叹道:“是为泣军!恐儿郎们不得归家也。”
大军抵达东方,樊崇主动邀战,预备给官兵来一个下马威,又担心乱战之中难分敌我,命士卒皆染红眉毛,以相识别。著名的“赤眉”之号,从此而来。
然而,出乎樊崇预料的是,官兵采取了田况曾提出过的坚壁清野之策,避而不战。据守重要城池,多藏谷食,并力固守,是为坚壁;散居民户,徙其人与财货,置于城中,是为清野。
很显然,坚壁清野并非王莽所好,一上来就摆出一副防御挨揍的姿态,怎能显出天朝的威风?田况正因为提议坚壁清野而被免职,谁还敢顶风而上,扫王莽之颜面,批天子之逆鳞?
廉丹敢!决定坚壁清野者,正是更始将军廉丹。廉丹,乃赵国廉颇之后,身经百战,功勋显赫,在当时最为名将,威望无人能及。此时的廉丹,已届花甲之年,老眼愈发毒辣,一入青徐,便知田况之计,实是最佳策略。
太师王匡,乃是王莽之侄,最明白王莽心思——这场仗不仅要打得赢,而且要打得硬。王匡虽然名义上是主帅,但年纪刚三十出头,毕竟资历尚浅,和廉丹一比,只能算是黄毛小儿,又慑于廉丹的赫赫威名,因此并不能公然反对坚壁清野,只能默许。
然而,坚壁尚可,清野却副作用极大。官兵所到之处,抄掠抢夺,蹄骨狼藉,其凶残比赤眉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青徐二州民谣所唱:“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乱世百姓之苦,古来皆然。民国初年,四川也曾有民谣道:“匪是梳子梳,兵是篦子篦,军阀就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扒皮。”
部下放纵滥杀,廉丹非但不制止,反而故意纵容。慈不将兵,义不掌财,在廉丹看来,战争的逻辑本来便是残忍的:这些散布野外的老百姓,如果官兵不抢走他们的粮食,那就一定会被赤眉抢走;如果官兵不杀害他们的性命,那他们就有可能被胁迫加入赤眉军,反过来对付官兵。一时的仁慈不忍,只会便宜赤眉,祸害自己。
所谓坚壁清野,打的便是消耗战、持久战,然而到了十月,见官兵全无战果,赤眉还在逍遥,王莽的耐心终于用尽,给廉丹下了一道诏书。
诏书共十六字,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
自古诏书,无有奇过此诏者,接连叠用四个“矣”字,丝毫不显累赘重复,反而急迅错落,笔下似见叹息,纸上如闻愤怒,读来不由击节。想来王莽腕中有鬼,方可作得此般奇文。
王莽文章虽妙,廉丹却无心鉴赏,更无诏书下酒的逸致。作为王莽的老臣子,他太明白这短短十六个字的份量了。廉丹接诏,大为惶恐,连夜召掾吏冯衍,以书示之,叹道,“陛下震怒,诏书责问。某受国重任,不捐躯于中野,恐无以报恩塞责!”
冯衍见廉丹大有破罐子破摔、战死给王莽看的意思,连道不可,劝廉丹不如干脆割据一方,等待时机,道,“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厉其节,纳雄桀之士,询忠智之谋,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
廉丹苦笑道,“此话休再提起。”冯衍书生之见,割据叛变哪有这般简单!且不说他在长安的家族性命不保,单说他如真要割据,十万大军的大部分还是掌握在主帅王匡手上,这他带不走,而他统领的三万将士,又有多少人真的愿意跟着他背叛朝廷?
廉丹接诏不久,东平郡无盐县县吏索卢恢等人结接赤眉,据城而反。王匡见廉丹遭诏书谴责,胆气大壮,力主进攻,廉丹不得已跟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