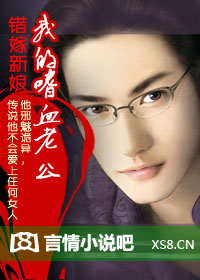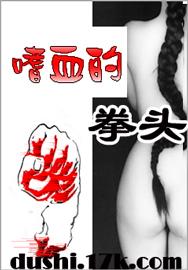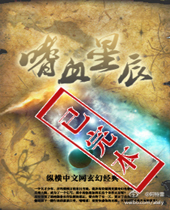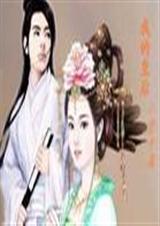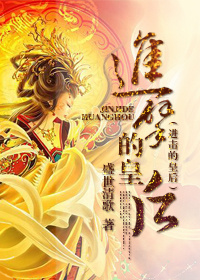��Ѫ�Ļʹ�--����ʵ�֮�������-��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Լ��ľ�ϲ��
�ڴ�֮ǰ��������Ϊһ��С�к���������Ҫʹ�����Dz�Ҫ��ǰز�ۣ�Ȼ�������س��������ë�������ڲ�ͬ�ˣ����Ѿ�ʮ�����ˣ���ֵ�ഺ�궯�ڣ��������ȶ࣬��Ҫ�㹻�ķ�й��ת�ơ�
��ͥ��Ȩ�����������ڳ������t����������tҲȷʵ������һ��֮�������Σ����������չ˵úܺã��������չ˵�̫���ںã���������������ã���������Լ������������κ�һ�㱧Թ�Ͳ����Ļ�����ֱ������������������ʵ�����еûţ�������ѰЩ�������������
�����뵽���Լ������游���أ�����ũ�ڣ������¸�����������Ȼ��������̫ѧ������Ϊ������Ҳ���������⣬�ǻ�������ѧѧũ�ڣ��պ�˵����Ҳ�������游���������������¸�������һ�����������tҲ�Ͳ�����ΪȱǮ�������ˡ�
��������ǰȥ�����t��������������ͬ�⡣���t���գ����һ�����������ν⣿��
������֪���t���Լ���һƬ����֮�飬Ҳ֪�����tΪ��������Ѿ��߾����ܣ����Բ���Ը¶�Լ�����ʵ�뷨�����������t�ĸ��飬���ֻ���ſڴ��������������Ҳ�����š���
���t�����ҡ��ҡͷ���������������ĵܵܣ���ô������ũ�б�����ô���ң�����˵ʲôҲ���ɡ���
���������ũ�ڣ�����Ҳ�����游��Ҳ�����ٳ��𣿡�
�������һ�仰���㱻���t�����˳�������ζ�����t��ŭ���������˵������֮��Ϊ������а���ˣ���
����û�ϵ����t��Ӧ����˼��ң�ֻ��������ʾ�Լ������⡣���tȴ�����������ͣ������Թ��Ե�˵��û�꣬ʲô�ɴ����߲���С�ڡ�֪����ν�����ǣ���֪����ν�ұ�¶��ʲô���Ʋ��죬�˺����գ���Ȼ�鵶��ˮ������������ʹ�˳ʲô���˱���֪�����˶����ã���Ϊ���ʣ����߽Կ��ס�ʲô����Ϊ���գ��Ҳ�����Ҳ����С�������ȥ����ߣ���ǧ���ˣ�����Ҳ��
����ֻ�����ţ������t�ݽ���ϣ����С��˵���������Ҳ�ѧũ�ڱ��ǡ���
���tҲ��ʶ���Լ��ղŵ�ʧ̬�����̱��侲��������Ц�������㲻�뼱���һ����㶼���źõġ�������ʵ���е����ģ��Ҵ˿̻�����һ�£�Ҫ֣�ذ��и��㡣��
�����ϲ��æ��ɶ���塣���t����������Դ�����ɫ˵���������ҸϽ���������
�����ʱ�����߳ߣ���ͬ�������䲻���㰫���������߰˳��ߴ�ij������t��������ȴʵ�����е㲻�ߡ����t���Ϸ��һ�����ֵ��������Ӵ�Ц��
�˺������ٲ�����ѧũ��֮�¡���ż��Ҳ��ȥ����ͷ������ũ�Dz����ո���Ӳ��µء������ʱ�䣬�����Ǻ����t���ſ��ǻ���һ��ѧϰ�鱾��ѧ�����Ķ�����ij�̶ֳ��ϣ�����һ����õĴ�ѧ���ſ��������������������ſ��Ƕ�����Ҳ���ҵ���������ү����ÿÿ���ʱش�����ѧ��Ҳ���������ڡ�
����ʵ۾�һ��Ŭ����NO��7��
��ү
������⣬����⣬��ү�ſڳ���Ϸ���ӹ����Ů����С����ҲҪȥ������ͯҥ�������š�
�Ժܶ�С����˵��ÿ��ȥ��ү�ң�����һ�ο��ĵľ��������㵱ȻҲ����ү��������ү�շ����أ��־��ƣ���ס�����������أ��ڵ�������һλ�պ������Ĵ������
����6��
���ؼ��о���ͷ�ԣ���������ң�һ�����һ�������������Խڼ����������������ڹ���������ͯ�����������ˡ��������������ļӼ沢��ӵ������Ѷ���������꣬�Ͻ������Ķ���Ƹ�Ҳ��Խ��Խ�࣬��������һԾ��Ϊ����������ʹ����������Ҳ�������ĸ����˼ҡ���ͷ������ѹ���ϡ֮�꣬������Ȼ����úܣ��±ع��ף������������������ܶ�С���Ӷ����Ƕ��֡�
���ǣ������С�Ͳ�����������������游����������ͷ�Ӳ������ɰ��������ܱ�̬���ڼ��������ڶ�ɭ�ϵĹ�أ������������Ҫ�����������밲���⣬���ڹٸ��칫һ�������ѹ�ֵĻ�����Ҳ�ѹֲ���С�����ϲ����
��ͷ���ڼ������ž��Ե�Ȩ�������д�Ȩ��������һ��֮�֡��غ�ʱ���ļ�ͥ��һ�����ӽ�飬������Ӽ��зֵ�һ�ݲƲ���Ȼ���뿪��ĸ�����Ż�����Ҳ�;����ˣ��غ�ʱ���ļ�ͥ��һ��ֻ����������ɡ�Ʃ��������������常��������ʵ�Ͼ��������ˣ�����ס��һ�𣬶��Ǹ������������
������һ�ң�ȴ�Ǻܺ������������ƣ����ӷ��ص����Ķ��ӣ��ٵ��������ӣ���δ���ּң�����ʼ����һ��ͬ������غ�ʷ���ϣ������й�������ͬ�ӹ��Ƽ��صĽ��е�����֮һ����
���������ڸ��ӷּ����ǵ�ʱ��᳣̬������£�Ҫ�����������ƣ���ͷ��һ��Ҫ�㹻ǿӲ��ͬʱ�ڵ�ƽ�����ˣ���������Щϣ�������Ķ�ϱ������ϱ���ǡ���ͷ�Ӳ��Ϸּң���������ϵĿ��ǣ����о����ϵĿ��ǡ�������Ի���������裬����Ƽ֡���ͷ�ӵ�Ȼ��������������Ƹ��ļ��У������ڸ������Ч����������ؾ�ȡ����IJƸ�����һ�����ɶ��Ӻ����ӽ��Ҳ���ȥ���Ƹ�����Ϊ�㣬��ģЧӦ���ʹ�ʧȥ��
������ĸ�ĸ���ʱ���ϸ��˵���Ƿ��Ҹ��������ҡ�������Ȼ��Ǯ���վ�ֻ��ƽ��������ȻǮ���࣬ȴ�Ǵ����ң����Ҵ����˻£�ӵ��ƽ���ĵ�λ��Ȩ����
ʱ����Ǩ������Ҳ�����ƽ���ҼҲ�Ҳ�����t������ˡ�һ��һ���������˼���Ҳ������ͷ�ӷ�Ⱥã��������ΪŮ���������Ż��£����ܲ�ס����������̬�����˱仯����ʼ������һ�������������ܻ�������Ҫô������Ҫ���ͱض���Ҫͼ���Ǽҵ�ʲô����ˣ����������������ү���档
�������ط���������������ڣ����������ĸ�װݷù�һ����ͷ�ӡ���ͷ�Ӻ�����Ҳ�����ǣ����ڵ�һ�仰���ǣ�����������ܼ�����ôû������
�������t��������Ϊ����ͷ���Ǻܲ���ΪȻ�ġ���ȫ������ͷ�ӿ����㲻��ʲô�����ں������С�ط���������һ�����绽��Ĵ�������ң������н��յijɾͣ�ȫƾ�Լ����ǻۺ�Ŭ�����������������ɸе��Ժ��ͽ�������Ȼ���;������������Ҳ����һ���ɹ�����һ���������Լ��ijɾ����Ź��ߵ����ۣ����Լ�������Ҳ���ų���ʵ�ʵĿ����Ҳ�����뵱Ȼ����Ϊ������������˵ijɹ������˶�Ӧ�ú������ɵ�����ѧϰ�����������߹��ĵ�·��
��ˣ���ͷ�Ӷ��������t�Ķ�������ʹ�ļ��ס�������Ϸ���һ�����ޱ����ظ�̾��������Ī��˹��Ҳ����Ϊʲô�������Ҹ���ָ������������
��ͷ�ӵ��������ȷ��ʶʱ����Ϊ���ܣ������Ѿ��������£���Ӧ�����������������ٶ�ؽ�ɽ�����Ǹ��������ܵġ�����ͷ����ν�����������ǣ����������Կ࣬��������Ǯ�������������ơ����پ����أ������ȷ�������繫�������ˣ������Ҳ��
����ļҾ�������ԣ������ͷ�ӵ�Ȼ֪��������ͷ�ӷǵ�֪�����ȣ����һ���������ˣ��Ƥ�ӣ������������һ����������һ��������ͷ�����ˣ�����߶����Ʋ��ˣ���ȴ�����DZ߸��һ����伢���㲻��Զ�������Ĵ������𣿲����������壬�������̣����һ����ʱ�������������ķ�ծ�ʹﵽ������֮�ࡣ��ô����������ǰ���ͱ��һë�����ˣ��ڻݶ�ʵ������ɷ�ǿɺޡ�
���㲻����ô�롣����С�Ͷ����ˣ���ү������Ǯ����Ҳ����ү�ҵģ����շ��ģ����������ġ�
�ڵ�ʱ��Ů����û�м̳�Ȩ�ġ����ص�Ǯ�������ĸ����û��Ȩ���ֵģ���ˣ����ص�Ǯ��ȷʵ������һ���ϵҲû�С�
�����š��������˵�������Ե��ϵ���ֱ�Ϊ���塢ĸ�����������ݡ�һ������������������ĸ����ĸ�����������������������ݡ�������˵�����صĶ��ӷ��꣬Ҳ��������ľ˾ˣ�Ȣ������ȴ�����͵����ã�������������������֡������������Ĺ�ϵ������Ҫ�ܷ�������Ž���㡣�������ĸ���Ĺ�ϵ��������ùܷ�������Žо��衣��������������ĸ�����������㲢����ܷ�������Žо��裬����ֻ�ܳƺ���Ϊ��㡣
����Ϊ�ˣ���ijһ����ͥ������������������Ԯ������ģ�ͨ���������壬Ȼ���������ơ�����ʵʩԮ���ϣ�Ҳ��ͬ����ˡ��Է�����˵�������Ҫ���оȼõĻ���Ҳ��Ҫ�ȴ��Լ������忪ʼ��Ȼ���ٵ�ĸ�����������ơ������������Ե�����У�����ĩ��ʹ���˽��죬���ܻ��ǻ��кܶ�ͬѧ�й����ָ��ܣ���ү���۵�������������Ů���������㡣�����ʵ�ɣ���Ϊ���������һ���յġ����游���������˼�壬�˴��վ�ֻ�������ѡ�
��˵�ˣ����ص��������ֹ�����ֵ����������к����ֵܡ������ֵܲ��Žᣬ���������س�֮��������������ϡ�һ�س����˾٣��ƾٷ���Ϊ�����ϣ����ƽ̻���
�ɴ�Ҳ���Կ������Ӳ����Ͼ��������������Ϊ��ү���뾡�����Ρ�����ã�����һ�£�����ֵ�ó������⡣���鲻�ã���������Ҳ������������˶�������֡�
���ز��������t��ԭ���Ƕ��ġ�һ�Ǵӷ���ϰ���ϣ��������Ͳ��ؾ��������tҲ�������������þ������t�ģ������t�������������塣�����������Ͳ���ͬ���t����Ϊ����������Ϊһ�����ˣ����Ͼȼ�������ĵ��������t���ֺýŵģ�ȴ�������������ֺ��С�һ��������Ǯ���������Ͷ��������������������˵���ȥ��
�ۺ����ϣ����DZ㲻�����⣬Ϊʲô���t������ôһλ�������͵���ү��ȴ��ȻҪ��������ȥ��Ĺ�ٵ����Խ���������⡣
��һ���棬���tҲ��������������ͷ�����������Ѿ����겻����ͷ�ӵ����ˡ�����������ͷ�ӵ���߶����������ͷ�ӱ�������������Щ��ν�������ǻۺͳɹ���������׳־���Ƶ����t���У���ͷ�Ӿ���һ���������̣�������գ�
���غ�ʱ�ڵļ�ͥ��ģ���֮С����ʱ�ķ����ƶ���һ��ؼ����ء��ع������������������У������ж������ϲ������ߣ����丳�����������ֵ�ͬ����Ϣ��Ϊ�����������ķ��ɣ����������³��õ��˼̳С�����ϸ�ķ�������μ���ͬ�������ġ��������ṹ����
����һ�����ڡ����顭���ߴ������������ߣ����常���ӵ�ͬ�ӣ��������ֲƣ��絳�����塣��
����ʵ۾�һ��Ŭ����NO��8��
���
ÿ�����t���ţ�ֻҪ���DZ��ɻ���ȥ�ģ�һ�㶼����������У�������ʶ�������Ӧ���¼�������Ҳ֪�����������t�����������������t��δ������ҵ�У��Ѿ�����Ԥ����һ����Ҫλ�á�
������ͬ���t�ȥ�ĵط�������Ұ�Ķ����˳��ҡ�����˵���t��ȥ���ţ�����˵����ȥ��������Ϊ��Ҫʵ�����Ǻ�ΰ�ļƻ����˳�����������ؼ���һ�����ѡ�
�˳�����ΰ�䣬��������֮�������˻£��Թ�����ǧʯ���ý���Ļ���˵���������������˶������˲����߹١����游��¡���پ����ݴ�ʷ���游��ѫ���پӽ��n��ʷ�����˺꣬�پ�ԥ�¶�ξ����Ȼ������Ժյļ�ͥ�������˳�ȴû�����ȱ�����̤����;�������о��ڼҡ��̳е˼��˻´�ͳ�����Σ����г��ֵ��óе����˳����ĵ�������Ұ��������Ұ�ĵ����ϣ���Ҳȷ����ʵ��������
�˳������tһ����Ҳ�������ͣ�����������֮�ڡ����t���ݷõ˳�����ʵҲ��˳�����ݷõ˳���������Щ�ſͣ���һ�߰ݷã�һ�������а������㣬һ���췴��������Щ�ſͶ�����Щʲô�ó����ţ�������ʹ��ɥ�ʲ���������ʹ������Ĺ�����ſ�ʹ���űջ������ο�ʹ�״�������ɿ�ʹ�����������ҿ�ʹ��ţ�������ֽ���ʹȡ״���У�����ʹ������ϭ������ʹĥ�������������ʹ����ʳ�㣻�ڽ���ʹ������ǽ����ο�ʹ����ɱ���������t����ô�����ţ��·�����Ȼ��ۣ�������Ȼ�뱸���������ĺ���֮�£��ƺƵ�����ɱ��������
�˳��γ���֪���t�ڴ����ſ͵����⣬������һ���ܿ��ŵ��ˣ��Դ˲������⡣���翴�����t����ƽӹ֮������һ����ɳ�������ҵĴ���������ע��Ϊһ��ΰ������˶��������˳�û�����t�����İ��������ţ������������ɵ�ѡ��վ�����tһ�ߡ����ܲ���ΰ������ҲҪ��ΰ��ͬ�С�
�˳����ſ���Ҳͬ�������t������������������ĺ��ӣ����ҵĺ��ᣬ���л�������òΰ����һ���ͷ�ͬ���У��պ�ؽ��˷����ˣ�����Ǭ�������ŵ˳�������ԡ��������t��ȴ�ܳ������࣬���Ϸ����Ƿ��ģ�������ɡ�
����7��
Ȼ����ǰ·����������̫ƽ����ç�ڳ����Ļ������������ȣ�һʱ�������κα����ļ������t�͵˳�����������ֻ�����ո�̸���ۣ��������֡�
������ʱ�����t�ν�ն�����������裬�Ը�¥����£���ν�˳���������ӵ����Ұһ������һ�죬��ҲҪӵ�������¡���Ҫ����ç֪������������ʧȥ�ģ���һ�������ֶ������
����ȥ�����t�͵˳�ȴ��ֻ����Գ�̾����Ҫ�췴��̸�����ס�ʱ��Զδ���죬����ֻ�ܺ�ʱ��ɺġ�
���t����֮�����������������˵�ע�⡣��������ڳ��ֵ���Ӱ֮�£����ð�ȫ�����ð��ġ��������������������غ����Լ������ǿ������ң����ǿ������ҡ��˳�����Щ�ſͣ�Ҳ��ȷ�������Ӷ�����������ֻ�ǽ����������t��һ��С������ѡ�
��������һ�˵��۹����ڲ�ͬ���DZ��ǵ˳����˳������������㣬���������������t֮�¡���ʱ���˳�����ζ��ؾþ�ע�������㣬�·�Ҫ�������������㲻Ϊ�������ں����ƣ�����������������
�˳�û�ޣ����Ƕ�����˵���������ʵ��������壬���������Щʲô����
���㵭��˵���������ɡ�
�˳���Ц��������úá�������ɫ�������壬��Ͳ�����ͬ��
�⻰����ʱ���������常������ô˵�������������˶���ô˵�����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