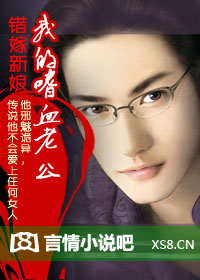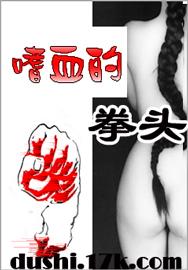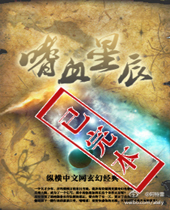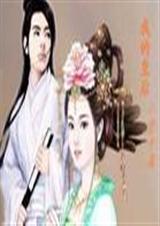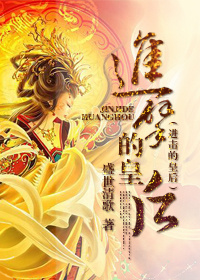嗜血的皇冠--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第7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传说昔日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一开始连遭败绩,其幕僚在起草上呈皇帝的奏折时,其中有一句“臣屡战屡败”,曾国藩颇为不满,大笔一挥,改为“臣屡败屡战”。结果因为这一改;清廷不仅对曾国藩未予责备,反而慰勉有加。
后人论及此事,皆惊叹于曾国藩高明的文字游戏——屡战屡败,废物也;屡败屡战,则非但不废,反而显得英勇无比。如此解释,固无不可,然终因不谙兵法之故,见识未免流于浅陋。
屡败屡战,谈何容易!每遭一败,都是对兵力的巨大消耗,都是对士气的沉重打击,倘是普通将领,要想维持部队免于哗散都成问题,更何况迅速重整旗鼓,继续作战?
追根溯源,便要从曾国藩的起家说起。曾国藩组建湘军伊始,便确立了两大方针:
一是募兵的地域,严格锁定在湖南,尤其是其老家湘乡。二是所有大小军官,皆由他个人任免指派。
正是这两大方针,使得维持军队稳定的两个情感纽带得以极大的巩固和强化:
首先是士兵对其领袖的情感。曾国藩大权独揽,全军只听命于他一人,在湘军内部,他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威,集君主与父亲的双重身份于一身,士兵们自然能够惟命是从,竭死尽忠。
其次是士兵对同伴的情感。士兵之间,同乡同里,语言相通,习性相近,很容易便彼此熟悉,彼此信任,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作战之时,不会像陌生人或者夫妻那样,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真正做到不抛弃、不放弃。
也只有情感结构如此稳定的湘军,才能够屡败屡战,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也正是这样的湘军,恰恰可以套用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的那句名言来形容:他们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也正是这样的湘军,才可以让曾国藩笃定持重,宁迟勿速;不用奇谋,逐步推进,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收获最终之胜利。
今人每以湘军为论,自诩湘人骁勇,为它省所不及,从而陷入地域之争,诚陋也。历朝历代,神州各地,几乎都出过强军劲旅,而这又从何说起?何处人不善战哉!特在于善用之也。苟用之得当,点豆拈草,皆可成兵;飞花摘叶,皆可伤人。岂地域使然!
NO。20:吊昆阳
再说突然变得极端恶劣的天气,同样也让汉军措手不及,雷声大震,风骤雨急,能见度急剧降低,汉军不得不停止攻击,守住阵形,先求自保,同时祈祷着坏天气快点过去,以便早点再度上阵杀敌。
然而,官兵居然在这时全军崩溃,这倒是让刘秀等人始料未及。一道道闪电,频繁划破长空,勾勒惊慌而逃的人影,照亮饱经践踏的尸体。刚刚还热火朝天的战场,转眼间便沦为凄凉冰冷的地狱。
大雨瓢泼,刘秀等人站在雨中,一动不动,张大嘴巴,为眼前的奇观所惊吓。雨水斜飞,灌满嘴巴,噗,吐出来,然后继续张大嘴巴。他们就是没法将嘴巴闭上。这也太神奇了,难道战争就这样轻易结束了吗?
刘秀等人百无聊赖地抚摸着肱二头肌,惆怅着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场战争,他们猜到了开始,却绝对没有猜到这样的结局。他们胜利了,而且是一场做梦也不敢奢望的大胜,胜得如此干脆,如此彻底。难道是天意不成?就算是天意,那老天爷也未免太慷慨了些。刘秀等人不可置信的互相打量,很久才敢确认胜利的事实,于是笑声和雷声混响,泪水随雨水飞扬。
当雷声渐止,战场上的嚎啕与呼叫也渐渐稀少,刘秀等人这才听到一阵沉着而坚定的战鼓声,隔着雨幕望去,便看见一个胡人,浑身湿透,擂鼓不休。那是官兵的司鼓手,无视周遭无数尸体,无视战场一片狼藉,在天地之间,在雷雨之下,忘我独奏。他根本就浑然不觉,他已是昆阳城下官兵留下的最后一人。汉军围上前去,静静听着胡人击鼓,没有人想到要去伤害他,他并非战士,手中也无寸铁,然而他和他的战鼓,却响彻到了最后。
战鼓声如此激昂,却又如此绝望,刘秀忍不住大叫道,战争已经结束!胡人见是敌军,鼓声丝毫不乱,大叫道,只要还有一个官兵在战斗,我都要陪他到底。刘秀大叫道,一个官兵也没有了。胡人停下鼓槌,举目四望,除了尸体,还是尸体。胡人呆立半晌,全身不住颤抖,半是寒冷,半是悲伤,良久,向刘秀道,“男儿死异乡,请奏安魂之殇。”说完,也不等刘秀同意,径自击鼓。
鼓声再次在昆阳战场回荡,为那些早逝的魂灵,为那些横死的儿郎。低沉压抑的鼓声,穿越凄风冷雨,穿越闪电惊雷,在每一个生者和死者的耳畔奏响。鼓声之中,不再有敌我双方,不再有胜兵败将。所有人皆为一体,每一个死者都是生者的哀伤。何必问鼓声为谁而响,它正在为每一个人而响!
胡人从战役开始一直擂鼓到现在,早已筋疲力尽,随着最后一个鼓点的落下,胡人潮湿的身躯缓缓倒地。昆阳城下最后一面战鼓,就此安静下来。
再说王邑逃至安全地带,回马眺望身后的昆阳战场,望不几眼,忽然悲从中来,披发狂笑,如歌如泣,似疯似魔:
毁了,全他妈的毁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百万之军,说没了就没了。遥想当日,我曾有怎样的降临?那时我是黑夜,我是战魔,我将抚摸河山,征服所有。而如今,数十万将士,在眼前这片战场同时毙命,更可笑的是,他们不是死在汉军手上,他们是自己将自己摧枯拉朽地残杀了个干净。远方的亲人,关上那敞开的门吧,不必再等,儿郎们不会再回来了,他们将永远留在昆阳,留在这个被诅咒的地方,他们再也不能在肩上托一朵小云,他们再也不能在喉间蓄一缕歌声。
王莽已经什么都依了他,王莽这回够哥们,他还有什么借口可找?没有,一万个没有。三个月时间聚集起来的百万大军,毁灭却只用了两个时辰。失败,窝囊的失败,而且是败在刘秀这么一个无名小辈手上,还提什么不朽名将?还提什么万世流芳?
第155节
火光在天地喷涌,将人命归零,一如从未诞生。那些惨死的尸首,只是假造的伪证。荷叶上的蜻蜓,来不及闭上它那太多的眼睛,只能牙一咬,腿一蹬,决意自沉。当少女捂起明媚的小脸,也许是因为腮腺发炎。当露珠发现自己的晶莹,意味着离破碎已经不远。
如何渡过这一生,实在是一门最为艰深的学问。
天气略有好转,汉军即刻趁胜分头追击。对一场战争而言,更大的战果,往往是通过追击才能获得。刘秀领一军,西追数十里,截获严尤、陈茂残部百余人。严尤自知反抗毫无意义,命部下放下武器,接受汉军发落。汉军正待一拥而上,大动屠刀,刘秀伸手止住,打马邀严尤道,“新朝气数已尽,严公何不归降?”
严尤望着刘秀,想当年长安之时,他贵为大司马,而刘秀只是一名年轻的穷太学生,寒风中苦苦守候在他的府前,只为能见上他一面。如今故人重逢,形势颠倒,贵贱易位,他反成了刘秀的俘虏,抚今追昔,情何以堪,只能强笑道,“击溃百万大军,只在反掌之间,如此伟业,千古未有,而小子竟办之。吾老矣,无降,愿死。”
刘秀一心想要招揽严尤,不仅仅出于私人情谊,对汉军来说,以严尤的才能及威望,一旦归降,无疑将是一巨大鼓舞,对新朝则是一沉重打击。于是再劝道,“民心思汉,刘氏当复兴,严公与我叔父刘良乃是至交,倘能投汉,日后必为社稷之臣。望严公三思。”
严尤苦笑,他已经一大把年纪,不可能再忍受羞辱,和他眼中的一群流氓无赖为伍,与其折节下之,毋宁一死,于是答道,“多谢文叔美意,吾意已决。宁死不降。”
刘秀嗟叹不已,严尤于他有知遇之恩,真要杀严尤的话,他如何下得了手?一挥手,命部下闪开一条道,道,“当日恩情,小子未敢忘也。严公请便。”
严尤也不道谢,率众而去。去不多时,单骑而返,语刘秀道,“再见不知何时,临去,有一言不得不表。王莽虽不能用人,犹胜过汉军之不能容人。我观汉军,其中小人多有,共患难易,共富贵难,今虽大胜,不久必起内讧。宜未雨绸缪,早作防备为幸。”
刘秀悚然道,“多谢严公教诲,小子自当谨记!”
严尤扬鞭而去,刘秀也收兵回返昆阳。晚风劲吹,夜色渐深,新月如钩,高挂天际。一路之上,伏尸百余里,踩死的,挤死的,吓死的,淹死的,战死的,其状各异,其惨同一。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此情此景,刘秀心中忽起胜利者的悲凉。
回抵昆阳,一副繁忙景象,官兵溃奔之时,抛下所有军实辎重,汉军此刻正在月光下哄抢,刘秀部下惟恐后人,一哄而散,也加入到哄抢的行列。
刘秀想去寻邓奉,却发现邓奉早已不告而别,正如他不告而来。刘秀感到一阵无比的寂寞,突然来临的胜利,显得是那么不可思议,强大的百万官兵,何以一时间便溃散无余?难道真是冥冥中的天意在眷顾自己?
思索然后顿悟,刘秀浑身滚烫,他想他终于明白了蔡少公所说的那句大谶。
大谶曰:刘秀当为天子。为什么不说刘秀必为天子、刘秀且为天子、刘秀将为天子?一字之差,其中大有深意。当者,选择之意甚明,上天选择了他,要将天下托付给他。以前,刘秀和他的长兄刘縯一样,将天子视为权力、财富和地位,视为家族失去的荣誉。而如今,刘秀明白了,天子其实意味着责任,赐苍生以安宁,为万世开太平,让眼前的惨剧不再发生,让天下远离灾荒和纷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然而,刘秀不敢再多想下去了,在这句谶语当中,他已经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启齿的罪恶。而这种强烈的罪恶感,甚至让他有了立刻自杀的冲动。幸好姐夫邓晨及时赶到,将他从自我折磨的深渊中拯救出来。邓晨车马满载,显然是在哄抢中收获颇丰,见刘秀正在发呆,笑问道,“你不拿点什么?”
刘秀摆摆手,道,“此皆将士搏命而来,自当由他们分去。”
邓晨道,“你不拿,部下岂敢先拿?”
刘秀无奈,于众多金银珠宝中,独挑出一块黝黑的石头。邓晨笑道,“好眼光,此乃天外陨石,用以铸剑,必远胜干将莫邪。”刘秀大喜,即命铁匠铸剑,献与长兄刘縯。
以上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最为以少胜多。千余年后,东坡兄途径昆阳,触景生情,感动于中,为前人及后世留下一首《昆阳城赋》,赋曰:
淡平野之霭霭,忽孤城之如块。风吹沙以苍莽,怅楼橹之安在。横门豁以四达,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伛偻而畦菜。嗟夫,昆阳之战,屠百万于斯须,旷千古而一快。想寻、邑之来阵,兀若驱云而拥海。猛士扶轮以蒙茸,虎豹杂沓而横溃。罄天下于一战,谓此举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获,固已变色而惊悔。忽千骑之独出,犯初锋于未艾。始凭轼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纷纷籍籍死于沟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窃,盖已旋踵而将败。岂豪杰之能得,尽市井之无赖。贡符献瑞一朝而成群兮,纷就死之何怪。独悲伤于严生,怀长才而自浼。岂不知其必丧,独徘徊其安待。过故城而一吊,增志士之永慨。
日期:2010…04…0603:58:38
【第十三章,手足之断】NO。1…2(基本原文)
NO。1:一夜成名
且说王邑昆阳大败,收拾残众数千人,一路狼狈逃归洛阳,因为这场惨败,加上又死了王兴,吓得连长安也不敢回。王邑此番征战,战果全无,后果倒是一大堆。官兵溃败之后,士卒各还其郡,再也不能聚集,帝国军力丧失殆尽,从此只能被动防御,再也无力主动进攻。昆阳惨败的消息传来,关中震恐,盗贼并起。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起而造反,杀其牧守,占其州郡,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昆阳大捷,既成全了汉军,也让两个年轻人一夜成名、威震天下。人们记住了百万军中力取巨无霸人头的邓奉,也记住了指挥若定、谈笑间官兵灰飞烟灭的刘秀。更难得的是,这两人还都是年少英俊,唉,真是要命。
世人汲汲经营者,不外乎名利二字。利,钱财也,真金白银,实在。名,名气也,气者,飘渺而虚。
世人爱财如子,唤金银为金子、银子(近世行纸钞,则曰票子),铜铁锡之类,则无此待遇。钱财固佳,然土鳖财主,终究只能为害一方。名气虽虚,却能憾近动远。所谓名望,远得以见;所谓名声,远得以闻。故名利虽并称,而名在利前。
先论一般之名望。当一个人占据某个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和头衔,仅仅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不管他本身多么没有价值。故韩非子曰:“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谷,材非长也,位高也。”
此等名望,已经足以迷惑常人的眼睛,使其不自觉地对对方予以美化。司汤达作《爱情论》,其中描写一市井女子,在伊眼中,哪怕男人再难看,但只要他是大公或亲王,立即便觉得他风貌可人。意大利使臣见英王查理二世,其观后感也曰:“英王若只是寻常百姓,则可谓仪容丑陋,然既贵为国君,遂俨然可称美丈夫也。”
总之,一旦沐猴而冠,那就不再是普通之猴,乃冠猴也。一旦鸠占鹊巢,那也不再是普通之鸠,乃巢鸠也。
然而,此类名望寄生于地位或财富,有如月亮,终须仰仗太阳之光。一旦财势两空,则名望如气球一戳而破,光环瞬间褪却,泯然众人矣。
第156节
而最高之名望,非关财富地位,不拜外物所赐。有此名望者,乃是活着之传奇,在其生前便可预先宣布不朽。在常人眼中,他已经不再是凡人,而是超凡入圣,几乎接近神灵。名望赋予他神奇的力量,众人在面对他时,将彻底丧失批判能力,满心只有惊奇和敬畏,众人对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