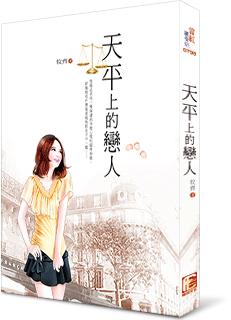地板上的母亲-第5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候竟然还需要排队。排了几次之后就不耐烦了,于是就在每天中午最热的时候,从家里溜出去,把屁股放在滚烫的水磨石梯道里上下打磨,皮倒是没烫掉,裤子难免被摩擦生的热煎熬得痛苦不堪,不久就不堪重负,于是就到了捂着腚回家的时候了。动物园里弥漫着各种禽兽的味道,日熏夜陶,也就有了禽兽的资质。好玩归好玩,可是每次进去都要交钱可是件极其郁闷的事情,好在五六年可不是活在狗身上了,歪点子层出不穷。第一种方法,跟在一群素不相识的大人后面,安静沉默,胸有成竹地迤逦而入。当被查票的阿姨发现人数票数不对时,早就高高兴兴地开始磨炼腚了。随着个子日渐增高,此法渐渐不灵,只好另辟蹊径,天天溜公园的墙根,试图发现狗洞之类的东西,最后发现,狗洞倒是有,可是人果然钻不过去。于是考虑翻墙。翻墙有好处若干,第一,当然是能达到不给钱就进公园的直接目的;第二,强身健体,利于身体发育;第三,获得很高的成就感;但也有不好的地方,由于胆子小,每次翻墙都是战战兢兢死活不敢在墙上站起身来走,于是就骑在上面‘挪动’,后果可想而知,裤子被磨破的地方从腚后转移到了裆下……
“啊,日月如梭,转眼就丧失了对滑梯长达五年的浓厚兴趣,转而对
电子游戏情有独钟。那时哪有现在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电脑游戏,最快乐的时候也就是做完了作业(还算有点责任心)偷偷溜出去找个乌烟瘴气的游戏室呆上半天,然后晕头转向地游荡回家……
“小学三年级前回家的路不可谓不漫长,对一个六岁的小屁孩儿而言,说翻山越岭也不为过。出了学校往东走,跟一群同学结伴而行约四百米,大家就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剩下我和一个二院的小胖继续前行,先往南行至曙光街二院家属院,一般在这里我要和小胖例行公事地打一架,以防止我在后面漫长的旅途中备感无聊——我可以在被打得落荒而逃之后一面拍身上的灰一面在心里用最恶毒的脏话骂遍小胖全家。即使如此,我走到青少年宫的时候就消了气。剩下的路倒也不长,上河堤,过湛河桥,到家啦,旅途愉快……可怜的小胖第二天仍然要忍受我的挑衅和骚扰,看在他帮我消愁解闷的分上,他捶我那几拳我至今也没还……
“一年级时,家里给的早餐钱老老实实花了买胡辣汤油条,吃完抹嘴上学。
“二年级时,家里给的早餐钱全给了学校门口一个可怜的老奶奶,买来
泡泡糖跟同学比赛看谁吹得大,最终以因为在课堂上被自己吹爆的泡泡糊住了整个头脸而差点窒息而告终;不过显然,我是比赛冠军。
“三四五年级以后,家里给的早餐钱,卖破烂的钱,犄角旮旯里放了猴年马月的毛毛票,还有在外面捡废铁卖的钱,偷废报纸卖的钱,地上捡的钱——关于从地上捡钱的生活经验,使我发现‘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句话真是很有道理——这些钱通通被电子游戏机吃了去,换来的是近视眼和熟练的游戏技巧……直到五年级暑假,差不多把能找到的游戏玩了N遍儿,闭上眼也能很快过关,这时,心爱的小学时光即将过去,心里空荡荡的没了着落,一夜之间,我对这小孩子的弱智把戏就腻味得不行了……
“考初中幸得年级第六,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鼓励。初一期终考试,又蒙了个全班第四,年级二十七名,八个班也就是四百人吧,我被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俘获,注意力大转移,最终踏上了老妈和老师耳提面命舌头起茧的拼成绩、考名校的‘人间正道’……
“金色的童年结束了。”
哗啦——汤汁子洒一地!一群没肝没肺的家伙哄笑着跑走了。
妈妈小时候也不是省油灯
妈妈小时候胖嘟嘟的,带个红绫子绣花肚兜儿,满世界疯跑。连年大水把咱们老家涨成了“台子庄”,一个土疙瘩一丛树,一丛树里一户人家,小胖妮儿从这家儿跑到那家儿,露水珠子一样滑个U就是一个来回。
上小学的时候,也干过这么几桩好事儿:
三月里,春风刮得土地松软,上学路上不走大路走麦田,扑扑拉拉趟着麦垄,一路踢得土花儿乱飞还不过瘾,专拣长得又深又密实的麦苗,逮住两垄一替一脚踩倒,叠压出一溜麦辫子。幸得脚小身子轻,五月割麦的时候,这些“辫子”照样结出鱼娃子一样的麦穗子,只是相互交叉的麦秆半躺在地上,惹得割麦人不住声地骂:“谁家的妮片子,吃饱撑哩害煎人!”
高粱地里有“哑巴秆儿”,就是那些长半截儿被风刮断或是被割草娃儿削了头的高粱,有劲儿没处使,憋成小孩儿胳膊粗,撅下来劈劈当甘蔗吃。高粱地里还有“乌莓”——高粱打包儿被菌类侵占不结籽儿,结成粉白皮儿包着的“白胖娃儿”,咬到嘴里粉面粉面。大麦也会结“乌莓”,一结就是一墩,一抽一大把。大麦穗小,“乌莓”也小,还有麦芒,没有高粱生成的白胖娃儿好吃,又光滑又可嘴。
夏秋之交,天热。放了学不想回家,怕被大人支使得陀螺子一样脚手不得闲,就在高粱地边迎风头儿搭凉棚。搬着一人多深的高粱,用青麻批子捆扎个“屋顶”,扔上几把草,脱下小布衫耷在弯着腰的高粱秆上,两个人坐在下面,抓子儿、站方。风一阵一阵扑打着高粱叶子,卷起热烘烘的野气,哗啦啦,哗啦啦,高一声,低一声,流向不可知的远处去了。泥土松软,一蹭就破皮儿,刚才还晒着腿的那片太阳,不大会儿就跑到身子后面的几棵爬地龙上去了。这时就听见你老头爷又焦急又恼火的喊:“敏——敏——晌午错了还不回来吃饭!”
秋深毛豆饱了,逃学的日子来了。前后桌儿几个人一嘀咕,趁第三节自习偷跑出来,一溜烟直奔东大沟。沟东一大块黄豆,沟西一大块黄豆,胖乎乎瓷丁丁的豆荚子从根结到顶。书包往地上一撂,看看四下没人,揽干草的揽干草,薅豆子的薅豆子,狼烟一起,豆荚落地,炸出来的豆籽儿焦黄油亮。
不好了,东南风刮过来了,把一股直上青天的“狼烟”吹倒了,那股烟简直就像被点名儿叫着一样,一刮刮到学校里,校长闻见了,逃学匠的诡计暴露了!几个人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狠狠教训一顿。班主任李老师跑来讲情:“算了吧,念他们是初犯,就别在放学路上点名了。”把几个丢脸儿的家伙领出来,李老师也不看别人,只点着我的脑门儿说:“你呀你呀,平时的聪明劲儿跑哪儿去了?带头儿干坏事儿,也不选个离学校远点儿的地方……”为了班主任的大恩大德,当然是下不为例了。
妈妈小时候疯起来也是狼一群狗一伙的,那才真叫“好三天臭半年。”有一年夏天,几个人蛊住一个叫德敏的女生,先开除她“英雄小八路”的队籍,她的名号由“铁牛”改成了“黑鼻儿开汽车”。上学路上不跟她一起走,星期天割草也不叫她。打百分、抓子儿就更没她的分儿了。有一天下小雨儿,天傍黑儿的时候,几个人一商量,找半拉破瓦盆儿,扣在她家灶火的烟筒上。烧火做饭,烟气冒不出来,呛得掌锅的娘和烧锅的德敏不住声地咳嗽,不大会儿,她娘掂着勺子跑到院里,揉着眼睛东瞧瞧西瞧瞧,说:没风啊,咋会倒烟哩?第二天早上,她爹才发现那块瓦片,吆喝了一个庄子:谁家的小孩儿有娘生没娘管,干这种不冒烟儿的事儿?再教我逮住腿给你打断!吓得我大气儿不敢出,被你老头爷从门后拧着耳朵拽出来,黑着脸又打又骂:“死妮片子,看你往后还敢给老子挣骂名……”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初中时看白戏。班里有个女生是老红军的后代。演样板戏,她替她妈把门儿。收几张票,装着上厕所,交给躲在黑影里的我们,交代说:只能站着看,不能坐座位。有一次下大雪,散场后几个同学凑了六毛钱,下馆子买胡辣汤。一间屋门朝东,里面放着三张四条腿乱晃的桌子,桌子上蒙着白塑料布,就因为没凳子让我们歇歇看戏站麻的腿,几个人把粉条、肉星儿、白菜帮子捞了,剩下大半碗清汤,看谁的手头儿麻利,啪一声把碗扣在桌子上。然后躲在门外,眼看着服务员用冻僵的手指一点一点把倒扣的碗抠起来。一直抠到桌边儿上,哗啦——汤汁子洒一地。一群没肝没肺的家伙哄笑着跑走了。
那叫人话吗?既没有人性的温暖,也没有生命的气息。
可怕的冗余
好多年没参加过会议,那天下午,坐在冷气开放、装修豪华的会议室里,受了一晌洋罪,我开始可怜那些公务员了。他们吃这碗饭不是一般的不容易,是太不容易了!说真的,我宁愿在大太阳底下装车拉沙,忍受铁锨磨着沙子的声音,也不想听那几个官员面无表情地念讲话稿。原本不满两页纸的文件,被他们大一、二、三,小1、2、3地说来说去,如果没有老僧入定的工夫,这会要是开上三天,非得发疯不可。那叫人话吗?既没有人性的温暖,也没有生命的气息,完全是一堆被无数人搓来搓去搓得脏兮兮的麻将牌!好端端的一档子事,就这样被糟蹋掉了。
熬到散会,如获大赦,辞掉晚宴,我迫不及待地逃到广场上,逃到那块花眼地砖涌起成窝子绿草的林间小路上,两边松柏和海冬青被太阳晒出浓郁的香味儿,正好供我大口大口换气。来来回回不知多少趟,一直走到身上汗津津,发懵的大脑才活泛出人味儿,浑身的皮肤也被新修剪的草味儿丝丝泡醒,看来,“洗耳河”绝不是古人矫情的杜撰……
想起一位朋友,在大机关里工作多年,因为不入流儿,一次又一次被边缘化。终至不能忍,想到调离。好在朋友圈儿里有可以利用的人资源,于是开始张罗。上方很快有了答复,两个选项,在我看来都是再好不过,工资翻番,单位的牌子也很硬。可他却不看好,非要去工资低且毫无发展空间的高一级对口单位。你说这人,为什么连一加一等于二都算不明白呢?真可惜了他的博士学位,可惜了上天赋予他的聪明才智!
真是一家不知道一家,和尚不知道家。先前偶尔见面,我只是可怜他手机、电话不停地响,连十分钟属于自己的囫囵时间都没有!开过这次会,我恍然大悟:可恶的机关生活,没完没了的文山会海,就这样置换了一个人灵性的大脑,把他变成身上心上糊满水泥的“砖块”,变成了一个迂腐而不自知的冗余。
只要一闻见纯正的野草味儿,我就会不可遏止地掉回乡间!
草味儿,杏味儿
每次去广场散步,阴晴晨昏,草的味道不同。
清晨,微风迎面扑在脸上,如同一帘儿薄薄的瀑流,把露珠闪动的青草气儿吸进心里,清凉凉的。雨丝飘动的日子,无根之水聚集在草窝子里,缀在茎梗上的小气泡儿,成了潜在水底的露珠儿。咕唧咕唧过去,草叶带水吮着脚掌,清凌凌的色气拱鼻子拂眼,水淡草香,带股甜味儿。酷热的中午,草被毒太阳晒软在地,根里叶里的水汽几乎全释放出来了,那种不管不顾不要命的味道,更是烫鼻子焌脸,热蒸气一样烘人。换了雨后黄昏,暑气消退,走进剪草机刚刚修整过的草地,浓郁的草香带点儿苦,不知不觉,我就跟着这味道走进了多年前的牛屋院儿:几百斤刚过完秤的青草,堆在一口木把儿铁铡边,一个人“喂”草,一个人捺铡,嚓——嚓——嚓——铡刀切断草梗儿,一股一股溅起来的就是这味儿……
想起远去的童年,想起悄没声来了又去的无数个乡野草民。
走在都市几千万银子建造的广场上,走在几十个工人一遍又一遍除草浇水的绿草坪间,随着衣衫光鲜的城里人,在喷泉、太极、健身操和儿童乐园的各色背景音乐中,花眼方砖分割的几何草图,被我匀速运动的步态走成了三维立体画儿。就这样,一早一晚,沐风浴草,我在广场上走了一圈儿又一圈儿。有时候还真相信,人有醉酒的,有醉拳的,有醉舟的,也有醉步的……
可我只要一闻见纯正的野草味儿,就会不可遏止地掉回乡间!掉回岁月之风吹它不去的泥与草的生命年华,掉进那个扛锹荷锄、曳耧扯耙的乡下人的灵魂里。
不久前,我在尧山镇五小遇到一个女孩儿,身姿清纯,面容姣好,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赵敬慧,家就在石人山下的西竹园村。两岁时,命运的铡刀不由分说切断了她父亲的生命,母亲改嫁,剩下她和奶奶相依为命。
尧山五小有130多个学生,50名寄宿生,赵敬慧是其中之一。学生们的书费、杂费全免,15%的特困生每学期还有100元补助。学校有食堂,孩子们的伙食费一个月最多60元,少的只有30元。还有从家带东西来的,很少在食堂里买饭。赵敬慧一个月的费用一般不超过40元,除了补助,就靠奶奶在山门外卖熟鸡蛋。功课重,12岁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她把握着每星期10元:早上玉米糁儿,5角一碗。中午米饭,清炒萝卜白菜,连米带菜1元一份。晚上面条儿,有汤,有馍,有咸菜,吃馍不喝汤,喝汤不吃馍,也是5角一顿,小姑娘的账头儿精细得让人心酸!
西竹园是个美丽的山村,一路仰着脸爬坡上去,累得大喘气。树多地少,山色绝佳,还不曾卖门票。坐在赵敬慧家的院子里,石人山风光尽收眼底。顺着磨光的石头,随便跟着条影影绰绰的小路,就能走进清极净极的人家,走进一处溪泉翻白浪的森森幽谷;走近一座白石缀着绿树的峭壁。通往山外的路,陡虽陡,也能过摩托,能开拖拉机,可不知为什么,进村那一段儿,却保持了原有的风貌:大石头小石头,懒人膝盖儿一样,拱起在路中间,这一家到那一家,相连的石阶大都是自然本真的模样,踩来踩去多少代了,就没有人想起来归整过。
看着敬慧的奶奶手脚不闲搬椅子、拿毛巾、烧开水,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中午,天热得蝉都叫不出声来了;母亲锅上一把锅下一把忙得汗透衣衫:炒鸡蛋,煎南瓜饦儿,烙油馍,熬绿豆汤……尽其所有,招待上边来的干部,她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招待好这些人,她的女儿就能被推荐上大学。直到那些人吃个盘底朝天,抹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