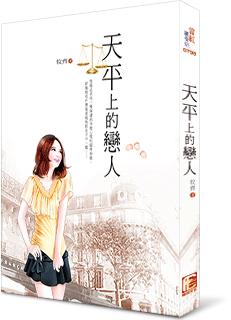地板上的母亲-第6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希昧礁鋈嘶ハ嗦裨梗骸八心阆盅郏易愿龆俗潘懔耍憧纯矗仗淼囊坏朴团髁恕钡担骸澳慊孤裨刮遥煤玫赝白撸心憷洳环劳笸恕甭韪峡彀锬棠贪研旅薨劳严吕矗跫概跚嗷襮i上。
煤油灯比香油灯简陋得多。随便一个小玻璃瓶儿,剪块又软又薄的白铁片子做个芯子,穿上根四股线五股线的灯捻儿,外面再套个能盖住瓶口儿的白铁片子,或是一枚铜钱,往瓶子里一插,就是一盏灯了。有人干脆把墨水瓶盖儿上钻个洞,罩片儿洋铁页儿,装个芯子,盛上煤油,一点照样亮。“白天游四方,夜里点灯熬油补裤裆!”这是讽刺懒婆娘的一句俗语。从这句俗语里,就知道煤油对于贫苦的乡下人有多珍贵。虽然几分钱就能去代销点儿添一灯油回来,也不舍得把灯头儿挑得太亮,影影绰绰能看见人就行了。如果亮得冒黑烟,当家人就会骂你不会过日子。只有织布时挂在织布机旁边的那盏灯,夜里纳底子上鞋时挂在床头儿那盏灯,才燃得亮些,就是再亮,也没有一根蜡烛亮。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带罩的煤油灯只有公办老师的办公室里才有,孩子们早自习晚自习,用的是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玻璃瓶儿做的小煤油灯。木排窄,白天上课的时候,小油灯就被放进各人掏出的墙洞里,密密麻麻,佛龛似的。到晚上再拿出来点上,那些冒烟或不冒烟的小小的灯火,如同毽子上不住点头儿的鸡毛,抚弄着一排排稚嫩光洁的额头,翻动的书页上面,是熏得黑糊糊的两个鼻孔,这曾经是乡间最具历史特色的一幕。
铁匠铺
一进入麦天,那个外号驴的老铁匠就靠在自家的院门上,眯着眼往半里外的公路上望,一起儿一起儿的收割机,先是从北往南,后来又从南往北,赶大集一样追着黄熟的麦子跑。这些高大威猛一身火红的家伙,让他又恨又爱又说不出个啥来。
想当年,方圆所近,谁家能离了他的铁匠铺子?废品站收来的废钢铁,从他手里过过,就变成了有用的农具。一年四季,除了近不得火的伏天,他的日子差不多全都丁丁当当敲在红得冒花儿的钢铁里了。
铁匠铺没有固定的房子,刚一立秋,驴师傅就去找个宽敞的炕烟棚,带着他的两个徒弟脱坯垒炉子,挨着炉子栽个斗粗的大木桩,半截儿埋地下,露出二尺高,一尺来高百十斤重的生铁砧子往上面一搁,抢起锤来正使上劲儿。方棱四正的砧子一尺多厚,微微凸起个鼓形的脸儿,一边两只大耳朵,一边两只小耳朵,前面抻出一段尾巴,活脱就是个大老鳖。一只小耳朵上有个洞,打家什的时候就在上面冲眼儿。除了支起来的砧子,还有一个略小点儿的放地上,高的做热活儿,低的做冷活儿。少不了的还有个大风箱,一米多高,两米来长,半米多宽。煤是能开铁的好煤,风箱拉起来呼呼响,蓝幽幽的火苗蹿起半尺多高。一切准备就绪,分门别类摆开他摸熟的打铁工具:手锤三把、大锤三把。钳子四把:手钳、平口钳,专门用来夹耙子齿儿的鸭嘴钳、叨大铁块的大嘴钳。还有一把大铁剪,三四把三棱的、平板的铁锉子,另外还有个打钢活儿开槽使的圆刃儿抢子……
铁匠的衣裳补丁越厚越好,弄不好铁渣子掉身上,哧啦冒股烟儿,就是一块难看的疤。打铁的时候,驴师傅总是提醒他的两个徒弟,腰里系的那块旧帆布片子一定得厚实耐烤,脚脖子上绑两块帆布盖严脚面,鞋得趿拉着穿,万一有铁花儿子落在脚上,一甩就掉了。俩徒弟年轻轻的,还没娶媳妇儿呢。
秋天来了,得先打老虎耙子,刨红薯等着使。这活儿巧儿不大,徒弟们都会干。接下来打铡,才是大手笔,一年几万斤麦秸,全靠这它铡碎了喂牲口。去废品公司买材料儿,驴师傅得亲自去挑。“短铁匠,长木匠,石匠八尺算一丈。”石头难弄,得往多处算,铁料儿短了,敲两锤子就长出来了。一口铡一米多长,十多公斤重,得用大块料儿。一大块好铁,一小块好钢,搁火上烧软了,师傅拿把二尺多长的手钳,叨紧那铁块儿,慢慢挪到靠近砧子的地方,另一只手小锤儿顶着,手钳夹起来猛一使劲儿,铁块就翻到了砧子上。打铁得趁热,两个徒弟早已掂着八磅重的大锤等在一旁,师傅的叫锤儿在砧子耳朵上当当两响,对面的大锤依次开叫儿,丁丁咣咣,丁丁咣咣,铁花儿溅出去三四米远。打通身,师傅就在砧子上移动铁块儿,重点打哪个部位,叫锤一点丁丁当,最后一声敲到哪儿,大锤就跟着往哪儿打。
打会儿冷了,再放炉子上烧,烧了打,打了烧,打成一边厚一边薄的毛坯,差不多得一天。然后凿眼儿、束裤儿,成形,挪到低处的铁砧子上,用顶子磨得光溜溜的手锤,一点儿一点儿敲得平展展滑溜溜,青光锃亮,抢抢锉锉,开了钢口儿,装上木座儿就可以用了。冬天打铁钉盖房子,打九齿钉耙平整土地,年关近了打菜刀,开春儿打锄、打菜耙子,打钐刀儿,活多的时候老少爷们挤挤攘攘,常常为你先我后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引来成群的小孩子看热闹。
最忙的是麦前打镰那一阵儿,别看家什小,一点儿也马虎不得。选一小块铁,一溜儿钢,放火里烧得冒火花儿,浮一层油样的汁水,叨出来放砧子,打得它们叠合成一块儿,这叫“熟火”。再加热,打成背厚刃薄的毛坯儿,一头儿打个薄片儿,折个揳木把儿的裤儿,有模有样儿,再放火上(火+通)均匀,拿钳子快速叨出来往冷水里一扔,这叫“淬火”,不淬火不锋利。一把镰卷不卷刃,崩不崩口儿,全在这会儿的火候儿看得准不准了,淬早了软,下地割不上两个来回就卷刃儿,淬晚了脆,拌着个小石子儿就崩口儿……
掐指头算算,有好几年没开炉了,钳子、锤子、锉子、抢子没情没趣地搁置在那儿,差不多锈成了一堆废铁,小孙子天天嚷嚷着拿废品站去卖了。小娃娃咋会知道驴师傅对它们的感情呢?大半辈子啊,这些家什在他手里玩熟了,一个个都成了他的胳膊腿儿了,胳膊腿儿能卸下来拿去卖钱吗?
眼见那收割机三五成群,抻长了舌头席卷而过,籽儿是籽,秸是秸。那真叫机械化。驴师傅吧嗒吧嗒吸几口烟,长长叹出一口气来,心里明镜似的,曾经属于他的铁花儿四溅的日子,随着“镰是一块铁,全仗胳膊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喷雾器
每年夏天下大雨,老北岗上就会有一股水顺着大路沟和水沟流下来,经过村子北面的三角坑和坝子,依次流进村里大大小小的五个坑塘,盛不下了,漫出来往南河流,途中还要经过一个水坑,就在村子南面不远的丁字路口,水不算深,正中间最深的地方也淹不住人。因为也是从老北岗发下来的那水结的“瓜”,只要不缺雨水,它就不会干。
因为那儿有个坑,打药方便,靠坑边儿的那块地每年都种棉花。棉田里生了蚜虫,队长就通知各家各户吃捞面条儿。趁中午头儿,男女老少端着大盆儿小盆儿的捞面汤到地里洗棉花。一块地三十多亩,三天洗一遍儿,洗它两三次,那些蚜虫不是掉盆儿里淹死,也被粘在棉花苗上晒死了,被它们吸得搐成疙瘩的棉花叶儿,慢慢又抻展开来。还有一种治蚜虫的方法,就是打棉油皂。把成大块儿的棉油皂放水里搦化,装到喷雾器里一棵一棵打,直到每一片叶子都往下滴水,那些蚜虫死的死亡的亡,干了风一刮就掉了。
早先的时候,很少打1059、1605和3911这样的剧毒农药,成群的小鱼儿和小蝌蚪儿像一层被风吹来的树叶子,成群漂浮在水中,长着六根长腿的“拐线婆儿”,似挨似不挨地在水面上飞快地拐来拐去。后来,为了治棉铃虫、造桥虫和红蜘蛛,开始打这几种农药。3911专治红蜘蛛。红蜘蛛比针尖儿大不了多少,繁殖得很快,开始发现不过十棵八棵,要是不管它,要不了三五天,成大片的棉花就被它们绣着了,变得红堂堂的,叶子和棉铃掉落一地。打3911,太阳越毒越有效。几个棉花技员捂着大口罩,一喷雾器装二十七八斤水,摁着把手打足气,不歇气儿一个人一晌能打六七桶。中午换班儿,不停事儿把整块地打完。如果点点片片还有,就得抽调劳力,人歇喷雾器不歇地打,直到彻底消灭为止。
圆铁桶形的喷雾器,上面有一个装着把手可以打开的椭圆形盖儿,水就从那儿灌进去。紧挨那个盖儿,是打气的把手儿,装满水时,打二十多下儿就可以了。随着水量的减少,打气的时间越来越长。要是想让喷雾气快点出水,就把气打得足足的,打开喷杆上的开关,高压下的水颤动着通过手掌心“哧哧哧”冒出来,喷成一大团半透明的水雾,在棉田里慢慢往前移动,眼前的小水珠儿带着七彩虹光,下雨一样打歪了棉花棵子。一杆喷云吐雾的“烟杆儿”拿在手里,比国王的权杖还威风八面。但这在棉花苗不够高的时候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打浪费农药。
那些剧毒农药都有一股熏人的怪味儿,棉花技术员到最后都丧失了嗅觉,什么味道也闻不见了。不过也有一个好处,夏天蚊子再多,也不咬农药熏出来的棉花技术员。
我最喜欢打的是“石硫合剂”,就是蓝得像天空一样的波尔多液。虫情不重,一晌打三四桶,用不着不停地呼哧呼哧打气,把结着一层老茧的手掌心儿磨得火烧火燎。不打剧毒农药,三角坑里的鱼儿和虫子们都活得好好的,歇歇儿的时候,长袖布衫抻开往头上一耷,坐在坑岸儿上,脱了鞋踢腾着水,一边说笑,一边看清水中的鱼儿张开圆圆的小嘴儿,一下一下啄破了水面儿。出过力的身子格外松爽,风一吹就透了。人的心情也是这样,干净得像蒲草下面那捧清水,被田野里特有的安静笼罩着,空旷而轻闲。
箔坠儿
春秋天下小雨儿,白菜叶子一样的云彩从天边飘过来,长脚稀腿的,遮不住黄黄的天光,正是织稿荐织箔的天气。两根板凳支在枝稠叶密的槐树底下,上面立个门板拿绳子摽稳,两个人,一个站那儿织,一个坐在旁边续“毛儿”,一晌下来,“十三脚,两头窝”的一领稿荐就成了。
无论绩箔还是打稿荐,除了麻经子、高粱秆或是浸泡好的一大捆麦草之外,少不了的工具就是缠经绳的“箔坠儿”。六道经儿的稿荐,就得十二个箔坠儿坠着经子“哐通哐通”来回掂。在我的记忆里,织稿荐的时候比织箔的时候多,为什么人们不把这断砖磨成的坠子叫“稿荐坠儿”呢?大概因为叫起来没有“箔坠儿”简单响亮吧。
箔坠儿在人们眼里算不上重要的工具,随便去哪个房屋檐底下、院墙角落里找几块碎砖头,拿刀砍砍,搁石头上磨磨,中间开个凹腰儿,不伤手能缠经子就成。有时候急活儿,一时找不到现成的,捡几块半截砖也能凑数。做箔坠儿,旧砖当然比新砖好,特别是那种从老房子上扒下来的,不沾水泥不沾沙,人手加岁月,磨光磨玉了,露出些麻坑,这是箔坠中的上品。不用的时候,箔坠儿就堆放在门旁边或窗户底下,风来了,雨去了,太阳晒晒又干了。一个个就像那个正和孩子们打闹嬉笑的白胡子老汉的脸。真要织起稿荐来,悬挂在门板两边的箔坠儿,简直就是两排弹奏生活的编钟:一老一小父子俩,或是一男一女两夫妻,一个续毛儿,一个手脚不闲地拉动经绳来来回回地织,他们小声地交谈着一些私密的话语,或是家常的打算,或是些田里庄稼,来回翻动的箔坠儿伴和着,微明的天光下,沙沙的雨声中,门板上稿荐一寸一寸悬垂下来,简单、安适而恬静。
枸杞
枸杞其实就是甜菜芽。春天到来的时候,风吹着生长在荒僻沟坡或是老坟园里的甜菜芽,一天一天把丛丛灰白带刺的枝条吹软,这些扎人的家伙伸个懒腰从冬眠中醒来,不住用带刺儿的舌头沙沙舔着阳光。雨脚扫过,挂在枝条上的水珠儿颤颤悠悠就变成了小不点儿的枝芽。那些小不点儿抽出一拃多长,掐下来焯焯,拌蒜汁儿就黑馍,吃起来青气黏牙有股儿甜味儿,于是,“甜菜芽”就成了它人人叫得响的小名儿。
枸杞还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红秦椒”。一蓬甜菜芽悬挂在高高的河岸上,不分昼夜憋足劲儿吮吸着天光水色,开出成串的紫花儿。秋天的时候,这些紫花就变成了尖尖头儿的“红秦椒”。
长长的暑假结束了,新学年开始了。打开新发的语文、算术,一股抓挠人的墨香从鼻孔直拱到嗓子眼儿里。自习的时候,孩子们摇头晃脑大声读课文:
“夏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可是我还十分想念……”
要不了几天,新课文中的字就被染出红黄蓝绿各不同的颜色。要是有十二色蜡笔就好了,可班里大多数同学都生在吃盐也要一粒一粒数的人家,三分钱一根的铅笔都不敢磨尖,怕浪费,谁家大人也没闲钱买这在他们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不过这不要紧,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办法。一放学,大家就在野地里四散开来,到处跑着寻找“红秦椒”。摘来的“红秦椒”也不全是长熟变红的,还有青的、半青不红的。拿起一颗,对准一行字,一边挤一边抹,红的抹出来是橘红色,青的是
苹果绿,半青不红的那些,会是淡淡的青、浅浅的黄。
入夜的广场上,我被大酒店狂红浪紫的霓虹招牌逼到假山下的角落里,鸵鸟一样深深埋头在灯光直射不到的地方,弯着两只手掌,为自己圈出一块小得可怜的幽暗。结满“红秦椒”的甜菜芽在幽暗里显现,慢慢地清晰,带青气的甜味儿来到我的舌尖上,瞬间滋润了一只鸵鸟的老心灵。
丝瓜
大年初二,所有的人都出门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和大片的阳光,和吹着口哨的风一起,等待丝瓜到来。半个多月了,那一篱丝瓜,时不时举起嫩绿的小腿儿,踢打我记忆的门窗,不幸的是,差不多每一次都被人和事和一些声音阻断了。
其实也没什么,几棵普通的丝瓜,种在房前下坡处那个狭长的菜园边儿上。栅菜园的高粱秆儿被雨水淋朽了,父亲就用槐树枝子修补。槐枝子有刺,打从那些黑得起绒发亮带白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