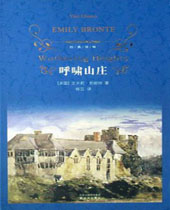歇马山庄-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
月月平静地看着国军,说我信。可是你已经不了解我了,我不是原来那个月月了。
国军说不,我了解你,你除了变黑什么都不会变,我保你还去教书,我们可以与家里脱离关系。国军说着要拥月月,边伸手边说,我们搬到镇上去住,我们到镇上买房子,永远不见买子和小青。
月月笑了,心想我怎么能不见买子,怎么会呢?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躲避着国军的亲近,默默等待国军离开。当国军从月月眼中看到毫不动摇的坚决,他跳到坑外抓一把沙土朝树枝甩去,日渐憔悴的苹果树叶哗啦啦飘然而落。
买子和月月
买子第二天中午,独自来到古本来承包的沙地。
古本来眨眨眼睛,眼角的肉球跟着晃动,先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买子说,我,我想看看月月。
古本来呼吸立刻粗起来,他摸来一根稻草一拽两截,你去看嘛找我做甚?程买子我就问你,你和她到底有没有事?
买子也从地上拣起一根稻草,在手上缠绕出一个个圈圈。本来叙,那都是过去的事,那时我的日子很空虚,她来找我……
古本来转过脸来,直视买子,哼,玩火不怕烧身,女人是好随便玩的?玩女人有罪!有罪你知不知道?
买子低下头不再吱声,对于月月,他是否有罪他还从未想过。
你叔我这辈子最怕什么?最怕伤害女人。古本来纹线模糊的眼角映出亮盈盈的东西。我四十岁上还没沾过女人的时候就知道女人是男人的命,不能伤她,哪怕一根头发。
买子听见古本来的语音是颤抖的,感到有些意外,他不知道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庄稼人心里装着这些东西。他用洁白的牙齿咬着嘴唇,本来叔,我确实不是成心伤她,我不知道她会为我离婚。
你不知道?古本来依然粗声粗气,但音质是低沉的,混沌的。你当初跟她好时就该对她负责,要不就不跟她好,你以为你是虎爪子吗?你以为女人都像潘秀英吗?
是的,她不是潘秀英,我不知道她会这样,我想让你陪我去看看她,你得陪我,本来叔。
古本来说,你想例行公事,走走形式?
买子沉吟似地笑了一下,说本来叔,你以为还能咋样?我就是一千个对不住她,我能离婚跟她结婚?我当着村长……
古本来愣神思谋着,语调平息下来,和蔼下来,说,她一天挖一个半果窝。
买子和古本来进到果园看到月月时,月月正像一个小松鼠似的爬在树枝上够落在枝头上的一只苹果。她听有吭吭的脚步声赶紧跳下来,当她回过头来看见古本来和买子,脸腾地升起一片彩虹,两手下意识揭开扎系很紧的头巾,然后将抓着头巾的手捧在腰部,眼睑在晒得有些粗糙的脸皮上忽闪忽闪,一会儿,就低下头去。古本来说翁老师—;—;古本来一直称她翁老师,古本来说村长来看看你……干的活。月月抬头冲古本来笑笑,赶紧跳到新挖有一尺深的果盘里边。见三人相见非常尴尬,古本来转身要撤。不想刚刚转身,买子就敏感地喊了一声本来叙,但他用背影告诉买子他不会回来。
自从古本来自己一走,月月就系上纱巾一锹接一锹往外甩土,再也没有抬头。买子愣愣地看着月月,准备好的话被不断甩上来的泥土打得七零八碎。这个奇异的女人同一个月前大不一样,鼻尖上布满雀斑,腰身被一套肥大的运动服裹着没有了以往的线条,她的整个外形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尤其那顶头巾在头上鸭舌似的杵着,地道的村妇相。月月的表现和外部形象一同抑制着买子准备在心里的话,他甚至有些后悔一念之间来到这里,他静默地伫立一会儿,见月月没有停下的意思,就扭头向外迈步。可是,他的步子刚刚迈开,就听月月在身后高喊一声程买子—;—;
买子回过头来,沙土不再向上飞舞,月月正正地对着自己,目光一下子就泊进她的眼里,深深的,牢牢的。月月说买子,我爱你!三个字刚刚出口,一汪眼泪就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滚落下来。这三个字在买子的生活中搁置了那么久,使他听起来感到有些陌生。其实这一直是月月向他表达的主题,而时隔几个月,它没有消失,竟再一次叫响在买子耳畔。买子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月月,准备好的话语终于寻到机会,翁老师,你受委屈了,我对不住你,我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后果。其实,其实你并不了解我,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我是一个很现实的男人,我一直是想有自己的女人,而你当时是国军的女人,这对我很重要。买子说着,停了下来,像发现自己走错路的人重新张望方位,因为这些准备好的话一经说出,买子感到它似乎是在肯定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倘若她不是国军的女人,他就会要她,这在最初是这样,在他没有来到这个荒僻的果园之前都是这样,可是眼下不是这样。并不是眼下的月月没有了往昔的风韵,不是,而是他从月月目光中发现,只要他在表达曾经对她有过的感情,哪怕是好感,她都会将“我爱你”的话义无反顾地说下去,说下去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这太可怕。买子将目光送到果树的枝桠上,好像正确的道路就在那晃动的枝杠间。他说,翁月月,你不是十八二十三,你应该现实一些,我觉得你一直都不现实,我说过,我是一个很现实的男人,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大概是停留在买子面孔上的目光太贪婪,太迷醉—;—;月月其实不光是在听话,而是在迷醉地吞噬他,买子的话使她一下子难以转换成仇视。月月在买子的话语停止之后,很久很久脸上都沉醉着一种激情。后来,心理的仇视幻做了一块乌云,在月月脸上笼罩下来,泪水隐进云层,不再滴落。月月有一种被推进深井的感觉,四周一片黑暗,只有买子一人在光明处,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在她和买子不算太长的相处的日子里,他从没有这样居高临下地和自己说话。月月赶忙低下头去,狠狠踩住坚硬的铁铣,一铣土在买子前方扬起弧形的抛物线,跟着,一句响亮的话语震响在买子耳畔:走吧我永远不要见你—;—;
这是月月多少年来喊出的最有力量最有底气的声音。买子从不知道一向温顺恬静的月月会如此歇斯底里,他慌乱地看着她—;—;这个偏执的、怪异的女子,他想这是怎么了呢?她怎么就会变成这样了呢?像一只被轰出家门的猫,买子缩头缩脑穿过果林。买子在转身离开月月时有一种豆腐掉进灰里的感觉。他并没得到设想中的那种成功,比如说出了温存的不失原则的话,月月表示理解,表示自己遭遇一切跟他无关,是命运的安排。他需要月月有一种姿态,有一种一切都跟他无关的姿态。只要月月有一种姿态,他就敢于好好地珍惜她,关心她,把她做为朋友,像当初她做为庆珠的朋友那样,他甚至想过把她用到砖厂当副厂长,砖厂正需要月月这种有文化有形象又性格沉稳的女子。然而他没有成功,月月变得不可理喻,他不知道月月想要什么,想干什么……
买子走出果林同古本来打了个照面,买子颓丧地看着古本来,说本来叔,你劝劝她,让她现实些,她现实些对谁都有好处,她该去找找国军,让他们恢复,他们应该恢复。古本来说,国军已经来过,翁老师不同意。两人一同沉默。许久,古本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女人。
月月
当着歇马山庄一村之长的买子,在为他曾经有过的一段小小迷失理智地做着技术性处理的时候,又一次打开了在爱河里迷茫跋涉并因此失去一切的月月血淋淋的伤口。
一段时间以来,月月已经习惯了在灵魂里、在感觉里与买子厮守、独语。在果园里,在黄昏的炊烟里,在黑夜的窗棂上,月月常能看到买子黑黑的小眼睛,洁白的牙齿。月月还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将手伸到腹部,轻轻而细心感受着里边的跳动。买子其实早已不再只是一个灵魂里的形象,而是一个支撑月月生命的一缕阳光,一缕炊烟,一丝轻微的波动。月月劳作着,浑身酸疼,却异常踏实。初做农人的月月每日上班挖土下班伺弄猪鸡鹅鸭,做着一日三餐,心情十分踏实,就像一个等待出民工丈夫的乡下女人,把盼头打入灵魂深处踏踏实实去过每一个日子。她在睡梦里都渴望见到买子,却怎么也想不到,买子的出现,会是这样一番景象……
治愈伤口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只有让她一寸一寸疼着,一针一针疼着。月月在买子走后好长时间没有停下铁锹,泥沙仿佛是那伤口上的溃烂之物,她拼力掘着,抛掷着,清理着,一直把脚下的一层泥土打扫干净,她才停歇下来。她人停歇下来,心口里的疼却并没有停歇,买子的话在她心口上一直钉钉子似的钉着:我是一个很现实的男人,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她想象过他吗?她想象过的他是个什么样子呢?她想象他心底是爱她的,像她爱他那样,只不过她没有早些告诉他她可以离婚嫁他,她想象她只要告诉他她可以离婚,他就能够去为她做到一切。然而,他没有如她所愿,他不是她想象那样的男人,他很现实,他想要属于自己的女人,他可以不管爱与不爱,他只想要没有属于任何人的女人,是黄花姑娘……疼是伴着理性的思考一层一层深入的,月月总是在伤口揭开时才从感情进入理性,才有理智。月月用头巾一角抹着额头上的汗,眼睛呆呆地看定冬季微风里抖动的树梢,她想自己多么傻啊,自己不是黄花姑娘还要爱情,简直岂有此理,爱情原来属于黄花姑娘……突然,月月在一个问题上停留下来,像一早她在果树上发现一只漏摘的苹果,那问题很耀眼—;—;买子与她对话的自始至终一直回避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爱情!他到底是否爱她?如果他是爱她的,只因她不是黄花姑娘,她是可以原谅他的。这时,月月第一次发现,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坚持,坚持要保留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认为买子是爱她的,而只要她确定无疑地知道买子是爱她的,她并不一定非要嫁他,只要他爱她,她就无怨无悔。现在,月月终于弄清一个事实,那便是买子一直绕着一个词,好像那个词是一个陷阱,买子所指的现实,不是爱情,而是爱情以外的东西,其实他对她是有爱情的,只是碍于现实的东西……
这么想来,月月感到疼在慢慢减轻。疼在降低了的标准上沾到一点药面,然后涂在了流血的崭新创面上。月月从来不知道,爱情,原来是这么不要脸面,不讲尊严,它竟然可以稍有缝隙,就乘虚而人,长成参天大树;它竟可以找到一切可以生长、站立的理由。
因为不再计较买子的态度,月月在这天剩下的时光以及后来的日子里心情略为平静,她再次爬到树上摘掉那只灰皮苹果,酸果汁随牙齿的咀嚼沁人肺腑时,月月感到胸腔里有股滚热的东西涌入喉口,与果汁汇合着让她呛出一串声泪俱下的咳嗽。
小青和买子
做着新媳妇的小青依然特别注重打扮,但一改未婚时的露星露月大紫大红,她竟然穿出了只有为姑娘才穿出的蓝色水磨牛仔衣裤和大开领西服套裙,头发也用电梳抻直,在脑后系成马尾巴,乡道上每每出现恍如仙人道士。对于蜜月,对于买子的肌体,小青有着一种超出山庄任何一个女子的疯狂热情,尽管她在买子点烧草垛那日,从买子的暴虐中觉察到了什么,但她事后从不再提,态度十分豁达。如果买子去村部,他们早上或中午就一起离家;如果买子在村部,他们中午或晚上就一道回家。只要他们在一起,小青就扯耳动腮动手动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恶作剧让买子对她的热情做出反应。山道上,她不是用柞木编织木环在后边套住买子,让他倒退,就是抽冷子将手伸进他的脖颈让他一高一高跳起;夜里,她不是闹着逼着买子露出大腿,用口红在他大腿上画出红红的花瓣,就是教买子一丝不挂和她在地上跳舞,小青使买子看到婚姻如何大胆地发掘着人的想象力,男人女人一进入婚姻,又是如何没有约束没有廉耻没有尊严。小青回家从不主动做饭,都是以不厌其烦的取闹方式给买子打着下手,有她咯咯咯的笑声响在屋里,买子早已忽视娶女人回家侍候老人的最初的理想。
然而,沉迷其中的买子就像身在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一样,他无法知道,小青婚后那种过分的喧嚣,正是一种激情退落的开始,如同已经沦为乡村妇女却偏偏故意用别致的服饰,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就连小青自己也不曾了解她的闹人缘于一种怎样的念头,她只是清醒地知道,只要面对草房小院,只要蹲进充满草灰的灶坑,只要见到瘫婆婆臭气熏天的便桶,她就涌起鼓噪买子的念头,她就特别想在孤零的院子里、空旷的山野上听到自己的笑声和买子的笑声,就特别想让村里的人听见他们的笑声。显而易见,蓄意鼓噪的热情总有消失殆尽的时候,那是入冬之后的一个上午,小青带领全村育龄妇女到镇卫生院透环—;—;每年一到初冬,出民工男人回乡之前,歇马镇妇联都组织一次避孕措施大检查。女人们走到一起仿佛麻雀聚会,东家长西家短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有人说林小青,看你这身打扮,真想不到你能去伺候瘫婆婆。另一个声音赶紧接上,我宁愿下田干活出大力,也不愿伺候病人,买子当村长,那不明摆着老人负担在你身上。于是有人问,林小青你将来生了孩子谁给你哄……因为有种种无形的东西推动着她跟买子的婚姻,她对结婚之后充当的角色和这个角色将面临的一切从没细心想过,女人的话给她做了个准确的定位,她要生孩子,她要伺候瘫婆婆,而她原本不是一个能够伺候病人的人,她原本就没想做乡下女人,她原本应该是个城市人;即使不是城市人,至少应该离开歇马山庄,或者嫁个有钱人家。现在她做了乡下女人,她嫁的男人没钱没地,还有一个瘫妈妈……回来的路上小青心里很堵,好像有须草塞在心口。心口堵,又没有买子在跟前让她戏闹,叫女人从她们的戏闹中领略她的生活并不像她们想象的那样可怕,骑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