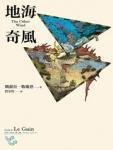地海孤雏-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天,刻意安排的巧合让恬娜与亚薇在村里街上相逢。她对亚薇说:「亚薇太太,我有问题想请教你。与你的职业有关。」
女巫看了看她,眼光尖锐刻薄。
「我的职业,是吧?」
恬娜稳稳点了头。
「那跟我来吧。」亚薇耸肩说道,领她走过磨坊巷,到自己的小屋。
这里不像蘑丝那声名狼藉、家禽四处的巢穴,却也是间女巫房舍:屋梁满挂已干燥或待干燥的草药;炉火堆埋在灰烬里,只剩一小块煤炭有如红眼般眨巴;一只窈窕丰润、嘴长白须的黑猫在架上安睡;四周散置小盒子、盆子、水罐、托盘,及有瓶塞的小瓶,充满芳香、恶臭、甜美或奇特气味。
「我能为你做什么,葛哈太太?」两人进屋后,亚薇极度冷淡地问。
「请你告诉我,你认为我的养女瑟鲁是否有任何在你技艺方面的天分?她是否有力量?」
「她?当然有!」女巫说道。
这立即、鄙夷的回答让恬娜一时哑口无言。「这……」她说道:「毕椈好像这么想。」
「连洞穴里的瞎眼蝙蝠都看得出来。」亚薇说:「就这样?」
「不。我想要你的建议。我先问问题,你再告诉我回答的代价。公平吗?」
「公平。」
「我应不应该在瑟鲁长大一点时,让她跟女巫学艺?」
亚薇沉默一会儿。她正考虑价码,恬娜想。但她回答:「我不会收她。」
「为什么?」
「我会怕。」女巫答,突然狠狠盯了恬娜一眼。
「怕?怕什么?」
「怕她!她到底是什么?」
「一个孩子,一个遭受恶行伤害的孩子!」
「她不仅是如此。」
深沉怒气进入恬娜体内,她道:「所以女巫学徒必须是处女,是吗?」
亚薇凝视她,一会儿后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是,她用一只可见、一只失明的眼睛看我时,我不知道她看见什么。我看着你像带普通小孩一样带她,心想:『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她不愚蠢,但哪个女人有力量,能以手握火、以龙卷风纺线?』太太,有人说你还是小孩时,与太古者——暗者、地底者——同住,你是那些力量的女王与仆人,或许因此你不怕她。她是什么力量,我不知道、我不能说,但这超越我或毕椈的能力所及,甚至超过任何我所知晓的女巫或巫师!太太,让我给你免费的建议:小心。小心她,小心她发现自身力量的那天。如此而已。」
「我感谢你,亚薇太太。」恬娜以峨团护陵女祭司的冰冷礼仪说道,离开温暖房间,走入秋末稀薄刺骨的寒风。
她依然愤怒。没人愿意帮她,她想。她知道这件工作超过她的能力,他们毋须告诉她这点——但没人愿意帮她。欧吉安过世、老蘑丝胡言乱语、亚薇警告连连、毕椈置身事外,而格得,唯一可能真正帮她的人,逃走了,像丧家之犬般逃跑,没捎给她只字片语,完全没考虑到她或瑟鲁,只有他自己宝贵的耻辱,那是他的孩子、他嗷嗷待哺的婴孩、他在意的一切。他从未关心或考虑到她,只关心力量:她的力量、他的力量、他能如何运用、他能如何从它创造更多力量——愈合断裂的环、创造符文、让王登基。而他的力量消失后,他还是只能想这件事:它不见了,消失了,只留下自己给自己,他的耻辱,他的空虚。
你不公平,葛哈对恬娜说道。
公平!恬娜说,他有公平相待吗?
有的,葛哈说道,他有。或者试过。
那好,他可以跟他赶的山羊公平相待,跟我完全无关,恬娜说,在寒风及第一波稀疏冰冷的雨滴里,蹒跚拖步返家。
「今晚也许会下雪。」她的佃户提夫说道,两人在卡赫达河边草地旁的路上相遇。
「这么早就下雪?希望不要。」
「至少绝对会下霜。」
太阳下山后,一切冻结,水洼跟水槽表面浮现一层薄膜,而后冻成厚厚一层白冰;卡赫达河边的芦苇静止,锁闭在冰块中;连风都止息,仿佛亦被冻结,无法吹动。
清理晚餐残肴后,恬娜和瑟鲁坐在比亚薇家更香甜的炉火边,纺线、谈话,柴火是去年春天果园砍下的老苹果树。
「说猫鬼的故事。」瑟鲁以沙哑声音说,一面转动纺轮,将一堆乌黑如丝的山羊毛织成细毛线。
「那是夏天的故事。」
瑟鲁歪着头看她。
「冬天是说长篇故事的时节。冬天时,你得学会《伊亚创世歌》,好在夏天的长舞节歌唱;或学会『冬颂』与《少王行谊》,然后等太阳北归、带回春天的日回祭时,你就可以唱了。」
「我不会唱歌。」女孩悄声道。
恬娜正取下卷线杆上的毛线,绕成一团球,双手动作灵巧,富有韵律。
「不仅用声音唱,」她说:「脑子也要唱。如果脑袋里不通晓这些歌谣,就算有世上最美的歌声也没用。」她解下最后一段,也是最初完成的毛线。「你有力量,瑟鲁,但无知的力量充满危险。」
「像不愿学习的它们,」瑟鲁说:「那些野蛮的。」恬娜不了解她的意思,疑问地看着她。「留在西方的那些,」瑟鲁说。
「啊……楷魅之妇的歌谣……那些龙。没错,就是如此。那么,我们该从哪首开始?从岛屿如何从海中升起,还是莫瑞德王如何驱逐黑船?」
「岛屿。」瑟鲁悄声道。恬娜原本期盼她会选择《少王行谊》,因她将黎白南的面容与莫瑞德重迭,但孩子的选择是正确的。「好。」她抬头偷瞥置于壁炉上欧吉安硕伟的智典,激励自己,如果忘记片段,可以从中寻找。她深吸一口气,开始诉说。
等瑟鲁该就寝时,她已经知道兮果乙如何从时间深渊抬起最初的岛屿。恬娜为她塞好被褥后,坐在床沿,这晚没有为她唱歌,而是两人一同轻声背诵创世歌的第一诗节。
恬娜将小油灯提回厨房,凝神倾听绝对的沉静。冰霜束缚整个世界,将它锁闭。星辰皆无,黑暗压迫厨房内唯一的窗户。冰冷铺在石板地上。
她回到火边,毫无睡意。歌谣伟美的字词激动她的心灵,而与亚薇谈话后引发的怒气及不安依然残留体内。她拾起火钳,从壁炉内垫底的大木柴唤醒一小簇火焰。她触撞到木柴时,房屋后端同时传来一阵回音。
她直起身,专注聆听。
又一次:轻微、沉闷的敲击或落击声……在屋外……牛奶房窗户那儿?
恬娜火钳在手,走过黑暗走廊,通往开向后方凉室的房门。凉室之后就是牛奶房——房屋本体倚山而建,这两个房间则像地窖般嵌入山体,但与房屋其余部分同高。凉室只有通风口,牛奶房则有扇门,还有扇窗,像厨房窗户般低矮、宽广,安在唯一的外墙上。她站在凉室里,可以听到那扇窗正被拾起、撬开,还有男人低语。
火石是按部就班的主人。整间房子,除了一扇门两侧没各安上一条滑动长铸铁作为门闩外,其余每道门闩都保持清洁、上油,却也从未上过锁。
她拴上凉室门闩,铁条一声不响滑动,稳稳嵌入门框上沉重铁闩槽。
她听见牛奶房外门打开。有人终于在打破窗户前,想到先试试门,发现并未上锁。她又听到喃喃声响,然后一片死寂,漫长得让她只听见自己鼓动的心跳,大声到让她害怕会掩盖所有声响。她感到双腿一再颤抖,地板的冰冷像只手般从裙底攀上。
「是开的。」男人声在她附近低语,让她的心脏痛苦狂跳。她将手放在门闩上,以为是开着——以为她原来是打开而非锁上——正要拉回门闩时,听到凉室与牛奶房之间的门吱嘎一声开了。她认得上铰链的辗轧声,也认得说话声,但缘由天差地别。「是储藏室。」悍提说。她倚靠的门扇喀喀作响,撞击门闩。「这扇门锁着。」门又喀喀作响。细锐的一道光像刀锋般自门扇及门框间闪射而入,触及她胸口,令她向后一缩,宛如被割伤。
门再次喀喀作响,但不太剧烈。这扇门装设得十分坚固,门闩也牢不可动。
他们聚集在门的另一边低声讨论。她知道他们打算绕到前方,试图开启前门。她发现自己已身在前门,上闩,完全不知道自己如何抵达此处。也许这是个噩梦,她做了一个梦,梦里他们想侵入屋内,以细薄的刀子刺入门缝中。门……还有什么他们能进入的门?窗……卧室窗户的窗板……她的呼吸如此短促,还以为自己走不到瑟鲁房间,但她到了,将沉重木遮板横在玻璃前。铰链僵涩,木板砰地一声关起。他们知道了。他们正往这儿来。他们会到隔壁房间的窗前,她的房间。他们会在她还未关上窗板前就到来。他们到了。
她看到脸,一团团模糊在外面黑暗中移动,她试图松开左边窗板的搭扣,卡住了,她无法移动分毫。一只手砰地摸上窗户,紧贴成死白一片。
「她在那儿。」
「让我们进去。我们不会伤害你。」
「我们只想跟你说说话。」
「他只想见见他的小女儿。」
她松开窗板,强拖着关上窗户。但如果他们打碎玻璃,就能从屋外推开窗板。扣环只是一个锁在木头里的勾子,用力一推便能扯落。
「请我们进去,我们就不会伤害你。」其中一个声音说道。
她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踏在冰冻地上,踩得落叶沙沙作响。瑟鲁醒了吗?窗板关上的巨响可能吵醒她,但她没发出半点声音。恬娜站在她与瑟鲁房间之间的门口。一片漆黑,无声无息。她不敢碰触孩子唤醒她。她必须与孩子留在同一个房间。她必须为她而战。她手中本来拿把火钳,放哪儿去了?之前她放下它,好关上窗板。她找不到。她在无边的漆黑房间中,茫然摸索。
通往厨房的正门喀喀作响,撞击门框。
如果她找得到火钳,她就会留在这里,与他们对抗。
「这里!」其中一人喊道,而她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他正抬头看厨房窗户,够宽、没有窗板遮挡,伸手可及。
她摸黑走,行动非常迟缓,走到房门前。瑟鲁的房间曾是她孩子的房间,育儿室,因此房间内侧没有门锁,让小孩无法将自己反锁,也不会因门闩卡住受惊。
山后,穿过果园,清溪及香迪熟睡在村屋里。如果她大喊,也许香迪会听到。如果她打开卧室窗户大喊……如果她叫醒瑟鲁,两人爬出窗外,跑过果园……但那些人正在那里,就在那里,等着。
她终于无法忍受。束缚着她的冰寒恐惧立时粉碎,凭着一股怒气,她红着眼冲入厨房,从砧木上抓起长而锋利的屠刀,扯开门闩,立定门口。「你们来啊!」她说道。
她刚开口,便传来一声哀嚎与倒抽的喘息,有人大喊:「小心!」又有一人惊叫:「这里!这里!」
然后是一片寂静。
从洞开门口射出光线,照映在水洼的黑色冰面,晶亮亮闪在橡树黑枝与银白落叶上,她恢复视力后,看到有东西从小径向她爬来,深暗的一团或一堆东西向她爬来,发出尖锐、啜泣的哀鸣。在光线后,一个黑色形体奔跑纵跃,长刀锋银亮。
「恬娜!」
「站住。」她说道,举起了长刀。
「恬娜!是我……鹰,雀鹰!」
「别动。」她说道。
纵跃身影立定在歪躺小径上的黑色堆团旁。门口射出的光线微弱地映照出一个身体、一张脸,还有一把直立的长铁草耙。像巫师的巫杖一样,她想。「是你吗?」她说道。
此刻他正跪在径上黑色物体旁边。
「我想我杀死他了。」他说。他越过肩头回望,起身。没有动静,亦无声响。
「他们在哪?」
「跑了。恬娜,帮个忙。」
她将刀子握于一手,另一手抓住蜷缩在门径上的男人手臂。格得将他自腋下扶起,两人将他拖上台阶,进屋。他躺在厨房石板地上,血从胸膛跟肚腹上的洞口像倾倒水壶般汩汩流出。他上唇后掀,露出牙齿,眼睛只剩眼白。
「锁上门。」格得说,她锁上了门。
「柜子里有布。」她说。他取出一条床单,撕裂成绷带,让她一圈圈绑在男人肚腹与胸膛上,草耙四根铁叉全力戳出三个洞。格得撑起那男人上半身,好让她缠绕绷带时,血浆泉涌而出,四处喷洒滴落。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跟他们一起来的吗?」
「对,但他们不知道。你能做的大概也只有这些了,恬娜。」他任凭男人的身体滑落,往后仰坐,沉重呼吸,用沾满鲜血的手背抹脸。「我想我杀死他了。」他重复道。
「也许吧。」恬娜看着鲜红点缓慢扩散在男人瘦弱毛茸胸膛及肚腹缠绕的绷带上。她站起身,晕眩摇晃。「快去炉火边,」她说:「你一定快累垮了。」
她不知道自己如何在外面的黑暗中认出他。也许是他的声音吧。他穿着一件厚重冬季牧羊人外套,用一片片羊毛皮缝制而成,皮外毛里;戴一顶牧人毛织帽,压得低低的;脸上刻画线条与风霜,发长而铁灰;全身气味像木烟、霜雪,混合绵羊味。他在颤抖,全身震动。「快去炉火边,」她又说:「加点木柴。」
他照办。恬娜装满水壶,勾住铁手把,让它一摇一晃垂挂在烈焰上。
她将布单一角浸泡在冷水中,擦拭衬衣上沾染的血迹。她将布块交给格得,让他抹去手上鲜血。「这是什么意思?」她问:「你说跟他们一起来,他们却不知道?」
「我下山,在从卡赫达泉来的路上。」他以平板语调说着,仿佛上气不接下气,颤抖混浊了语音。「听到后面有人,我就靠边。到树林里。不想说话。不知道。他们给人的感觉。我怕他们。」
她迫不及待点头,隔着壁炉在他对面坐下,前倾专注聆听,双手紧握腿上。她潮湿的裙子靠着双腿,一片冰冷。
「我听到他们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