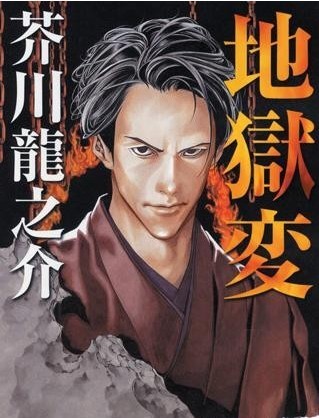燕垒生中短篇作品集-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杨国光记的谱啊。他笑了笑,道“中国古代有一种四景盘,就是把棋盘上的三百六十一个点全部用不相同的字填满,一般是四首汉诗。而记谱时,棋子下在哪儿,只消把对应的字记下来就可以了……”
突然,他一阵惊愕。
他终于明白杨季轩为什么为答应高川大佐要他下棋的要求了!
“你记的谱呢?”当想通这一点,他迫不及待地对岛田作道。
※※※
那不是一个高手应有的棋路!
小野田当看到绪方在那美国人身后用唇语传出的谱时,几近于震惊。
俗手!不折不扣的俗手!
按杨季轩的棋力,绝对不会下出这等棋来的。难道是绪方传错了?可当他用疑问的眼光投向绪方时,绪方却报以肯定的答复。
如果没有错,那么杨季轩肯定有自己的算计吧。可是,不管怎么想,这一手下去,盘面一下便要落后。现在还是第六手,若落后那么多,后面又该怎么走?
他端坐着,只是难以决断。
这种国际围棋赛虽然只是军部作为接管上海后的余兴节目,但如果冠军被一个美国人夺走,也难以说得过去吧。这五番棋已到了第三局,第三局是五番棋中的天王山。不管前两局胜负如何,第三局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自己已连负两局,这天王山也已是奈何桥了。
要按杨季轩的谱下么?他咬了咬嘴唇。
二十三岁的江户麒麟儿,方圆社后期的四天王之一,如果下出这样的棋来,那可真要成为笑柄。可是,他也实在无法不相信杨季轩。
他把棋子放入枰中。
果然,克雷德抬起头,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这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居然也有一股东方式的儒雅之气。
但愿杨有妙手吧。他暗暗地祈祷。
这一招俗手使得克雷德长考了半个小时。因为限时两小时,加上布局时用去的时间,克雷德已经只剩不到一小时了。
也许是杨季轩的战术吧。当下一招俗手由绪方传来时,他想着。克雷德已经脸上露出喜色来了,即使有再多的东方教养,他体内流的还是美国人的血。这一次他不再长考,飞快地应了一手。
这一定是个欺招。小野田麟三郎想着,可是绪方一直没有传来新的棋招,他也只好做出长考的样子。
大约也过了半个小时,绪方才重又走出来。
果然啊。当得到绪方传来的那新的一步,小野田几乎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那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虎,但这一招棋却似点铁成金,刚才那两招俗手一下化腐臭为神奇。
几近耳赤之妙手。
在心底,他暗自这么评价。
当年秀策与幻庵争胜,秀策执黑先行,一百手以前,幻庵始终与秀策分庭抗礼,且隐隐有反客为主之势。至一百二十七手,秀策一招落枰,使得幻庵面红耳赤。这一招后来便被称为“耳赤之妙手”。
这么早便放出胜负手,那也只有杨季轩才敢为吧。
果然,克雷德已是双眉紧锁,耳根也红了起来。他一定想到了先后无数变化,但没有想到二记俗手后还会有这等一招。
真是匪夷所思的手筋啊。小野田麟三郎暗自赞叹着。
后面几乎妙招奇招层出不穷,盘面上他所持的白子已愈发生动,反观克雷德的黑子则疲于奔命,处处受攻。每当绪方传来一招棋,第一个惊叹的反倒是小野田了。
终局之时,白子不用黑子贴目,便已领先三目了。
克雷德面如死灰,站了起来,向小野田鞠了一躬,道:“先生,你的棋力,今天比昨天已大为进益了。”
他说的是汉语。大概克雷德只会说英语和汉语吧。小野田不知该如何回答,克雷德忽然人一歪,倒了下来,将棋上的棋子也推了一地。随之,一口血呕了出来。
陪同克雷德来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抢上来刚扶起克雷德,却听得里面忽然传来一阵杯子碎碎的声音,随之,是一声枪响。小野田麟三郎吃了一惊,冲进了里屋。刚一进去,便见高川大佐正往腰间插枪,杨季轩倒在地上的一滩血泊里。
“出什么事了?”
高川大佐把枪放好,道:“杨竟然来袭击我!”
他的话里也带着惊愕。确实,在这里袭击高川大佐,那和自杀没有两样。可如是杨季川的确是不想活了,那又何必来下这一局棋?
两个士兵来抬走了杨季轩的尸首,小野田道:“大佐,那山木课长那里怎么交代?”
高川大佐道:“那没什么不好办的,给杨发个讣告,说他为皇军尽力,劳累过度而去世。哼哼。”
小野田初听还是一怔,但马上恍然大悟。这么一来,就算杨季轩弄走的情报能送到中国政府那里,恐后也不会有人信了。他站直了,由衷地道:“嗨!”
小野田对照岛田作纪录的谱,按照杨国光的谱,一个字一个字地试图还原杨国光记谱所依据的盘式。
尽管过去了四十年,与克雷德那惊心动魄的一局他还牢牢记着。那一次克雷德因为用心太过,回去后马上生了场大病,后两局也弃权了。从此,这个棋力绝高的美国人也再没出现过。
如果不是战时,那一局一定会成为传颂后世的名局吧。
他淡淡地想着。
岛田作和杨国光的棋共下了一百五十五手,其中有打劫放在同一位置的,所以只有一百五十一个位置能填字。换句话说,杨国光所依据的盘式,他只复原了一小半。这盘式,多半是杨季轩自己设计的吧,用的全是些常用字。
但依靠这一小半,已足够破解出杨季轩的谜了。
杨季轩的前七手,如果按杨国光那种谱记下来,是“安同洋行西墙下”七个字。
安同洋行,是闸北的一家洋行,那时也确实存在,就在离高川支队驻地不远。如果说杨季轩下的棋是偶合,那也太不可思议了。这肯定是他早就和外面人设好的通迅方法,用棋谱来传递消息。
怪不得,他当时一定要求将棋谱登在申报上吧。外面,他的同党恐怕时刻都会关注棋谱,就算不知道这局棋是他下的,也很有可能会发现其中的秘密。
杨季轩即使早有死志,想的,仍然是要把情报传出去啊。
小野田麟三郎把几张纸都撕得粉碎,扔进了边上的痰盂里。
那两招俗手,其实并不是他放出的胜负手或欺招,而是因为选字的缘故,不得不下出那两招恶手来吧。可是,以这两招恶手之后,居然还能反败为胜,甚至逼着克雷德吐血,这杨季轩的棋力到底已到了何等程度?看着纸上的字迹在痰盂里一点点洇湿,变模糊,小野田麟三郎忽然有一种欣慰。
可恶的支那人,幸好那局棋谱最终并没有公布。
他想着,只见来送行的上海官员正向这儿走来,脸上带着一股灿烂的微笑,不用猜也知道他时刻都要说出“中日友好”之类的话。
※※※
黄永卫拍了拍桌子,喝道:“杨国光,你里通外国!说,你和日本人有什么关系?那天为什么把一张小纸条放在桌上?”
杨国光嚅嚅地道:“我不认识他们啊,那张纸条只是我记得棋谱……”
“胡说!你会记什么棋谱?刘书记看得清楚,那是张写满字的纸条。”
杨国光睁大了眼,有点惊慌失措,他大声说:“那是棋谱,是按我爷爷传来的记谱方法记的。”
田书记在一边义愤填膺地道,“你爷爷是汉奸,日本鬼子还为他发过讣告,你爸爸就是汉奸的儿子!你也是汉奸!”
台下,群情激昂的学生们终于在老师的带领下举拳高呼:“打倒汉奸!”他们手里的小红旗此起彼伏,依稀还是那天欢迎日本围棋代表团的架式。
有约
1…A
出差总是让人心烦。
如果说,平常的出差让人心烦,那么这一次则更让人心烦。拎着一个包,防备着小偷、搭上来的可疑的女人,以及似乎无处不在的联防队员,我走到了一个迷宫一样的小巷子里。
这居然是我的故乡?然而我搜索着我可怜的记忆,却找不出一点熟识的地方。故乡于我,也如一个陌生人一样了,包括早已忘了的乡音,那些江南常见的黑瓦白墙,那些随风摇曳的瓦松,以及坐在门前下棋的老头子。
一个老同学告诉了我他的地址,而我出差每天有二十九元的差旅费,如果不想在个体旅馆里被跳蚤和蚊子咬死,我就得拿出我半个月的工资去宾馆住一夜,这当然让我无法接受,所以我满心希望找到我朋友的家。可是,在这些迷宫一样的小巷子里,当我第三次转到边上的墙上画了一个眼睛,写着“不得在此小便”的垃圾箱边,我开始绝望了。这些人的语言,简直比非州土人的话还难懂,我都不敢相信我小时候居然也能说一口这样的方言,至少现在我连一个字也听不懂。我问了几个好象很有学问的人,他们除了发出一些鸟叫一样的声音,让我听着,一会儿说要向东,一会儿又说要向西,让我觉得象是来到一个花鸟市场。当我掏出纸想让他们写下来时,几个人的笔迹简直可以贴在门上当驱鬼符用。
正当我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孩子,指着巷子尽头的一幢房子,吱吱呀呀地说了半天话。我只好拎着包,照他的指点,或者说,自以为照他的指点,向那房子走去。
1…B
眼睛。眼睛里下着雨。
你看着窗外。窗子是明亮的,又逐渐变暗,然后变成了流泪的眼。你推开了窗子,雨点一下子蜂拥而入,“叭叭”地响着,打湿了放在桌面上的台历。台历上,那两个并肩高举着《毛主席语录》的工人农民也被打湿了,本来已经变得发白的红宝书一下成了暗红色。
——你这孩子,下雨天怎么把窗子打开了?快关上。
象沉没在古井里又冒出来的声音,你听见窗子被关上了。你只好垂头丧气地坐在窗前,无聊地玩着一盒积木。
雨打在玻璃窗上,雨中,那棵泡桐树的叶子不时有一两片被雨打落下来。即使在雨中,也象飘过一片碎纸片。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你听见门开了。门外走进来一个灰色的人。
灰色的人。纤细的身影,即使穿着灰布衣服,也一样是纤细的,如一枝芦苇。在一张雪白的脸上,你看见了两个灰色的,象有阴云密布的眼睛。
——小吟,你怎么了?
你听见了一个轻柔和忧伤的声音。即使那声音象是从极远处传来的幽渺而不可辨认,你还是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声音。
你吸了一口气,看着那两只忧郁的灰色眼睛。映在玻璃窗上,若隐若现,有时一片树叶落下,又仿佛长在树叶上的。尽管你知道那眼睛里并没有你,你还是垂下头。
——别哭了,想开点吧,人总要活下去,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你看着窗子,那两只眼睛好象闭上了,但你知道没有。很古怪,映在玻璃上的别的部份都那么模糊,唯有这一双眼清楚得象是用淡墨勾出。
——我走了。
那个声音胆怯而痛苦,你看见那个灰色的影子从你眼里消失了,玻璃窗上,依然是室内的几件旧家具,还有墙上的一张画。你伸出手去,胆怯地试探着空气,似乎想知道那个影子是不是还留着一点体温,可是,当你的细嫩的手指碰到玻璃时,指尖上传来的冰凉的感觉让你很不舒服,象是浸入一团冰水。你看着窗外,试图看到在暮色中的那一个人影,可是,什么也看不到,除了雨。
2…A
这房子也有点年头了,门是厚厚的木板,上面有个向里开的小窗,但没有电铃。本来门上有过红漆,但如今全都褪了,成为松散的褐色,如果用指甲掐一下,就可以掐下一块来。我在门上敲了两下,半天,才听得里面“踢踢踏踏”地,一个人拖着拖鞋走出来。
门上的木板窗开了,一张干瘪得象一颗没成熟的花生一样的脸出现在小窗里。
这很让我吃了一惊。在这张脸上我找不到一点我那个老同学的样子。尽管我们也已十几年没见了,但这张脸一来还是太老了,二来也太怪了点,松垮垮的皮肉上,也没一根胡须,几乎象个老太监的脸。我还没有开口,他就很凶狠地问道:“你是谁?”
他说的倒是很标准的普通话,不管怎么说,我总算碰到一个能问话的人了。我刚想拿出我朋友的地址,他却很热情地说:“唉呀,是你啊,瞧我这记性。”
他拉开了门,门发出“吱呀”地噪声。我不由一怔,说:“你认错人了吧?”
“不会的,变成灰我也不会认错你。”他有点幽幽地说,正是黄昏,在他的话语里,也象浸透了暮色。他已经向里走去,我只好跟了进去。
里面是个院子。这院子出乎意料地大,到处杂草丛生,只有一条象是荒地里的路,狭窄而又简单,只是一条用石子铺成的小道。
路是直直的,只是深可过膝的草渐渐侵上了路面,象是无所不在的记忆。尽头是一间很旧的房子,他拉开门,说:“看,还不错吧。”
2…B
——叫吟姑。
你抬起头,看着那两只眼睛。那是两只细长的灰褐色眼睛,大大的眸子明亮而寂寞。如果在春天下过最后一场雪,那一定就是这样的。
——吟姑。
——真乖。
又象是珠子沉落在古井里的声音。即使是蹒跚学步的你,也感觉到一只柔软的手掌抚上你的头,象一阵细雨。
象一阵细雨轻轻洒过瓦。
象一钩残月送我走回家。
你看见了那只细长而洁白的手抚在你头上,留得很长的粉红色指甲象一片脆薄的春冰。你看见那只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你的脸,又缩了回去。从袖口望去,你可以看见手腕上蓝色的血管在轻轻跳动。
——现在好些了么?
——是啊,谢谢。
你看见那个身影走远了,即使是黄昏。一只飞鸟掠过天空,落在树梢上,路灯还没有亮。墙上,血红的大字已经要滴下来一


![(伪装者同人)[伪装者]明楼中心短篇集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1/2143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