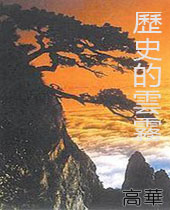漂泊的云-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招呼来人的茶水,有时,还要请别人吃饭。
我按照当年海灯武馆老师的教学方法一招一式地认真教,大家都很尊敬我,亲切地称我“梅老师”“梅教练”。十九岁的我感到一种无比的自豪和喜悦。
假如不是一个月后何乡长找上门来,我也许会考虑一直办下去的。
原来乡里发生了一起打架斗欧事件,主犯的男子说是在我这里学武术的。另外,有人造谣说我每个学生收了三十元钱的学费。我很委屈气愤。何乡长说:“你要教也可以,必须办营业执照。”想到办营业执照要四百元钱,我又怕自己武术浅陋误人子弟,我决定解散培训班。
(三)
培训班一解散,我又开始烦恼。家里是呆不下去的,我又只能回滨州吗?这时父母暗示我去拉萨武警总队找八叔或许有办法。
我动心了。
八叔是我父亲的弟弟,只比我大六岁。八叔高中毕业后便入伍当兵,后来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军事学院,那时在拉萨武警总队当参谋长。
我一直很佩服八叔。而且,我和八叔曾有一段草绳缘。
据说我小时候八叔很喜欢背我。六月天气,他就搓草绳,光着上身,用绳子背,汗水一个劲儿地往下淌,他也不肯放下歇一歇。有时实在背不动了,他就双膝跪在地上慢慢爬。有人问他:“你不上学了?”他歪着头认真地说:“我把小侄女背大就上学。”
虽然我和八叔好多年不曾谋面,但我坚信,我的叔叔,我最喜欢、最敬佩的八叔,我最疼我的,关心我的八叔会给我指出一条希望之路;我坚信,我的叔叔能够也可以为我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暂时遮蔽着我,一个疲惫的跋涉者……
-
八月底,我坐了近六天的车终于在一个黄昏来到拉萨武警总队。我从来没有想到八叔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滚!从哪里,就滚到哪里去!”犹如晴天霹雳!只觉天旋地转!倔强的我含泪转身就走。八叔又吼道:“这么晚了到哪里去?要走也明天走。”
在拉萨的五天,我几乎是在泪水中渡过的。我不敢提半句让八叔给我找工作的事。八叔一直不给我好脸色,并一再说:“我再也不回仁寿了,这个大家庭的忙我谁也不帮!除非梅勇有一天找到我,我也许可以考虑,毕竟他是我们梅家的长孙。”梅勇是我二叔的儿子。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来拉萨的第二天早上,我习惯性地起来练武术,八叔撞见,又是一阵劈头盖脸地大骂:“还不快滚进去,丢人现眼!”诚然我的武术练得不好,也不至于如此大发雷霆啊!那个温和友善的八叔到哪里去了?或者是八叔觉得我不配练武术吗?因为我是近视眼。还记得八叔像是为我担心,又像是对我嘲讽地说:“你戴个眼镜以后怎么上山干农活?”当时我的心里就有点委屈:为什么以后我就必须上山干农活?难道就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如果八叔知道我喜欢武术,还梦想有一天成为教练,不知道又该做如何感想?!我什么也不想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八叔曾带我到布达拉宫游玩拍照。虽然这是我曾梦寐以求的,虽然眼前是一片金壁辉煌,但我始终提不起兴趣,那缕笑容要有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我走的那天,八叔送我到车站,为我买好到格尔木的车票,又递给我三百元钱说:“你拿去买件毛衣吧,天气冷了。”我的鼻子骤然发酸,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我知道八叔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只是他不明白我需要的不仅仅是毛衣。
我到滨州之后曾给八叔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音信,我也就不再和他联系了。
听说八叔现在病退了,在成都买了房子,一家三口过得挺滋润。
我们很少见面,见了面也不过是点头微笑。提起八叔,我不再激动,甚至有种与己无关的感觉。是的,对于我来说,八叔是越来越遥远了,遥远得如同童年的梦!
不过,我还是常常想起童年,想起奶奶和妈妈讲的故事。八叔,你真的忘记你曾经背过的小侄女吗?八叔,如果我还是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女孩,你还愿意背我吗?
当我无言地告别八叔时,我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我想,我只能去山东了,在我最困难时,亲人都不给予帮助,惟有山东滨州那个厂给我汇来两百元钱。他们说过,他们的门永远是朝我敞开的!或许,或许他们能收留我吧!我还不能死,我还有好多事情好多事情要做,那太多太多的情,那无法偿还的感情的债……
到格尔木后,我坐上了由西宁开往青岛方向的列车。广播里潘美辰在唱《我想要有一个家》“……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我的泪水滚滚而下,模糊了双眼,模糊了外面的世界!哦,我只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学习、工作、生活,我只想要一个可以流泪的地方!当我有能力偿还债务之后,我将回到四川,回到父母的身边,用我全部的心血写一部,写一部关于我,关于我的家庭的……
(四)
“推不开窗户
外面是飞扬的沙土
听不到喧哗
城镇的繁华早已悄然远离
水,是一湾浑浊的池塘
半池的荷,开不出艳丽的花”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山东东营广北农场。
十月十日,李厂长派我跟随几位老师傅到东营广北农场的炼油基地,一边为老师傅做饭,一边跟魏师傅学仪表。
在广北农场那个近乎闭塞的地方,我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充实的。白天做饭、跟魏师傅学仪表,晚上看文学书、写点东西。记得那时,我还试着写了两首歌词,一首是《让我再唱一曲》,另一首就是《梦的泪痕》。
那时跟魏师傅学仪表的还有广北农场的一个本地青年小丁。小丁刚电大毕业,戴一幅近视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由于我们年纪相近,又都爱好文学,很快成为一对好朋友。
小丁的家有点远,所以,小丁在农场有一间单独的小屋。说来也巧,小丁的小屋就在我小屋的对面。
每当深夜寂寞地苦读,或者,无休无止地写稿抄稿时,我总会不时抬头凝望窗外,凝望小丁小屋的灯光。当发现灯光依旧明亮,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微笑,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一直伴我进入甜甜的梦乡。如果有一晚发现小丁小屋的灯光突然消失,我的情绪便会莫名其妙地低落,无精打采的,以至于早早地闷睡。第二天,总忘不了转弯抹角地打听小丁昨晚的去处……
但不久,小丁小屋的灯光再也没有消失,哪怕是小丁一天、两天的出差,或者周末探家。记得一次我惊讶地问小丁:“小丁哥,你不在小屋怎么不关灯?多浪费电啊!”小丁望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有种说不出的柔情:“我想,我想还是开着好……”也说不出是为什么,我的心一荡,再也没说出第二句话。
后来,小丁开始光顾我的小屋,我们谈理想,谈生活,讲文学、历史,谈天、说地……
我们之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情感。
还记得那天晚上,小丁到我小屋闲聊,我开玩笑地说:“小丁哥,听说你有女朋友了,什么时候带来我看看?”他拿起我桌上的小圆镜神秘地一笑:“是啊,我这里还有她的相片,你要不要看一看?”我的脸孔发烧。我敏感地感到他在套用马克思向燕妮求婚的故事。我假装不懂,走到他身边:“好啊!在哪里?”他突然把圆镜对准了我,我一下子看到自己那张红得像朝霞的脸。我捂住脸大叫:“你好坏!”他不知怎么的就把我拉到他怀里,俯下身吻住了我的双唇。我感到一阵晕眩!这就是我的初吻?
第二天早上我很后悔,觉得自己变坏了、堕落了。我提笔仿写了一首小诗:
“吻
-
不曾相遇在开满玫瑰花的山坡
也不曾对天盟誓
-
当你灼热的嘴唇骤然压向我脸庞
两行珠泪悄然滑出我眼眶
抖动
如风雨中的小树”
在写《吻》的同时,我当即写了一首题为《结束》的诗。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开始,这不是起点,而是决然的结束!
小丁似乎没有发现我情感的变化。他还是喜欢到我小屋,他还是那么静静地看着我,他还是那么羞涩地笑着。
他对我却多了一份关心。
他为我借来大量文学读物,他对我写的文稿总是很认真地提出意见,他从家里给我捎来他们的地方特产……当整个大地一片洁白的时候,他送我一条粉红色的围巾。他说他很想看看我系着粉红色的围巾站在雪地里的模样,那一定很俏皮,很可爱。
在我放假离开广北农场时,小丁似真似假地说要娶我为妻。我吓了一跳:“结婚?我才十九岁啊!”他笑了:“你明年就达到结婚年龄了!”我调皮地说:“我到潍坊考虑一下。如果我决定回来就写信让你到车站接我,好吗?”
我走的前一天晚上,小丁有些伤感地送来一套崭新的我最喜欢的《红楼梦》。我打开封面,只见扉页上潇洒地题着我最喜欢的李清照的那首著名的词: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书中还夹了一张他的黑白单人照。
到潍坊后,我完全冷静下来:我并不爱小丁啊!而且,我一直在为那晚的冲动自责啊!也许,那只是两颗孤寂地心彼此温暖,不是吗?而且,我们的家乡相隔那么远,对我来说,我的年龄还那么小,我真的不敢对自己做出什么决定啊!
我当即给小丁写了一封信,里面只有一首诗:
“灯光,曾是最初的和谐
而今夜的灯光
在另一种形式下照耀你我
透过心的迷茫
仿佛有晶莹的露珠滚落我双颊
-
当一切已经不能再提起
当每一次回首
只是一种痛心的感觉
那么,永久的遗忘
是不是一种坦然的解脱呢
-
也许当我决定离开的时候
你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灯光,我的窗外没有灯光
小屋里的你
早已模糊成一片”
第六章 寻梦温州
更新时间2009…4…15 8:44:44 字数:8579
(一)
我独自在公路上漫步。一阵凉爽的风轻轻吹过,偶尔,来往的人群传来一、两声清脆的口哨。我的心情似乎有些平缓,可成串的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多少的委屈,多少的伤痛?
我仿佛又回到四年前的初三生活。哦,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啊!就着那盏昏黄的路灯,我看啊看,写啊写,说不清有多少次划破稿纸,也记不得有多少次咬断笔头!我真想一下子就能解开所有的几何题,我真想考试的时候,能有一个高分数,我多么想坦然地走向讲台,去领回我的试卷……
难道我在几何上真是一个零,是一片无法开垦的空白?象席慕蓉女士说的?可是,我连扣子也不会做吗?我的头脑里竟也缺乏这种“纽扣细胞”?
下午的情景又在我眼前浮现。
我多少带点殷勤地对小姐妹贵琴说:“姐姐,我的纽扣做好了,请帮我看看,好吗?”贵琴在厂里做纽扣好几年了,可以说是行家了。贵琴勉强笑了一下,接过筛子拨动里面的纽扣。她一边拨动,一边不停地说着,邻座的女孩不断地向我看。她们说的是温州话我不太懂,但我从她们异样的目光里知道我做的不好。一会儿,我听见她叫师姐与另外一个女孩的名字,不知说什么,似乎很大的怨言。果然,师姐说:“我也不知道她做的那么不好……”那个女孩也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你做的不好,会扣钱的。”“我……”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又急又愧,汗水一个劲地往下淌。正在这时,贵琴嘴里嘟囔着,把筛子重重地放在我桌上,埋头做起她自己的纽扣。师姐说:“她说一会儿再给你看,有好多要不得,老板会批评的。”我的泪珠滚落下来:“那怎么办?我抠下来,重新做,好吗?”“不知道。”师姐也开始忙起手中的活儿。
我呆呆地站着,手足无措。女伴们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师姐,那目光我懂,我怎能不懂呢?同样是四川来的乡下妹子,师姐心灵手巧,我却笨手笨脚。其实,我又有什么可以清高的,只不过会写几句诗而已,除此之外,一窍不通……
后来,我茫然地坐在凳子上,透过朦胧的泪眼看着纽扣上晶亮的缀子,看啊看啊,我也不知道要看出什么名堂来,痴痴呆呆的。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把废的纽扣找出来,用剪刀一个一个往下雕,机械地木然地活动着。没有人对我说什么,也没有关切的目光投射过来,我静静地雕着,没有目的,不知道结果。
大概是快要下班时,我听见师姐说:“贵琴,你帮她看一看吧,明天我帮你做。”于是,贵琴走了过来,从我桌子上拿过筛子:“真是的……”
-
一九九一年四月底,我来到温州和师姐在黎明东路一家纽扣厂上班。
我是怀着一种宁静的重新开始生活的心绪投入故乡的怀抱的。我告诉父母我不走了,就在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自学。我请求父亲给我买一台录音机,我要让父母有一天为我自豪!最初,父母也没有说什么,我也自然而然地随父母上山劳动。但不久,我就感到有些不对劲了。起初,只是乡邻别有深意地问:“菊花,你什么时候走?”“菊花,你不走了?听说你在外面干大事赚了很多钱呢!怎么还想回到这穷山沟?”后来,妈妈也开始唠叨了:“你真的不出去了?你不知道外面的人说得有多难听!她们说,你那么有出息最后还不是回到农村!以后我们还有脸见人吗?”我觉得妈妈这最后一句话才是最重要的,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又有谁知道我心中的苦?又有谁怜我的弱与孤?其实,我对于回家一直是恐惧的,我也从内心里知道我根本不适合这农村,这个家的。还记得出走后第一次返家,妈妈开口说的几句话:“我们才没有找你呢!你是不是拿了家里三十元钱?”“你千万别和别人乱说!我们都说你去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