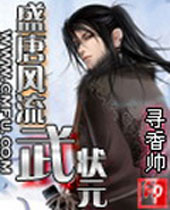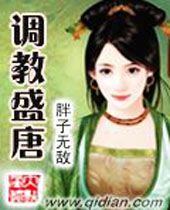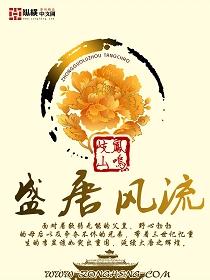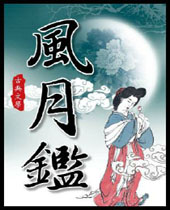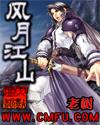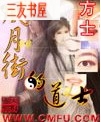盛唐风月-第25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在固安公主离开大半个月后;开明坊中一直籍籍无名的光明寺;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一度冲天;照得整个南城犹如白昼。坊中武侯闻讯前往帮忙灭火;可寺中除却不少无头苍蝇一般团团转的僧人之外;还有一个僧人对着一座起火的僧房哭天抢地;甚至一度抓着武侯大声嚷嚷;言道是抢出里头的东西便酬谢百贯。尽管那酬劳让人心动;可武侯们面对那样大的火势;谁敢冲进去?
当清晨宣阳坊万年县廨的差役前来查看那一片焦黑的残垣断壁时;那僧人仍旧逢人就哭诉自己的法事和法器全都陷在里头;那喋喋不休让所有人都不胜其烦。可这么一个谁都以为是穷疯了的和尚;却在所有人都不理他之后;仿佛是病急乱投医似的气急败坏抓着一个差役;厉声喝道∶“进去;进去帮我抢出秘药来;那是祁国公王驸马要的秘药”
第三百八十四章 黑暗之中的曙光
“你可听说了?祁国公王驸马人还没老呢;这就需要和尚炼秘药来助兴了”
“啧啧;可怜蔡国公主了蔡国公主听说贤良淑德得很;否则若是如当年那些个贵主也不知道要给祁国公戴多少绿帽子”
即使事情发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整整两个月了;但因为持续xing发酵和各式各样的流言蜚语;可就是清净如丽正书院;杜士仪都能听到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想也知道其他衙门是个什么光景。他对这么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也讶异得很;甚至利用了自己当初当过万年尉的便利;特地打听过;听说起火的原因是那四处嚷嚷的僧人炼药炼出了岔子;以至于丹房起火;他不禁暗自冷笑
不论王守一是不是请人炼制给自己吃的秘药;抑或是别处用的秘药;再次闹出这样的祸事;对于本来就已经麻烦缠身的这位王驸马来说;都是雪上加霜
“杜拾遗;太子殿下命人来问;今ri讲读时得问;汉之良吏;居官者或长子孙;孙、曹之世;善职者亦二三十载;皆敷政以尽民和;兴让以存简久。此句出自何处?”
见这内侍小心翼翼跑到自己背后;低声问的却是这种光明正大的学术问题;杜士仪不禁有些头疼。自从上次唯一一次讲读之后;他就再没有去过太极宫东宫;也再没有为太子李嗣谦充当过讲读官。
毕竟;丽正书院的主业是修书;如同贺知章徐坚这样的饱学文士;每个月也就轮一次;他这个八品左拾遗何至于还能够前去侍读?然而;李嗣谦却不知道怎的惦记上了他;更不知道怎的说动了这丽正修书院中供职的内侍省内侍;而请教的全都是些正儿八经的读书问题。其中最多的就是这种出自何处。他不用想也知道;很有可能是讲读官给太子殿下留的作业题。
他想了一想;想起上次说不知道的时候;李嗣谦次ri再问;再次ri又问;颇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劲头。此时此刻;即便他腹诽李嗣谦实在太不知道谨慎;却也不得不低声说道:“出自《宋书》;吉翰等人的列传;后文为;晚代风烈渐衰;非才有起伏;盖所遭之时异也。;”
听到这里;那显然不但识文断字;而且读过不少典籍的内侍立刻连连点头;不消一会儿便消失在了外头。这时候;贺知章方才捧了书卷在杜士仪身后立了;沉声问道:“又是太子殿下遣人问书于你?”
“悔不该当初在东宫讲读的那一次;太子殿下几次考较出典;我都答了;这下可好;几次三番派人直接问到丽正书院来了。”杜士仪苦笑摇头。
贺知章和徐坚都得杜士仪悄悄禀告过此事;可别的事可以想办法阻止;这种事贺知章却爱莫能助;总不成自己亲自去对太子说;不要再拿这些讲读官布置的课业来问杜士仪?于是;他心有戚戚然地拍了拍杜士仪的肩膀;正想安慰他两句;突然只见王翰溜了过来;却是用极其八卦的口气说道:“我刚从中书省来;张相国和崔侍郎吵了个不可开交听说是张相国认定的事;崔相国非要有异议;这下子真是针尖对麦芒闹开锅了”
张说在丽正书院中;固然大多数时候都温文尔雅仿佛典型儒雅文士;可在中书省中处置事务时;对于那些办事不力的下属;他却动辄大骂;有时候刻薄得让人无地自容;而对于同僚也是一样;他引见你的时候兴许还会让你受宠若惊;只觉得其人字字句句都如沐chun风;可要是他不待见你的时候;那是处处针锋相对让你别扭至极;恨不得自动求去。
而如今的中书侍郎崔沔;偏偏就不管自己位逊于张说;而且还是张说引荐的人;看不惯容不下的事就必要抗争;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而王翰这样看热闹的架势也不是第一次;就连贺知章也已经习惯了;此刻便打趣道:“怎么;子羽看那么多次热闹;还看不够?”
“我只是觉得崔侍郎实在是那个志气有嘉。”王翰挠了挠头;这才一摊手道;“十趟里头要输九趟;却还锲而不舍”
等到贺知章笑着一摊手便自顾自去继续编书了;王翰方才紧挨着杜士仪低声说道:“张相国身边一个令史悄悄对我透露说;张相国容不下崔侍郎。只要逮着机会;就会设法把人赶出中书省。”
杜士仪闻言却是眉头一挑:“那令史知道这个;自然是张相国的心腹;就算知道你是张相国颇为信赖看重的人;可竟然敢这么毫不避讳把话说给你听?他就不怕你王子羽万一醉酒泄给其他人?”
王翰倒没想这么多;此刻被杜士仪一提醒;他歪着头一思量;顿时悚然而惊。他是豪爽人;但并不意味着就真的一点心机都没有。而杜士仪则又接着说道:“若是你万一在哪酒醉失口说出这个消息;传到崔侍郎耳中时;这位中书侍郎说不定会借此发作;而后张相国只要左迁了你;反而可以摆出大公无私的样子;而崔侍郎反会因为小题大做失了圣心;要知道;他毕竟是张相国引荐的;谁人心眼小;圣人心里总会有一杆明秤。异ri再有机会;张相国再把你高高调回来也就行了。当然;这都是如果”
知道这种如果一个不好就会变成事实;王翰不禁长叹一声道:“唉;所以我不想留在京城便是如此纵使宅院甲于王侯;美姬环列左右;可却没有纵情享乐的机会;反而得时时刻刻谨小慎微经你这么一说;我从中书省听到的另一个消息也少了几分可信。听说;陛下对各地刺史的懈怠很不满意;而且天下一千余县;县令良莠不齐;圣人决定今冬好好遴选一批才于德行俱佳的刺史县令;以安四境民心;说得我都心动了。”
这个消息固然同样不知真假;但杜士仪却切切实实为之怦然心动。他不比青云直上一岁双迁;如今已经是从六品上侍御史;挂着勾当天下租庸地税使的宇文融;若要突兀地求为外官;只怕并不容易;可要是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他就可以立时三刻开始谋划了于是;他见四周其他人对于自己和王翰的窃窃私语已经司空见惯;没有一个人投来关切的一睹;他便拉着王翰低声说道:“今晚到我家里来;此事我们参谋参谋。”
“嗯?”王翰顿时大吃一惊;“这消息你倒相信?”
“这种事对于圣人来说;既可以安置官员;也可以把看不顺眼的打发出去;反倒不可能有假。正好我也想出去主政一方;你不是也想?”
“那好;晚上我到你那去”
这一天晚上;来的却不单单是一个王翰;还有韦礼。京兆韦氏九房;韦礼出自的是名臣辈出的郧公房;大名鼎鼎的韦安石便是他堂叔祖;如今他的伯父御史大夫韦抗因故出为蒲州刺史;父亲韦拯也即将万年令期满;可如今他的堂兄韦陟已经官居洛阳令;另一个堂兄韦斌亦是官居右拾遗;当年王维崔颢等人便是常常周游于那对韦家兄弟之门;可以说;尽管历经了韦氏之乱;但京兆韦氏树大根深;只损及一房;其余诸房并未动了根本。
于是;此刻韦礼一到就直截了当地说道:“杜十九郎;你知不知道;有人打算告你的刁状”
仿佛碍于王翰在场;他想了想便言简意赅地说道:“是太子殿下的事。”
他却没想到;自己话音刚落;王翰就把眼珠子瞪出来了:“不是;不过因为太子殿下派人到丽正书院;问过杜十九几句古文出典;这就有人小题大做了?贺学士徐学士他们全都知道;这简直是yu加之罪何患无辞”
“正如王六所说;幸好我禀告过上官;否则还真的是措手不及。”
杜士仪哂然一笑;并不觉得有多少意外。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继续说什么;就只听外间传来了秋娘的声音:“郎君;李十郎来了。”
所谓的李十郎;便是李林甫。宇文融这个飞黄腾达的大红人出京;杜士仪和李林甫的往来也并不算多;更不要说此人亲自找上了门来。他看了一眼王翰和韦礼;当即起身说道:“你们先少坐片刻;我去去就来。”
“杜十九郎;宫中有消息说;皇后殿下很有可能怀了身孕”
然而;等到杜士仪见到李林甫;他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便让他为之大吃一惊。李隆基和王皇后成婚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将近二十年这期间;李林甫别的妃妾给他生了儿子女儿一大堆;王皇后却一无所出。现在这些年还能用王皇后失宠来解释;可早先那些年伉俪情深自不必说;那会儿没有个一男半女;现如今王皇后都已经年近四旬圣宠全无的时候;却说有妊;这怎么可能
“含凉殿中的宫人如此透出的消息;据说王守一府上也突然毫无征兆地大肆摆宴。总之我给你报个信。”
尽管李林甫只是姜皎的外甥;此前也没连累到他;但他继舅舅姜皎之后和武惠妃搭上了线;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此事。此时此刻;他顿了一顿又似笑非笑地说道:“王守一此人睚眦必报;若皇后殿下真的终于有了喜讯;即便太子仍在;可嫡子名分非同小可;到时他自会重新得势。你得罪过他;小心为上。”
等到杜士仪别过了李林甫;重新回到书斋时;面对的便是两张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脸。王翰是好管闲事;而韦礼却是真的想知道李林甫特意走一趟是为了什么。然而;那等没有经过证实的宫闱秘闻;纵使面前这两位算得上是至交好友;可杜士仪也不打算抛出来耸人听闻;更何况他已经有所打算;因而此刻他便笑容可掬地说道:“英雄所见略同;刚刚李十郎来;正是为了王六今天透给我的那个消息。来来;韦十四郎你既然来了;我也告诉你听听。”
屋外夜sè渐深;群星璀璨;恰逢只有一丁点月牙的月初;一时更有如黑丝绒上点缀了无数珍珠一般。而屋子里的杜士仪和王翰韦礼说着话;心里却思量着;他一定要抽空去见一次杜思温了。
第三百八十五章 事发
李林甫告诉杜士仪的那个耸人听闻大消息还没得到证实,韦礼特地来告诉他,别人打算告他交连太子的刁状也还暂时没动静,即便没有王翰醉酒之后的大嘴巴,但张说对中书侍郎崔沔的反击却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胜局。
因为太行山以东各地从入chun之后,就遭遇了几十年一遇的大旱,即便官员祈雨等等亦不见起效,再加上各地州县官员良莠不齐,此前又一度括田括户,本就人心浮动的山东各地一时更显躁动,就连河南府一带也人心不安。因而,中书令张说便言辞恳切地上书天子,以历来重京官轻外官,名臣云集于京畿之内,而外官却往往选人太滥为由,奏请于考选上上、中上等优秀京官之中,遴选能员充实地方,以安民心,以顺天意。
而且仿佛是生怕源乾曜跳出来和自己打擂台,他还盛赞了当初源乾曜拜相之后,把自己的儿子们全都由京官派出去任地方官的高尚节cāo,又举了自己当初从相州、岳州、荆州到幽州并州等各地任刺史的经历,大有没当过地方官的阅历,就绝不足以为高官宰相的意思。
身为天子的李隆基本来就对天灾心烦,也有意从京官中剔除一部分不顺眼的放到外官任上,而张说所言之中有不少都合乎他的心意,因而,他便大笔一挥慨然允准。即便看到张说把与其不睦的中书侍郎崔沔和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也放到了出为刺史的行列中,他也连眼皮子都没眨一下。至少,张说主持政事堂这一年多来,与源乾曜一搭一档颇为默契,朝堂用人也称得上公允,排除一两个异己,还在他容忍之列
因而,当中书省按照圣意拟制书,在崔沔和韩休之外,就连新任黄门侍郎王丘以及另两位高官名臣都在出为刺史之列,上下一时为之哗然。这还不算,制书更令在京文武举荐或者自荐足堪为县令者,一时间候选者奔走相告,却是谁都不愿意去!即便县令之职最低也有七品,可那些偏远之地除却流外出身的杂职官,谁也不想去,即便山东并不偏远,可又哪里及得上长安附近这些京畿之县的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这雷声大,回应的雨点却寥寥的一片观望气氛之中。此前那仿佛只是虚惊一场的消息终于到了御前。正在梨园饶有兴致欣赏新派乐舞,甚至身前放着羯鼓,不时还按照节奏拍上一曲,甚至琢磨着是否要把宋瑕叫进宫来同乐的李隆基,当听到跪在身前的内侍禀告消息的时候,他的脸上一下子严霜密布。他几乎想都不想便把羯鼓往身边重重一搁,随即怒斥道:“为何不早报?”
“小人本以为,太子殿下乐于读书是好事”那内侍耷拉着脑袋,双膝肩头都在微微颤抖,仿佛真的是惶恐到了极点,“谁知道今天太子殿下便命小人去问杜拾遗,借之前刘太史撰的《史通》。小人去过丽正书院之后,实在是觉得不妥,故而方才来禀告陛下。”
在李隆基看来,自己是最酷肖太宗李世民的。尽管没有李世民当初征战天下的战功,但他在唐隆政变中平了韦后之乱,而后又铲除了太平公主,逼了退位的父亲睿宗再不管国事。所以,他这个通过政变起家,同样是最初在名分上不占优势的天子,最最忌惮的就是东宫结党。故而他在册立李嗣谦,这个太子又渐渐长大之后,他对其的防范竟是非同一般的严密,甚至于在选妃上头也至今迟疑未决。
“很好,你们都很好!太子如此妄为,竟然不禀告于朕!”
李隆基脱手掷出了手中的黄檀杖,眼看着那坚硬的木杖滚出了老远,他方才霍然站起身,余怒未消地说:“回紫宸殿!”
那内侍最初禀告的时候,因李隆基并未言语,台下梨园众人并未退避,尽管此人声音不大,可最终李隆基那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