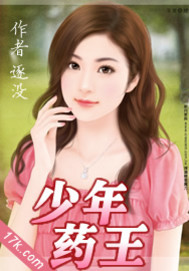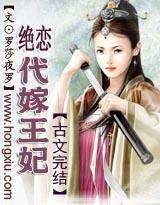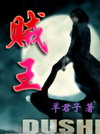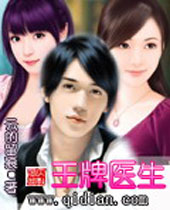春秋我为王-第59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洙泗的春风下,赵无恤意气风发,他指着前方的城池里聚说道:“天下的重新安定,将从邾国开始,虽然难免会流血漂橹,但还请先生,为我见证这一切!”
“孙武拭目以待!”
孙武现在已经不觉得铁甲不合身了,在这里,他见识了新的装备,接触到一位年轻君主的勃勃野心,同时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擦亮眼睛,好好看着这一切发生,这就是他能做的事情,也不知自己有生之年,能否看到结局呢?
他忐忑,忐忑新时代到来后,他熟悉的一切都将面目全非。他期待,期待陌生的挑战,期待看到新鲜的事物。
孙子那颗已经寂灭的雄心,再度开始兴奋地跳动,他的兵法,急需更新换代……
第929章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PS:之前有错误,邾国北部屏障不是梁父,是绎山。
虽然赵无恤做好了“流血漂橹”的准备,不过很遗憾,此番赵氏四路伐邾,遇到的抵抗却微乎其微。
赵无恤的主力万余人越过亢父,直插邾国,弱小的邾人本来就内部不和,岂敢与强大的赵军野战?纷纷缩回城邑,坐视赵军长驱直入。
就算有零星的战斗,也发生在前锋的位置,等孙武和赵无恤抵达时,看到只是一片被冲得七零八落的车马,以及蹲地投降的兵卒。
不单西路主力如此,除了受阻于北部绎山的赵广德部外,其余冉求、宋军的东南两部都顺利开进,预计很快就可以和赵无恤会师于邾国都城。
对此,孙武评价道:“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赵氏通过伐谋、伐交,将邾国孤立于泗上,已经奠定了胜利,这是好事。”
话虽如此,但孙武也为没有看到赵军战斗的方式意兴阑珊,跟赵无恤呆在中军,这次旁观就会这么平淡无奇地渡过,于是他索性请求,让他跟着前锋一起行动。
赵无恤同意了,给了孙武一辆车,两名甲士保护他安全,孙武跟在田贲的前锋部队后行进,他发现赵军前锋多为新兵,但他们的训练都不错,在老兵的率领下小心翼翼地扫清前敌。
十年前,赵无恤拥有了数千中坚老卒,这些人不断提拔,如今最差也是一个卒长。就这样,一人教十人,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万人!赵氏的军队数量扩张了十倍,二十倍,当年的经验被不断复制。
对这种练兵之法,孙武是持肯定态度的,可惜吴国穷兵黩武,二十年间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以至于老兵死伤殆尽。所以现在吴王夫差虽然号称吴国甲士“亿有三千”,和赵氏明面上的兵力差不多,但能拉到战场上的只有一半,而且良莠不全。
同时,他也注意到,赵氏的兵种组成和诸侯不大相同,车兵很少,只作为指挥车乘使用,对敌阵进行冲击的任务,主要由装备厚甲的武卒承担,这一点,倒是和吴军类似。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战车冲陷于阵,根本不是人力能当的。晋国所以称霸中原,就在于晋国多马,而马匹可以装备大量战车。但问题在于,战车一来太贵,保养战车就是一笔巨大的钱财,而战马的损耗也是非常惊人的,南方的吴国根本没有那么多马。
更要命的是,战车上士兵的训练也是积年累月还不见成效,换句话说,一个合格的御手,没有十年,不能成战,所以车上的甲士多为贵族子弟。
再加上战车需要在很平坦的地域才能投入战场,正所谓战车有“十死之地”,这限制了战车的发挥,在战争地域越来越广阔复杂的情况下,造成了战车慢慢不适应征战。但诸侯按照惯性,依然大量装备,最初还是孙武果断削减吴国的车兵,统统换成步卒。
于是吴甲一出天下震动,大败楚军,五战及郢,就是因为步卒方阵不受条件约束,可以实现一些前人想都想不到的战略大迂回和战术进攻。
无独有偶,在孙武练兵十年后,赵氏也果断用骑兵和步卒取代了车阵。赵氏轻骑屡建奇功,因为他们的机动力灵活性远超战车。而赵武卒方阵不亚于吴军,更有兵刃之利,假以时日装备上铁甲,就更加所向睥睨了。
现如今,中原争霸,已经到了要靠步骑分出胜负的时候了。从秦魏河西之战便可以看出端倪来,秦国,已经开始效仿赵氏的骑兵,而魏氏,则效仿赵氏的步卒进行改革,南方的楚国也在改革,经历柏举之战的惨败后,叶公的宛地精卒,开始以步卒为核心,毕竟他父亲沈尹戎曾在吴国为臣,偷学过孙武的招数。
孙武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里,毁车为步骑的军事改革将成为一股潮流。诸侯若不想早早灭亡,就不得不进行改变,学会以赵氏之战法对抗赵师。
赵氏的兵种和装备,诸侯卿大夫或许能学到皮毛,但有一些东西,可不是想效仿就能效仿的。
此番赵军伐邾,纵然孙武跑到前锋,但还是连一场像样的硬仗都没看到,没法对赵军战术进行全方位分析的他,只能在车上琢磨起赵无恤的战略来。
“赵氏用兵,在鲁时好用奇,拘泥于兵势的出奇制胜(战术);入晋后则好用正,以阳谋逼迫敌人决战,再以兵甲之利和强大气势战胜。”
这是孙武在吴国时,对伍子胥总结的赵军作战特点,来到赵军里观察思考后,他差不多明白了,前者是弱者击败强敌的无奈之举,后者,则是强者稳操胜券的持重之法。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在战略上,不能一味的防守,也不能一味的进攻,这一点赵氏就做的很好,每年农忙时绝不轻启战端,专心种田,发展生产,储存粮食。等到时机成熟,就迅速确定目标,无论是灭代、取齐河间,伐秦河西,都是一蹴而就,争取一到三个月的农闲结束战争,然后继续种田,等待来年的战机。这样,既保全了自己,又能获得局部的胜利,对邻国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大。
在孙武的兵法里,总结了国战的五项原则:一是度,二是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
度产生于土地的广狭;土地幅员广阔与否决定物资的多少;军赋的多寡决定兵员的数量;兵员的数量决定部队的战斗力;部队的战斗力决定胜负的优劣。
总之,要明修政治,确保法度,才能由内而外,主宰战争胜负的命运。
所以胜利之师如同以镒对铢,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攻击弱小的敌人,其气势就像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般不可阻挡,这就是军争中至关重要的“形”。
在孙武看来,赵无恤,可谓是用“形”的高手了。
他有些无奈地叹息道:“我向吴王传授兵法,他却只学了小道,不懂大势,更不懂何为战争的本质;赵卿虽然打仗作风生硬,近年来更是只知道以巧技和强兵压制敌人,但他在形势方面的造诣,很深啊……”
北上之前,孙武还觉得赵吴相遇不知孰胜孰负,现在,他只觉得吴军只怕是拼不过赵氏的,纵然能侥幸嬴一两次小仗,但最终会被赵氏深厚的国力拖死。
善于作战的人,总是战胜容易战胜的敌人,他们既没有卓越过人的智慧,也没有勇武显赫的名声,战争的胜利不会有差错,之所以不会出现差错,是因为他们作战的措施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上!
这就是所谓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了。
所以就连面对邾国这样的弱敌,赵氏依旧稳扎稳打,丝毫不冒进。邾国的失败进入倒计时,若是他们纵深广阔,或许还能多撑一段时间,可惜邾国与鲁国“击拆之声相闻”,大小不过两县之地,毫无纵深可言。不过六七日间,赵军便在沿途城邑或降或闭门自守的情况下,与东、南北三路偏师会师于邾国都城下。
将近三万大军云集,足以将邾都绎阳包围得水泄不通,而此时的邾国,已是一副亡国之景,非但投降引赵军前来的大夫络绎不绝,连公子公孙都纷纷逃离这棵要倒的大树,跑到赵氏羽翼下卑躬屈膝,希望能在邾子被废黜后,成为新的国君。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赵军已攻至郭门,邾子曹益却仍然在享用乐舞,在城外甚至能听到舞乐的声音,赵氏众将纷纷摇头,觉得这邾国真是没救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历史上,也是差不多的时段,鲁国三桓伐邾,邾子也是这副德行,结果被三桓俘虏。
孙武纵观邾城,发现其北枕绎山,南依廓山,地势开阔,南北高中部低,平面近似长方形。东西横距三里,南北纵距三里米,城周长约十余里。构筑利用山间高地,墙高两到三丈不等,墙基宽十丈,也算一处坚城。
不过“攻城为下”的理论对赵军无效,拔城无数的赵军并未将小小邾城放在眼里,他们开始架设攻城器械,准备过几天便发动总攻。
引赵军入邾的那位邾国大夫见赵军迟迟不攻城,有些忧心,便向赵无恤禀报道:“邾子已派遣使节向齐、吴求援,再拖下去,只怕两国合力救邾,南北来攻……”
第930章 邹鲁
“数年前赵氏与齐国汶水一战,邾子便蠢蠢欲动,想要配合齐人进攻鲁国,被吾等劝阻乃止。这之后,邾子与齐国陈、鲍,还有吴国一直暗中往来,上卿攻邾时,邾子也派人去吴国求援……”
叛邾的大夫一口一个邾子,浑然没把他当做国君,赵无恤听了以后,笑道:“齐国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河间郡羊舌戎,汶阳柳下跖,还有莒国的国、高流亡之士,都死死盯着齐国呢,陈氏才在河间打了败仗,不会为了邾国而再度与赵氏开战,至于吴国……”
赵无恤转而问坐在一旁的孙武:“武子认为,齐国和吴国会为邾国出兵么?”
孙武眉头一皱,暗道怎么问起了自己,但这些天里赵无恤任他出入赵军内外,甚至还将秘密武器弩砲让孙武一观究竟,一点不藏私,这时候孙武要是推脱不答,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他只好说道:“鲁国敲打梆子的声音,在邾国都可以听到,吴国却相距二千里,就算吴师北来,没有三个月到不了,哪里能管得了邾国的事?”
吴国的斤两,孙武再清楚不过了,淮北和徐地那数万吴军主要针对鲁国方向,与赵氏一直井水不犯河水。夫差虽然狂妄自大,对霸业情有独钟,但他却不糊涂,在彻底夺取陈蔡,解除楚国的侧翼威胁之前,他是不会贸然北上洙泗的。
但以现在吴国对楚国的优势和与齐国的眉来眼去看,未来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赵无恤急着解决邾国,也是为了提前除去一个隐患吧。
更多的事情,比如吴军的部署等,孙武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不会才离开就急不可耐地把吴国的一切都卖给赵无恤。
赵无恤也不强求,在确认齐、吴都没能力援邾之后,他们有条不紊地围三缺一。不过还不等大砲架好,城内就有受不住压力的大夫打开了城门,引赵军入内了……
原来,邾子也知道指望齐、吴来救援只是妄想,于是他整日醉生梦死,希望借此忘掉现实。喝醉时还抽剑追杀自己的夫人、公子,于是邾宫竖寺、女婢散尽,宫卫也各奔东西。国君都这样,卿大夫谁还有为国守社稷的心?不多时便纷纷开门投降,等邾子从宿醉中醒来,赵无恤已经带着甲兵来到他的面前。
……
邾国的大殿上一片狼藉,邾子瘫倒在装饰金玉的君榻上,胡子拉碴,眼角沾满眼屎,手里还握着带有残酒的爵,他是被密集的脚步声惊醒的,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夫人?”
深宫寂寥,无人回答。
“宫卫?”
回音阵阵,无人响应。
他抬起头,正好看到一队赵卒鱼贯而入,他们明火执仗,穿的鞋上还带着泥巴,好奇地看着高大的宫殿,有的人甚至伸手去触碰那些精美的礼器。
“贼子!”
邾子一个机灵,拿起了身边的剑。
“滚出去!”他嘶声道,踉跄地爬起来,持剑在头上挥舞,想要阻止他们靠近。
所有人都浑然没把他当回事,有人嘻嘻一乐,田贲更是扯开嗓门哈哈大笑。接着一声吆喝响起,众人连忙止住了笑,挺起了胸脯,放下手里的东西,在原本邾国大夫们的位置上站成两列。
从他们中间走进来的,是一位将领,披着华丽的铁甲,玄色的大氅拖在地板上,俨然是一位高贵的卿士。
“窃寡人国的大盗,来了么?”
邾子依然处于不清醒的状态,他竟主动朝那人步步进逼,胡乱挥舞宝剑,仿佛要在乱军中杀出重围。然而却被田贲轻松下了武器,在他后脑勺上轻轻一击,像老鹰擒获一只小鸡般,将他按在了地上。
一抬头,赵无恤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
札甲粼粼,随着脚步轻声作响,他的卫士尾随在后,仿如两个影子。
赵无恤面无表情地看着邾子的丑态,在他黑如玛瑙的眼瞳里,没有丝毫怜悯。
他轻启唇舌,说道:
“曹益,你可知罪?”
……
“以晋国执政之位,问罪小国君主,并非没有先例。”
子夏,这个阴差阳错没有投入孔门的年轻人在临漳学宫里呆了三年,他涉猎十分广泛,除了占卜、天文之外,对律法也有些心得。虽然暂时无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但跟在赵无恤身边保管档案卷宗,以备咨询是没问题的。
距离邾子被擒获已经过去几天了,齐国和吴国果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齐国是不敢,吴国是来不及。于是如何处置邾国的会议,便在原先的邾宫殿堂召开。
子夏翻着手里的竹简,说道:“例如七十年前,诸侯盟于祝柯,晋卿在盟会上抓捕了邾悼公,理由是邾国助齐伐鲁,于是便划出邾国的部分将于,归于鲁国。”
“然,应当效仿故事,割邾肥鲁。”既然有先例,鲁国出身的群臣顿时兴奋了,纷纷提议宰割邾国,宰予更是站起来向赵无恤疾呼道:“莫不如灭邾国社稷,将邾地完全并入鲁国!”
赵无恤摆了摆手,让众人肃静,随后说道:“先让理官定下邾子的罪名。”
赵氏的律法,不但通行于晋国、鲁国、卫国,更要求泗上诸侯遵从,若是有跨国的案件,就要移交赵氏审理,卿大夫、国君也不例外。
邾子曹益本来就是个昏君,历史上不但被三桓俘虏过,还被立他为傀儡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同时嫌弃,将他废黜两次。他的罪名很好找,随便就能凑出一大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