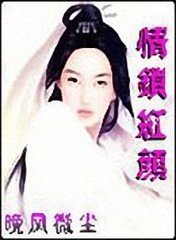漂泊红颜-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想到她竟会在那样快的瞬间就看清并记住了她的牌。
她用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准确的报出发牌小姐的牌。
“她有一对8”
“两个K。”
“傻牌。”
“她是四喜,赶紧撤!”
赌了一阵儿,更换发牌小姐了,四个人一轰而散,跑到赌场附设的酒吧喝酒去了。
发牌小姐看着空空的赌台发愣。
我问她们为什么不继续赌?她们说不行,就那一个发牌小姐发牌发得高,其余的都很低,看不到的。
我知道了她们的名字:要我让出位子的叫吴春英,27岁,是她们的大姐。能偷看牌的小个子叫叶兰,21岁,是小妹。稍胖一点的叫罗丽华,25岁。最漂亮的叫沈香妹,也是25岁。也许是年龄小的缘故,叶兰最活泼,闹得厉害。吴春英则显得稍微有点城府,也安静些。罗丽华好像略有心计,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沈香妹普通话讲得最好,但常常讲出让你吓一跳的字眼。
我把她们称为青田小分队。
她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番号。
有一天夜里,我和小分队全体战士在卡西诺战斗到12点,颇有斩获。这时又换发牌小姐了,几个小姐妹叽叽咕咕说了一顿,然后由吴春英对我说:“咱们一块儿去蹦迪吧?步行街新开了一家迪斯科舞厅,火极了。”
我想了想,说走吧。她们不在我非输不可,守住胜利果实算了。
叶兰说声:“撤!”随手扔给发牌小姐两个一百克郎的筹码做小费,一阵风似的走了。
这家迪斯科舞厅面积不小,人满满的,各种肤色都有,以欧洲人居多。音乐震耳欲聋,激光打得人眼花缭乱。她们都冲进舞池了,我在吧台上坐下,要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冰,慢慢啜着看景儿。
站在高台上领舞的是三个捷克女孩儿,身材美极了。长长的腿,细细的腰,丰满的臀部,高耸的乳峰。她们沉醉于疯狂的音乐之中,上身已经没有任何衣物,毫无束缚的乳房随着音乐激烈摇晃。下身穿着露了半个屁股的牛仔短裤,腾挪旋转,扭腰出胯,狂歌劲舞。
我在人群中搜索小分队的身影,但找不到。她们个子太小了,被牛高马大的欧洲人遮蔽得严严实实。
突然,叶兰不知道从哪里跑了过来,把一个药片塞进嘴里,又端起我的威士忌送下,然后就要拉我进舞池。我摇摇头,指指酒杯——说话听不见,音乐声太大。
她一笑,扭头又冲进了舞池。
我继续喝酒。
忽然,舞着的人们齐声喝起彩来,并且自动往后退,在舞池中心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我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便在高高的吧台凳上伸长脖子。
我看到小分队全体战士正在那里疯狂摇摆,特别是那个叶兰,不光身子摇摆,头也在摇摆,既疯狂又有节奏,仿佛进入了一种机械状态。而且,她一边摇头一边缓缓地脱掉上衣,手里高高地举着黑色蕾丝胸罩,两只小小的乳房在耀眼的激光下显得惨白和瘦弱。但欧洲人喜欢,他们已经看烦了山丘般的豪乳,这两只美丽的中国乳房在他们眼中如珍品一样妙不可言。
舞客们更加疯狂起来。
那时我还不知道她们的身世,只知道她们全是浙江省的农民。看着她们热舞,我不禁想:她们的父母,那些一辈子辛苦劳作的农民兄弟,怕是做梦也不会梦到自己的女儿在异国他乡竟如此疯狂吧?
这不是色情场所,但确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所在。
第二十八章 今宵酒醒何处
赌场其实是一个安静雅致的地方,不仅对赌客的衣着有严格的要求,如男士穿牛仔裤、夹克衫、旅游鞋,女士穿拖鞋一律不准入内之外,与欧洲其他公共场所一样,也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喧哗吵闹。发牌小姐甜甜的微笑和悦耳的低低的音乐陪伴着你,甚至在香气扑鼻的卫生间里,音乐依然悠扬。
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与他们在其他公共场所也一样:喧哗吵闹是永远的特色。要是在其他场合早就会遭到制止了,但赌场老板太喜欢中国人了,只能听之任之,网开一面。
有一次,四个小姐并肩坐在赌台上,手里拿着各式精美的家乡特产小吃,叽叽喳喳地一边说笑一边赌。是个看不到牌的小姐在发牌,发牌完毕,大家慢慢捻开手中的牌,用家乡话报出自己有些什么,然后分析发牌小姐手中可能会有什么牌。
突然,小个子叶兰一下站了起来,把牌往赌台上一扣,激动地说:“我是同花顺!我是同花顺!”
大家紧张地看着发牌小姐一张一张把自己的牌翻开,竟是一副傻牌!
四个小姐一齐指着发牌小姐的鼻子大呼小叫,显然是在用家乡话骂她。发牌小姐一边笑一边连声说:“lmasory,lmasory。”叶兰更是生气,她使劲儿一拍赌台,突然尖叫一声弯腰钻进了赌台下面,口里哇哇地不知嚷些啥。把个圆圆的小屁股撅得高高的,超短裙根本什么也遮不住。
罗丽华和沈香妹也钻进了赌台下面。
我问吴春英她怎么了?吴春英一边拽叶兰的裙子为她遮蔽屁股,一边笑着对我说:“一拍桌子把钻戒上的钻石给震掉了,有好几克拉呢!”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发牌小姐以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而赶来的老板,还有围着观看的各国赌客们。
大家一起哄堂大笑。
老板告诉我,这是卡西诺自开张以来最喧闹的一次。
看着她们在卡西诺颐指气使,大呼小叫,我不禁想到我的那些朋友,像汪虹,像吴霞,像侯玉花,还有辛佩瑶、黄文玉,她们显然比这些小分队队员层次高得多——小分队队员全部生活在农村,而她们却生活在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全世界都知道的大都市;小分队队员的父母全部是农民,而她们的父母却是教授、高级工程师、军官和领导干部;小分队队员出国前全部没有职业,而她们却是法官、教师、公务员,黄文玉的职业差一点,但也是上海的工人;然而在国外,她们必须日夜辛劳,来赚钱养活自己,从来都不知道卡西诺门朝哪边开。
而这些女农民呢?
心里有一些很复杂的感觉。
以后跟她们愈来愈熟悉了,便渐渐知道了她们的故事。
吴春英是正儿巴经的农民,没上过一天学。在青田那个地方,一对夫妇生四五个孩子是家常便饭。儿子才有上学的可能,女儿迟早是人家的人,上学有什么用?她至今只能认识并书写自己的名字,是一个标准的文盲。但她并没有感到有任何不便,“会写字又能干什么?”她曾这样问我。“比如你,每天也不过是东奔西走的劳碌。我在布拉格认识好多有文化的人,他们都要穷死了!”
我无地自容,感到会写字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她聪明,人也漂亮。不会写字不是她的错,甚至也不是她父母的错——她家里太穷了,八个孩子她是老大。超生罚款已经罚得父母债务如山,可他们还准备继续生下去,因为八个都是女儿。父母都是信念很强的人,不信邪,不想被村民叽笑,决心把儿子进行到底。吴春英四岁就下田插秧,割猪草、砍柴禾、做饭、哄妹妹,什么都会干,什么都得干。
她真干活儿干怕了。
青田是个穷地方,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土地既然养不活他们,他们自然就要离开土地。青田人爱往外跑,而且一跑就跑得很远,而且跑得方式只有一个:偷渡。话又说回来,不偷渡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说地方公安局对这些农民兄弟领取护照管得非常严,即便你拿到护照,邀请书和经济担保都符合要求,世界各国大使馆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们拒签的。
她跑到了布拉格。这只是一个中转站,她的终点是意大利。
她跑不动了,于是在布拉格与一个蛇头同居。
蛇头姓黄,是她的同乡,蛇头的村子离她的村子只有六里路。蛇头黄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在家里,为他抚养儿女伺候父母。他在西班牙有一个小老婆,在荷兰有一个小老婆,如今在布拉格又有了一个。
他很有钱,因此她很知足。
出国以前她最远的地方去过郦水县城,郦水是青田的邻县,却比青田繁荣。在山沟里的青田人看来,简直就是天堂。青田人并不贪婪,我后来问过许多偷渡出来的青田人:你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多数人回答说:在郦水县城买一套房子。我曾经去过郦水,县里的官员指着一大片很漂亮的楼房对我说:“都是青田人买的。”
青田偷渡客拉动了郦水县的经济发展。
吴春英的愿望也是如此。
蛇头黄很懂得他这些乡亲的想法,很轻易地便满足了他新纳小妾的宏伟心愿。吴春英感激涕零,除了更好地服侍蛇头黄的饮食起居外,只能在床上变着法儿地为他服务。
蛇头黄偷渡人蛇的目的地在西欧各国,但大本营却在捷克。这是捷克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地处欧洲最中部,与德国——偷渡客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有着漫长而又疏于管理的边境;与奥地利也有着同样漫长也同样疏于管理的边境。虽然大多数偷渡客并不喜欢这个美丽的山国,但奥地利与意大利——偷渡客心目中的天堂——有着不但漫长而且形同虚设的边境。
蛇头黄在这里指挥着手下带领一群又一群人蛇翻过厄尔士山和波希米亚林山,大举进入德国和奥地利。进入德国的便藏起来打黑工,进入奥地利的则还需继续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妙不可言的意大利。
但偷渡的费用必须在布拉格支付。
吴春英忠厚老实,吃苦耐劳,而且不贪小便宜。她渐渐取得了蛇头黄的信任,当起了财务总管。
半年后,蛇头黄在去德国的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经过多方抢救,命是保住了,人却变成了植物。
吴春英托人把这株植物小心翼翼地带回家乡,交到大老婆手里。
所有的钱都归了她。
她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但莎士比亚剧中所描写的黄金使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故事,在她身上又上演了。
她一下子变了一个人。
她的温顺贤惠不见了,她的忠厚老实不见了,她的吃苦耐劳也不见了。替代它们的是尖刻、狡黠、懒惰。大老婆打来电话想要点钱,诉苦说只能给他天天喝粥。吴春英一顿臭骂,说哪怕你天天给他喝尿呢!钱是他的?钱是他的你让他来取好了!
她不想去做生意——苦还没受够吗?她也不愿意嫁人——哪个不是奔着她的钱来?
她开始试着做蛇头黄做过的生意,毕竟耳濡目染,所有套路都一清二楚。虽然是在刀尖儿上求利,但这利是暴利呀!偶尔不去卡西诺的夜晚,她有时也会想起自己在家乡的生活:小小年纪便下田插秧,竟被可恶的蚂蟥咬住了阴部;领着、背着、抱着妹妹们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往家跑,摔倒在泥泞中,额头碰破了,雨水中掺杂着鲜血;一直到出国之前,从没有用过卫生巾。每个月的那几天里,只拿些破布条破棉絮对付,自己都能闻到恶臭。叶兰曾对我叽笑她这位阔绰的大姐:别人集邮集币集IC卡,她可好,专集卫生巾,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都买。而且,“不管那个来不来,都垫着。”叶兰嘻嘻笑着说。
罗丽华在家乡也是农民,但是和吴春英不同,家里不但不穷,还颇有些小富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哥哥在德国黑着,弟弟在法国黑着,父亲在家里还开着一个专做假冒商品的小作坊。打黑工虽然钱少,但和青田当地收入相比,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做假冒商品虽然有风险,但只要打点好了方方面面,还是有钱赚的。她读过小学,成绩不好也不坏。哥哥弟弟共同出钱把她办出来,目的地也是西欧。但这一阵子边境查得比较紧,只好先在布拉格安顿下来。也不用打工,哥哥弟弟每月分别寄些马克法郎来,日子过得蛮写意。闲来无事,听说卡西诺是如何如何的刺激,便随小姐妹们前往开眼。这一开眼就迷住了。开始只是在一边儿看,尔后牛刀小试,不料竟颇有斩获,便开始大赌起来。她有许多关于赌博的格言,像“有赌不算输”,像“小赌养家糊口,大赌创业发财”,讲起来振振有词,一套一套的。而且她认真研究,细心琢磨,有空儿则沙盘演练,力求找到规律,克敌制胜。西欧是不肯去了,去了至少要刷碗,哪有这里安逸?可是又不能逢赌必赢,尤其是叶兰的灵眼被卡西诺发现以后,十赌至少输七回。日子长了,就感到钱不够用。于是便骗哥哥弟弟说要在这边做生意,请他们多寄些钱来启动。哥哥弟弟信以为真,寄了不少钱来,但都被卡西诺给启动走了。慢慢地,哥哥弟弟听到了传言,一分钱也不寄了。她收不了手,便与一位也是在卡西诺相识的荷兰籍同乡“傍”上了。此人是贩卖毒品的,荷兰对毒品的管制相当松,他便从那边弄到带来布拉格卖,隔两个月来一次。还算仁慈,不叫罗丽华卖白粉,只给她一些摇头丸、迷幻药之类的软性毒品卖。生意时好时坏,但就是有座金山也不够她在卡西诺豪赌。有一回我见她就在赌台边给父亲打电话,虽然听不懂说什么,但看那严肃又恳切的表情便知道在商量大事。叶兰悄悄告诉我:她是在骗老爸的钱,说有一笔好生意急需十万美金。
关掉电话,看她一副轻松的样子,事情肯定是成了。我看着她笑,说:“好大的生意。”
她也笑了,说:“调钱出来用嘛,有什么关系?再说老爸要钱做什么?不是修坟就是包二奶。”
也对。
叶兰是穷人家的孩子。母亲病死了,父亲整天抱着酒瓶子不撒手。家徒四壁,叶兰还有两个弟弟,统统饿得脖子像鹅。适逢蛇头到村子里带人,集合起二三十人的队伍要上路。她跑去了,对蛇头说她也想走。蛇头说好呀,先拿一万美金来。
她说没有,脸红红的。
蛇头笑了,仁慈地捏捏她发育得不好的小乳房,打个榧子,说:
“出发。”
一路陪蛇头睡,从上海睡到迪拜,又从迪拜睡到布拉格。
蛇头又回国带人去了,她便在一个同乡开的中餐馆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