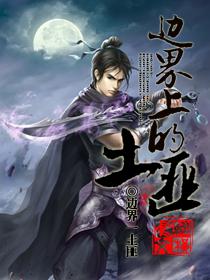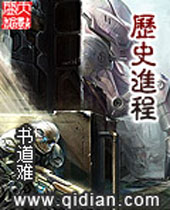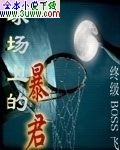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流血牺牲)的办法来挫败德国,意志坚强的指挥官是不会退缩的。
1914年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各国都已知道,军事效率并不决定于一些小股专业兵力的效率,而在于人力同合乎战略的铁路网的恰当组合。在这两方面都占优势的任何国家,即使其他方面都同别国一样,准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欧洲的政治地图。因此,人力的有效运用与人们的福利,便成为国家所关心的大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率本身就是军事力量的指标。法国见到1870年后本国出生率下降而宿敌德国的出生率却在直线上升,深感不安。兵员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联合王国在对俄战争前,在征召入伍的兵员中发现体格不合格者占有惊人比例,从而不得不改善其社会政策。还有基本的教育水准。现代化的军队现己成为复杂的组织,要求即使是等级最低的士兵也要有文化,会计算。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军土们有文化比军官们有文化更重要。而一般的说法则是:普鲁士的教师们赢得了普法战争。这一说法同公众对威灵顿的说法大同小异,说滑铁卢一役的取胜,是在伊顿公学伦敦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的操场上就决定了的。
不是说,贵族阶级的传统品质——勇敢、主动、独立、有领导能力——在战场上不那么需要了;高级军官笼统说说意图,交给低级军官去办就可以了。战争需要大量优秀军官。单凭贵族头衔是得不到优秀品质的,尽管本世纪下半叶土地价格暴跌,使有地阶级以新的兴趣把军事职业看作是拯救经济的源泉。即使贵族阶级还可以继续贡献出他们传统的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才能,对职业士兵也要求有更好的品质:懂得技术,其中有些人还须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正规军军官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精神:继续作为英勇的领导人,还要求成为经理人、工程师。
军官类型的转变,在法国实现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因为革命后,军官团中的大多数已是中产阶级。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阶级总是随机应变的、折衷主义的。俄国的贵族想在军队里找差使是决无问题的;但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过干部训练学校训练的中产阶级与中间偏下阶级的子弟所领导的。德国就远不是那么好改了。德国军官团同王室有特别亲密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家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到了本世纪中叶的多事之秋,普鲁士军官团认识到自己不仅在为皇家抵御外敌,而且还在为皇家镇压国内的分裂势力。尽管他们承认总参谋部逼迫他们扩军是军事上的必需,然而,军队领导人怀着理解的心情也已看出这种趋势:有自由思想背景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大有来取代他们之势,各级军士们则都将是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
他们无需担心。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中产阶级极端分子带着文化方面的与政治方面的“起义时代发酵粉”,在1848年当然是革命的,进入50年代后也仍然处于爱找麻烦的位置。俾斯麦则力促普鲁士王室宣扬爱国(爱德国)主义,用这个办法来拔掉那些极端分子的“刺”,到了1871年,这些人便高喊起“皇帝万岁”来,喊得比任何人更响亮。此后,德国资产阶级便支持武装力量,同他们关系融洽,因自己能从预备役军官委员会脱身而高兴。但是,资产阶级同军队一样,对工业无产阶级中逐渐增长的社会主义意识感到害怕,尤其是军事当局更感忧虑。鲁尔、莱茵兰等地的新兴工业大城市中的工人素无对封建领主效忠的传统,这种状况同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情况大不一样,那里大部分土地仍归地主贵族所有。而恰恰是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快,征召入伍的兵士也最多,这些人的可靠程度如何?先不说打法国人,就说让他们去压制德国上层阶级日益畏惧的革命,以“保卫社会秩序”,他们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吗?普鲁士军官团所惧怕的,正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希望的。从军事来说,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学生与精明的评论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使他成为19世纪最出色的军事评论家,他们两人都显示出对军事技术有详尽的研究,并对军事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这一概念是英国与法国的自由主义分子从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一词,系指18世纪欧洲思潮的主流。17世纪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科学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18世纪后,更多的人们相信了自然规律与宇宙法则,思维更为理智。继承下来,但在英国根子更深,可追溯到那些不奉国教的教派的主张,经过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赖特等有识之士发扬阐述,获得较大的政治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不赞同19世纪30年代浪漫革命派的观点,那些人相信由社会精英发动的起义便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军事力量始终是变革人类活动的工具,今后也将如此,但是这种变革必须符合某些客观规律。革命需要等待时机。职业士兵(迄今为止仍是旧社会统治者手中用来镇压人民的可靠工具)被经过训练、掌握了军事技术的人民群众所替代之日,便是可期盼的革命诞生之时。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希望、普鲁士军官团所害伯的事情没有出现——至少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确实处于再也无法容忍的紧张状态。德国军队并未被搅乱,相反,所有的军队,德国的或其他各国的,都被证明是军国主义化的有效工具。
“军国主义”一词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已被如此普遍地滥用,学者在使用此词时必须小心。我们在此使用此词只是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已占着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强调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强调个人行为中体力上的勇气与自我牺牲,强调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英雄式领导;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种观念,认为国家体制内不可避免地出现武力冲突,为此必须培育出具备必要品质的人来引导这一冲突。到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已达到很显著的地步。战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了。武装力量不再被看作是皇室的禁卫军,而是国家的保卫者了。
王朝统治者靠尽可能多穿制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来强调自己领导国家的作用;用军队游行、军队乐队、军事典礼来强调国家形象,使各阶层的民众也能普遍认同。
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主义不单纯属于资产阶级所有。马克思写到“工人无祖国”时,他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的情况,这些工人生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农村,在城市中度过了艰苦的童年,至今仍同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剥削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五十年后,随着国家教育的实施,力量强大的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报刊的出现,局面变了。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主义的反响已经等同于对社会主义的反响,能把这两种思潮搅到一起的人便成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工人阶级冲破各国边境联合起来的呼吁,在1914年吹起的喇叭声中随风散开了。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种过激的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乃反动统治阶级成功地向群众灌输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使群众放弃支持革命,吸引群众支持现存的社会制度。实际上,统治阶级中那些最反动的人,是最不相信国家主义的。黑格尔与马志尼朱塞佩·马志尼(J。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其吸引力,他们认为,民主同国家主义是互相促进的。参预国家事务的意识越强,国家越能真正体现它所建立的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不平凡的制度,人民保卫国家、服务于国家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国家成为民众效忠的焦点之后,宗教势力才能被遏制。国家为那些已经超过爱幻想的年龄、尚未事业有成的人们准备好了人生的目的、多彩的生活、激动的时刻与庄严的地位。但是,国家只有同别的国家相比,才能量出它的价值与力量。无论国家的目的有多么和平,国家的理念有多么高大,它想避免(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都在试图避免)一个结论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个结论就是:国家的最高使命是战争。
这样来解释1914年最令人夺目的现象,似乎就可以讲得通了。这一年,激动的人群拥塞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英国的志愿入伍者堆在征兵处想在紧张局面结束前进入法国;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穿着过时的制服,戴着白手套,军帽上插着大毛球,步伐整齐地进入战斗;德国的预备役军人,夏天还是大学生,现在手挽手,唱着歌,去迎接英国人在朗吉玛克的机枪手们送给他们的死亡,这种几乎像是狂喜的气氛,显然是受到当时文学作品的感染。1914年,就像1789年,虽然看来可说是一种体制的大崩溃,也许是一种文明的大崩溃,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蜕变与更新的时刻。在1789年这个无限空间里,郁结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受到军事专业训练的广大民众怀着充分无比的良好愿望向前挺进。他们踩烂了靴跟去争取实现施里芬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毫无怨言地把生命贡献出来,去履行乔弗里的进攻战略。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前进。支撑欧洲各支大军的热诚在1914年爆发,但在两年后开始低落下来。但是也有例外,至少英国与德国两国,这种热诚只是被纳入了顽强不屈与耐心硬撑的格局。
这种热诚是广泛传播的,不仅军队,而且包括军人之所由产生的各个社会阶层;报纸刊物既反映了又助长了这种热诚。如果把这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宣传、操纵,那是机械的曲解。英国与法国的传统政治家阿斯奎思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伯爵(Asquish;1852…1928),英国著名政治家,1908年任首相。他的第二任妻子马戈特·阿斯奎思伯爵夫人(1864-1945)也是一位著名人士,以聪敏闻名于伦敦,曾写过自传体的小说。们与维维安雷内·维维安(Vivian,1863一1925),法国政治家,1914年6月当选为内阁总理。
们在战争初期掌握大权的,被级别较低的人物如劳合乔治戴维·劳合-乔治伯爵(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首相。
们与克莱蒙梭乔治·克莱蒙梭(G。 Clemenceau;1841—1929),两度任法国总理,人称“老虎总理”。们不客气地挤到了一边,后者较能对我们所谓的“极右翼”作出反应。甚至在德国,平民首相贝特曼-霍尔维希(Bethmann … Hollweg)于1917年在统帅部策划下被迫下台,继承他的亨登堡(Hindenberg)与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军事独裁受到一个强力组织“祖国前线”的支持,这个组织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也许最大的支持来自中下层阶级。
所有这些使得只有很少一些有远见的先知者预见到将来必定会出现全社会总动员以投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些思想家曾以为20世纪的战争将是速战速决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大规模战争还能是不速战速决的。
所有适龄男子都穿上了军服,还有谁来耕地?谁来工厂做工?算算战争的巨大费用,整个财政机器还能不垮台?——战争国际化,国际贸易中断,财政还能不垮?所以,战争一定会在圣诞节前结束,谁也不去想,要是结束不了怎么办?
到圣诞节硬是没有停战。西线并未转入僵持局面,东线也没有决定性的战果。18世纪的政治家们只向各自的君侯负责,如果现在还是他们当政,在打了一场像1914年那样既无明显胜负又耗资巨大的战事之后,到1915年也许会跑到一起来拟订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和平协定。可是,1914年启端的战争,具有公众热诚、公众期望、公众义愤的威力,是无法像1792年那样轻易驾驭的。欧洲各国人民全部武装起来,并已承受了可怕的牺牲,是不会只作出一点小调整以保持权力平衡就罢休的。俄国人,通过他们新建立的代表性机构,不仅要求保证东南欧的斯拉夫人置于俄罗斯的保护下(这样就会使哈布斯堡帝国四分五裂),而且要求获得俄国外交政策历史悠久的老目标——君士坦丁堡。德国人,除了少数无畏的社会主义者外,要求获得领土足够抵御敌人方面的任何一种联盟,永保本国的安全。英国人,用阿斯奎思先生的话来说,在彻底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威胁以前,誓不把剑插回鞘内,直到德国人最终彻底失败,以致其政治制度可由协约国来任意摆布。
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作出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
到了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战术——德国人称之为“压倒战术”,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英国人1916、1917年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区别只在于更延长了时间。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最长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