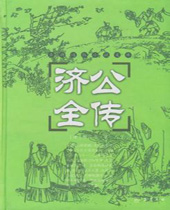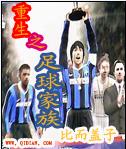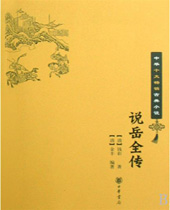蒋氏家族全传-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个县,对于全地区桥梁的铺设和水利设施,都了如指掌。
1940年夏季,蒋经国提出“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之后,又改为“五年计划”,准备在赣县郊外的中华新村设立现在建筑的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再设立贫民食堂,以收容孤儿、弃婴,取缔私娼、烟馆、赌博场,帮助犯罪者重新做人,还反对浪费的恶习,鼓励集体婚礼。又准备开设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以统治米、食油、盐等日用品,并把原来四十余种赋税简化为一种,以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官差从中盘剥的机会。
赣南过去的征兵制度,是以没有能力或不愿进行贿赂的贫民子弟为对象;新计划法令规定,即使是要人之子,也无法避开兵役的责任。
对于文教政策,相继出版发行《正令日报》和期刊《中国青年》,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刊印了一份《青年日报》。
与此同时,对管区内5万余名三青团员进行指导教育以使他们大部份成为东南战区的骨干分子。
新计划严格区分公与私,规定公职人员私用长途电话费,自己掏腰包支付;每星期一下午,打开公署的大门,听取民众的申诉。
蒋经国这般作为,使得政府高级官员望而生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一时被人们称之为“全面政治建设的模范”。只因1943年12月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离开江西到重庆赴任,没有看到“五年计划”的成果,但他的设计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目的是要在赣南这块试验区内搞出一个国民党行政规范的样板来。他经常将所谓“新赣南”同当时享誉中外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地区相比,并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的确,原本是“烂摊子”的赣南,经蒋经国的治理整顿后,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蒋青天”的称号也成为一时之誉,经国民党传媒的大力渲染,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许多外国记者也纷至沓来。
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蒋介石调到重庆任职,虽然名义上仍兼任赣州专员,但实际上从此离开了赣南。赣南的6年,可以说是蒋经国日后发迹的起点。赣南的6年也是蒋经国的辉煌时期。于公,他赢得了好的政声,为他由地方至中央、由赣南走向全国赢得了政治资本;于私,他开办了江西青干班,为自己培植亲信和嫡系干部,由此他还结下了一段风流姻缘。
1940年6月,蒋经国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取得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7月,被任命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这实质上是江西支团的首脑“第一把手”。但当时的三青团首领康泽却不买这位“太子”的帐洗使个杀手铜,在江西三青团支部安置了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是架空蒋经国,使其成为空头主任。蒋经国当然不甘示弱,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扶植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在赣州赤殊岭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在“青干班”的生活和训练中,蒋经国强调要“同心同德、患难与共”。要求不分男女,都以“兄弟”相称,号召“效忠团长”(蒋介石)、“主任”(蒋经国)。以后故有“赤殊岭精神”一说。“青干班”第一期是在1940年1月1日开训的,3月结业,为期三个月。赣州“青干班”共办了万期,训练学员500余人。这批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
1942年,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旨意”作了一次短暂的“西北之旅”。蒋介石也曾一度设想让蒋经国涉足新疆,掌握新疆大权。蒋经国本人也觉得新疆这块地方靠的苏联,他对苏联情况最熟,何况在赣南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加上在赣南的政绩还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首肯。现在要换一块更大、更重要的“用武之地”让他大显身手,那更能在父亲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才干”。因此,他从内心里是感到高兴的、跃跃欲试的,有好一阵子他的脑子里经常浮现出清朝“钦差大臣”左宗棠的影子,越想越觉得去收拾和整理盛世才留下的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了。
然而,蒋经国出任新疆主席的美梦却最终难圆。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在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嫉妒蒋经国,认为他年轻、资历浅,不堪担任“封疆大吏”的重任,让他去新疆独挡一面未兔太锋芒毕露了;其二,就是在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怀疑蒋经国,认为他从苏联回国后,在赣南的所作所为正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如果再让他把这一模式带到新疆去推广,“岂不比盛世才还盛世才”?这样,蒋经国治理新疆的“雄心大志”终于成了黄梁一梦。
“新疆王之梦”既已成泡影,蒋经国不得不重新设计他的前程。蒋经国深知政治斗争之险恶,深刻地领悟到,没有党派组织做强有力的后盾月B么再高明的“行政官”也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蒋经国决定还是寻其父蒋介石的“旧梦”走黄埔军校起家的道路。蒋经国首先选定的学校是国民党CC系控制的中央政治学校。他认为控制了这所学校,就能逐步控制全国的县长、县党部书记这一级干部、一改“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岂料,一向控制国民党党校的陈果夫、陈立夫哪能容忍蒋经国涉足“陈家党”。这样,蒋经国染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一职的企图又泡了汤。蒋经国只得另谋出路,把希望寄托在三青团上了。
1943年,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蒋经国当选为中央干事。会议期间,蒋经国提议,将原“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升格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作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团校”,以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一决雌雄。蒋经国这个提案很快获得通过。
19M年元月,蒋介石改派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这是蒋介石精心培植蒋经国取康泽而代之,以真正控制三青团的一个绝招。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起于江西,抓党组团,同是发动于江西。这次走马上任,率领一批来自赣州的嫡系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陪都”重庆“复兴关”,进驻“青干校”。很快就把持了“青干校”的实权,将康泽排挤出局。
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1946年初,蒋经国将原“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学员作为“青干校”的第一期学员,换发毕业证书,改组“青干班同学会”为“青干校校友会”由蒋经国统一领导。原“青干班”已毕业的一至五期学员,实际上已掌握着三青团各支、区、分团的大权,现在这批骨干已为蒋经国所控制,大大强化了他在三青团内的地位和影响。此外,在“青干校”内还附设了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专门招收一些具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为蒋经国培养幕僚以及亲信骨干。1946年9月,在庐山举行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最后“圈选”的72名中央干事中,蒋经国仅次于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位居第二。不久,又进行了中央团部的人事调整,蒋经国以中央常务干事兼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之职,直接把持三青团组织训练、干部培养等大权。所以,当时在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里,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中央干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干部的干部”。
在牢牢掌握三青团实权之后,蒋经国又把目光转向国民党的军队。后来,等到蒋经国把青年军的政工系统全部抓到手的时候,他在重庆的“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为他日后继承“父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时,以他为首的“新太子派”业已形成,他的组织力量和干部力量足可以同CC系、黄埔系等几个大的派别并驾齐驱了。
但是,蒋经国以在赣南“推行新政”起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却也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政敌。一些人攻击他,说他是“左派共产党的代理”。而当时,蒋经国的思想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抗战时期,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行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很少。而蒋经国居然能得到它,不但得到,而且看得非常仔细。甚至吩咐当时在他领导下的抗敌委员会所办的《动员旬刊》将延安方面的一些政治文章加以文字改动后转载,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抗日的作用。
薛汕在回忆蒋经国时曾说:
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大约是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是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辩》,登在《新赣南》上。我认为,辩与不辩,为无补于事,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境况而已。
一天,蒋经国问我:“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面有什么反应?”我说:“没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这样就那样,总要有意见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有共同点,指责也就绝不会少。
“推行新政”之举,固然反映了蒋经国初涉政治舞台、踌躇满志的欲以“政绩卓著”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欲望,多少有些“想出风头”意味。但是,就工作实绩而论,他也的确颇有建树,这一点是后世史家所共认的。当时的蒋经国,年轻、有朝气,政治上比较开明,思想上也比较左倾,对于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的确做了一些“体恤下情”的好事。为了推行新政,他甚至不惜微服私访,化妆成小商贩去抓赌禁娼。再如禁烟,蒋经国更是不遗余力,顶着巨大的压力强行查禁,表现了一个青年政治家的胆识与魄力。
30年代至40年的赣州,由于远离首府、地近广东沿海,所以烟馆林立,贩卖鸦片的人很多,抽大烟的人更多。蒋经国先是下令禁烟,接着下令动手抓人,以至抓的人太多,监狱里都人满为患了。对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关又关不下,放又放不得。于是,蒋经国又开办了“强民工厂”强迫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做工。1940年,张治中将军由广东韶关到江西,蒋经国还专门陪他参观“强民工厂”,受到张治中的赞扬。
蒋经国的“平民思想”和家乡观念也很郁厚。从苏联归国后,也许是长达12年的乡恋积郁过久过深的缘故,他在溪口“静读”期间,就曾有过不少关心桑样的善举,也曾多次到家乡的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日,动员家乡人民奋起抗战。就在这时,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安排到江西工作。
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去任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避祸。为使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向军校把他调来做帮手。
蒋经国到江西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州县长,成了一个执掌实权的“父母官”。这时,蒋经国又把溪口武岭学校的张凯、邓士萍、徐恒赢(都曾任武岭学校的教务主任)、胡乐天、黄寄慈(都是武岭学校的教员)等人调至赣州,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当时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战争的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匾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大家请求毛太君设法救荒。毛福梅想到儿子,遂派帐房先生唐瑞福去赣南找经国商量。
经国见到母亲的特使,备了丰盛的酒菜为瑞福哥接风。唐家与蒋家原无亲眷关系,只因为当年蒋介石出生时,蒋母王采玉奶水不足,刚好唐瑞福的祖母也养了个孩子,蒋介石吃的头口奶就是唐老太太的,所以毛氏一向把这位老太太当婆婆看待,这层关系蒋经国是知道的,所以他称唐瑞福为兄,相见特别亲热。
唐瑞福说明来意,经国略一沉思,随即爽朗地说:“这里大米有的是,但运输困难。不过瑞福哥,你放心在这里住,玩几天再回去,我会设法将米运过去的。”
唐瑞福有事挂心,急于回家,只住了两天,就赶回了溪口。回到溪口,只见满街都是背着米袋的人,原来从江西运来的米已先运到了。大家正在抢购呢。唐瑞福自己家里也缺粮,赶紧去买,但已卖完了,不免有点懊丧。毛氏安慰他说:
“这次经儿运来八百石米,被地方上插手,好处都让手长的人捞了去,有许多缺粮户向我告状。你再辛苦一趟,让经儿再运批米来,我们丰镐房自己掌秤,别让老实人吃亏了。”
第二次,经国又从江西送了1200石大米到溪口。这一来,溪口缺粮少钱的人暂时都渡过了难关,受惠人千恩万谢,都夸毛氏养了个好儿子。
报效桑梓的思想,并没有因为从政既久而淡化。张国祁先生曾撰文披露过有关细节:
在蒋经国的家乡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家家户户忙着腌腊肉、磨年糕、办年货,洋溢着一片丰年兴旺的情景。春节前几天,我们走访了唐瑞福老人。
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和蒋经国是三代世交,曾经是蒋家丰镐房的账房先生。谈到他在蒋家管账的经历史,他说:“我两度给蒋家当账房;第一次是在1939年,那年蒋经国从江西赣州回到家乡,他对我说,瑞福哥,我同几个长辈商量过,请你当帐房,托你做好几件事:一是给祖宗上坟作忌;二是同亲友人情往来;三是帮我家管管帐。第二次在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那时我在宁波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