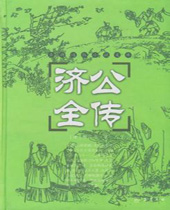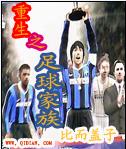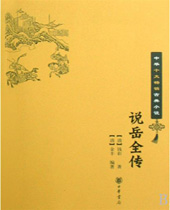陈氏家族全传-第8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记者对孙禄卿的话很感兴趣:“夫人感觉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如何?”
孙禄卿说:“别看我们现在这么忙,我倒觉得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哪里是人的生活呢?”
陈立夫接过来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易经》上也讲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们当今落此光景,也是自然规律。”
记者问陈立夫:“那你现在的心境如何?”
陈立夫笑笑说:“自得其乐,乐此不疲。”
记者又问:“假如有一天,台湾政府又邀请你,你会不会重返政坛?”
陈立夫不假思索地道:“我会婉言谢绝。”
在美国住留不久,因为他原来的地位和名气,便有人请他到大学讲讲课,且答应报酬颇为丰厚。
对此陈立夫犹豫了半天,还是拒绝了。
从经济条件来看,他确实需要增加额外收入,除了实业上的需要以外,还要供养孙子上学,还要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但是他不想什么样的钱都去挣。
陈立夫当年自己是留学美国学矿冶工程的,如今年代已久,早已忘却,至于中国文化可以讲,但这是在美国的大学,讲得必须十分慎重,而且还要长时间备课,想想还是不去讲为好。君子谋财,取之有道吧。他还是集中精力办自己的养鸡场。
陈立夫发现养鸡也很有学问,比研究政治更容易发生兴趣。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
正在陈立夫一心扑在养鸡事业的时候,1961年,他的父亲陈其业在台中病危。
陈其业乃陈其美长兄,蒋介石对他十分尊重,这次不得不亲自向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发了电报:
“尊翁病危,盼即返国。”
陈立夫接到电报以后,百感交集,可以说是既难过又难受,半晌没有说话。
10年前,因为政治原因,他离开80高龄的父亲,远走异国他乡,当时,果夫卧病在床,病人膏盲,但他还是义无返顾地走了。
他离开台湾的第二年,陈果夫去世,台湾拍来电报,让他回去参加葬礼,同胞兄弟在政坛上风雨同舟几十载,何不想回去见兄长一面,但当时刚刚离开台湾,蒋介石正集中精力整肃CC派,他不敢回去。
不敢回去,又为失去情同手足的兄长万分哀痛,于是,他伏在案头整整哭了一天。
他想起了离台前跟陈果夫告别的情景,想起了陈果夫那张痛苦的脸和那些令人伤感的话,谁知道,那匆匆的一面竟是诀别。
失去果夫兄,确实让他柔肠寸断,肝胆欲裂,痛不欲生,因为他们不仅是同胞兄弟,还有共同的使命把他们连在一起。
国民党“改造”以后,封赠陈立大“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等虚衔,陈立夫不敢回去。
国民党“八大”时,又把陈立夫增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陈立夫仍未回去。
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捎话,让陈立夫回台湾看看,他也谢绝了。
现在,年逾九旬的老父亲就要去世了,回不回去呢?
陈立夫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
要说不想回去看一眼病危中的父亲,对于倡导中国文化,提倡重整道德的陈立夫那是不可能的。当年离台出走,对父亲便是一个打击,10年了,生未能尽孝,死了还不为老人送终吗?这简直是天理难容。
可是,回去又怎么样?
家里的摊子谁来经管?还有,台湾政界是什么样的态度,蒋介石对自己是什么态度,回到台湾,会见到一张张什么样的面孔?
孙禄卿很理解丈夫的心境,安慰他道:“不管怎么说,老人病危了,我们也应该回去,不然于天于地于良心都说不过去。我们回去是看望父亲的,不问政治就是了吗?有什么值得为难的?”
陈立夫觉得夫人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下了回台湾的决心。
2。奔父丧重返台湾
1961年2月24日,台北松山机场。
通往机场的公路上,自下午2时起,新式轿车、吉普车、旅行车川流不息,源源不断。
各式各样的男女从汽车上走下来,挤往机场会客厅。
新闻界的记者们也潮水般地涌向机场。
3时整,忽然下起了雨,雨水冲刷着机场,冲刷着车辆,冲刷着拥挤着的人们。
3点5分,一位身材矮胖穿藏青色中山服的人从通道机场转弯处下车,他的两手插裤袋,沉思地穿人行道,冒雨踱步踏人机场接待厅。
他是蒋经国,他到机场是欢迎从美国飞来的一个重要人物。
欢迎的人群中,除了较年轻的记者外,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至少也是45岁以上的人,他们都是国民党的政界人物,其中“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较多,大都是CC派的人。
这些人中,一部分是从外县市赶来的,他们冒雨等待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人物到来。
一个很有经验的记者说:“这是正宗的政治新闻。”
这些人是欢迎陈立夫的。
泰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快要驶上跑道了,能够获得机场人场证的人都进了机场。
剩下的人仍在会客厅等候。
3时15分,机门打开,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
接着走下飞机的便是白发银丝的陈立夫。
在欢迎人群面前,陈立夫挥着帽子向大家招呼致意。
下机5分钟后,陈立夫夫妇便离开检查室,可是他们夫妇两位寸步难行,从检查室到门口贵宾室,平日最多一分钟可以到达,这天却被挤了10几分钟才到达。
陈立夫夫妇一进贵宾室,门就被关上了。
“副总统”陈诚正在贵宾室等候陈立夫夫妇。
陈立夫激动地伸出双手:“谢谢陈副总统前来迎接。”
陈诚也热情地道:“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记者们在门口等得焦急,力图挤进贵宾室,拍下这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真实镜头,却被警察挡住。
两分钟以后,陈诚陪着陈立夫夫妇走出贵宾室,人潮又涌了上来。
蒋经国、朱家驿、李石曾、莫德惠。陈启天、孙亚夫、黄国书等人抢上前去,和陈立夫夫妇握手问候。
陈立夫的孙女温梦营迎上前去,向陈立夫夫妇献上一束鲜花。
陈立夫高兴地把孙女抱了起来。
机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面对这个人声鼎沸的场面,陈立夫激动地流下眼泪。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是在政治上失意之时离开台湾,在美10年,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清心寡欲,不问政治,而一朝回台后,却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真有受宠若惊之感。
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人是要来欢迎他的。
除了国民党元老人物不计以外,当时在“立法院”、“监察院”、“行政院”、“国大代表”中,有不少人是陈立夫亲手提拔起来的旧部。因此,当他们听到陈立夫返台的消息以后,没有一个不争先恐后地到机场来欢迎他,于是,便造成了机场上一个空前的热烈场面。
陈立夫回到台北寓所后,曾向记者发表了如下书面谈话:“立夫出国年逾十载,退思补过,蛰居美国乡间,绝不耳闻政治。
“在此之间,对于留在国内之家父,未克稍尽侍奉之责,愧作殊深,幸承总统暨诸亲友同志多方照顾,各位主治医师悉心诊疗,深情厚谊,永铭肺腑。
“家父身体素健,兴趣甚佳,年逾九旬,尚能出席各种会议,此番病起仓猝,曾一度十分危险,消息传来,为之寝饮难安,正拟设法赶归侍疾,乃蒙总统先赐电召,当即尊命兼程返国,下机后欣悉家父病况尚未恶化,但仍在危险时期。
“惟望此番归来,有助于家父病体之康复,则余愿已足。
“内子禄卿除偕归侍疾外,以其继母今年已七十七岁,亦思归省,故亦同返。
“如家父病体幸得告痊,仍拟与内子即行返美。因离美时匆遽成行,各事均暂托友人代为照料,日久则困难殊多。
“今日下机时,承陈副总统与诸亲友远道冒雨而接,不胜感激。因急于探视老父病况,未及…一谢捆,尤深歉疚,唯祈祷予厚谢!”
陈立夫的书面讲话,确实是抵达台北以后才写的,虽然该话稿并非他本人手笔,但其内容却为陈立夫口述。
这一书面谈话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是对自己来台以后的去留问题作了答复。
在台湾,曾有人认为陈立夫的这段话虽然是本人口述,但听起来有些言不由衷,即使他有意留在台湾,也不能自己直接道来,需经台湾当局主动作出安排,他好顺水推舟,在这之前,他不得不表示其返美之意。
当时,新闻界各执一辞,引起哗然。
据接近陈立夫的一位人士透露,陈立夫在书面讲话中特别提出“即行返美”的意思,的确是因为陈立夫此行并未打算在台北久留。因为,如果陈氏并无返美的决意,他在讲话中不提及这个问题就是了。目前的客观环境并未迫使陈立夫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表示,除非他的确有意返美。
说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灭,也不完全是事实。
几十年的政治生活。留给他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他当年远走美国完全是出于无奈,是想出去避避风头,后来看到陈诚、蒋经国的政权根基越来越稳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念头也就渐渐打消了。
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想顺便观望一下台湾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如果台湾能容,他还是有意回台,自谋生计、远走他乡毕竟也是很凄苦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思乡之情,是任何物质享受所不能替代的。
到台湾的第二天,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拜望蒋介石。
一见陈立夫,蒋介石表现出特有的热情,他迎出门外,与陈立夫紧紧握手:“立夫.一别10年,我可是无时无刻不想念你呀。今日归来,实乃是令人高兴之事。”
陈立夫双手一拱说:“承蒙总统关照与厚爱!我奉命返回台北,总统,别来无恙吧!”
“好的,好的。”蒋介石操一口地道的老家话,“立夫在美国也混得不错吧,虽然不断打听你的消息.亦曾几次写信予你,但毕竟10年过去了,难得一见啊。”
陈立夫说:“‘我在美国的乡下生活,那里风景秀丽,气候适宜,颇能修身养性。我做些养鸡著书的事,倒也过得充实,只是闲下来的时候,也常想起台湾,想起总统,唉,毕竟是故乡难离啊。”
陈立夫说这话的用意是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这次回台有什么安排。他说得很婉转,但蒋介石想必会明白。
而蒋介石却有意避开这个话题:“果夫去世转眼也七八年的时间了,现在想起来,我就感到痛心。当时我把葬礼搞得隆重,就是因为果夫对中国革命有过杰出的贡献,政绩斐然。还有,姚文英(陈其美之妻)女土在台湾大学卧病多年,我也经常派人前去看望,最近身体还好,这请你放心就是了……”
陈立夫嘴上说:“多谢总统关照。”同时细听下言说什么,但等了半天,蒋介石总扯不到正题上来,他有些灰心。
陈立夫哪里知道,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现在蒋经国的地位还没有真正稳固,CC派的势力还不可低估,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让陈立夫卷土重来呢?
除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以外,台湾各报对陈立夫的报道也很少。
“新闻界除对陈氏行踪及尊翁病况略有报道外,其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煌赫,受其扶掖提携者自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寂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中央报,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
这是《公论报》对此情形作出的评论。
几天以后,蒋介石又找陈立夫单独交谈过几次,谈话内容跟第一次大同小异,始终没有劝陈回台定居的意思。
在这期间,蒋经国还亲自陪陈立夫前往陈果夫墓祭奠扫墓。
蒋经国还几次去探望陈父陈其业。
陈立夫见重返政坛无望,便一心一意侍奉父亲,尽一个远道而来之子的孝道,但陈其业毕竟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诊治,终于寿终正寝。
陈其业死后,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蒋经国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
陈诚、蒋经国等率2000多名国民党要员参加葬礼。
台湾的《征信新闻报》也发表社论,称赞陈立夫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纪律的人物”,并劝陈“不要介意于十几年前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而再次报效国家”。
此时,蒋介石的“改造”运动已见成效,肃清CC派系已是时间问题,然CC派仍负隅顽抗,张道藩下台,CC派失去了“立法院”长,显然是一大失败,为了挽回面子和减少损失,他们又争副院长的位置。
正在这时,CC派见陈立夫返台,觉得有了主心骨,纷纷向陈立夫靠拢,指望他能站出来说话。
但是,陈立夫看出CC派与主流派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如果帮助主流派来压制CC派,等于控制自己的墙角,他也不会那样干;如果支持CC派闹下去,蒋氏父子更不能谅解。陈立夫感到十分为难。
陈立夫只能说一句话:“不问政治。”
CC派的人问陈立夫能不能回台湾定居,陈立夫说:“过去有句话叫‘动则得咎’,我现在是不动也得咎”。
陈立夫为父亲奔完丧,即悄悄返回美国。离台前,他考虑到再回台湾已不是件容易事,便携夫人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3.再度赴美已然淡泊和自省
陈立夫在台湾住了42天,一般都深居简出,即便是他当年的下属CC派们来访,他也“莫谈国事”,只是互相问候,拉拉家常,或者找知己谈谈中国文化,跟实业家谈谈养鸡,很少主动到外面走走。
他没忘记远走之前的失意,也没忘记自己此次返台的身份和目的,他显得很谨慎。
对于记者的采访,他一般不见,实在无法推托,也是把话题避开政治。
香港《正午》报1961年6月报道:
当陈立夫为其先父治丧后,台湾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