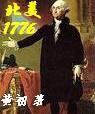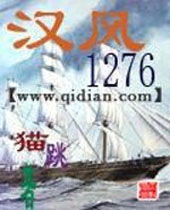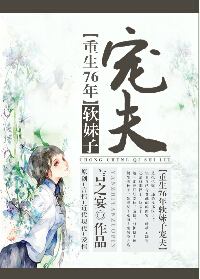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月二十五日,俗以仓官诞辰,用柴灰摊院落中为囤形,或方或圆,中置爆竹以震之,谓之胀囤,又谓之填仓。” 再次是饮食方面的变化。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念五日为填仓节。人家市(买)牛羊豕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尽饱而去,名曰填仓。”乾隆河北《永平府志》也记载:“是日必具食餍饱。”在山东淮县,“天仓二字,邑中俗习天或转为填,仓则转音为嗓,于是以‘天仓日’为填嗓日,谓宜以美食填嗓,故每届是日,家家食物较平时必加丰腴”。这是填腹中的胃仓。 明清时代填仓节与天穿节有相混的现象。有人认为填仓节起源于天穿节。这是由于天仓节与天穿节日期相同或相近;二节名称发音也接近;加上天穿节起源虽早,但在明清衰落,而天仓节却兴起于明清。比如在山西省,明嘉靖《曲沃志》卷一《风俗》说:“二十,作煎饼,邀婿填仓。”填仓节的名称下是天穿节的风俗,二节已混。清同治《阳城县志》记载:“新正念日前夕,各家以粱、黍为屑作饼,虔祀仓官,名曰补天穿,俗曰添仓。咸于室隅处燃灯,名曰照鼠嫁。”把添仓作为天穿的俗称,而所记风俗事项,糅合了天穿节和添仓节。一般来说,上述混合是将天穿节更改为天仓节。所以地方志中记载多数如前举《曲沃志》一样,把煎饼说成是填仓风俗。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晦日•;中和•;二月二(1)(图)
正月的最后一天和二月的初一、初二,相连的三天曾分别是晦日、中和、二月二三个节日,下面分别论述。 晦日 晦日是指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即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正月晦日作为一年的第一晦日即“初晦”,受到古人的重视。 南朝梁的《荆楚岁时记》记载:“元旦至于月晦,并为酺(p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乐。”看来划船或到水边宴乐是正月的习俗。北朝也有此俗,魏齐时代的卢元明、魏收分别有诗《晦日泛舟应诏》,描写了春游的情景。可知当时泛舟是君臣一起进行的活动,大臣还要赋诗祝贺,而且泛舟更明确是在晦日进行。实际上,到水边不仅仅是宴乐,隋朝杜台卿《玉烛宝典》说,正月初一到月底,人们都做些菜肴聚饮,泛舟游玩。士女都到水边洗裙子,倒点酒在水边,用来解除灾厄。说明人们在水边还有祓禊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活动在隋代进一步集中在晦日进行。杜公瞻注解《玉烛宝典》正月祓禊说,当今之世,人们“唯晦日”到河边消灾解厄,妇女有的还去洗裙子。 唐代的晦日已成为重要节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九月诏说:“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官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旧唐书•;德宗纪下》)把正月晦日作春游的节日提倡,德宗向官员赐钱,并“永为常式”。 唐人重视晦日,有大量诗歌描写它。《晦日高文学置酒外事》的组诗中,诗人郎余令有“三春休晦节,九谷泛年华”;解琬有“欢娱屡晦节,酩酊来还家”;宋之问的《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遥楼》有“晦节高楼望,山川一半春”;岑参的《晦日陪侍御泛舟北池得寒字》有“春池满复宽,晦节耐邀欢”等诗句,讴歌春游、泛舟、聚欢的情形。 唐代晦日仍有祓禊活动。沈佺期《晦日浐水侍宴应制》诗说:“素浐接宸居,青门盛祓除。”讲长安东门外浐水边的祓除活动。张说《晦日》诗有“晦日嫌春浅,江浦看湔(jiān)衣”;严维的《晦日宴游》有“晦日湔裾俗,春楼置酒时”的诗句,反映了水中洗裙的习俗。 唐代还具有祓除意义的陆上晦日送穷活动。这在唐诗中也有所反映,李郢《正月晦日书事》有“盐米妻儿夜送穷”之句。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中的“引客看扫除”,也是描写“送穷”。特别是姚合有专门歌咏送穷的诗歌《晦日送穷》,他说:“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沥酒当是送穷的习俗。“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表明送穷活动非常流行。 此外,文学家韩愈还著有《送穷文》,开篇说:“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qiǔ)与粻(zhāng)牛系轭下,引帆上樯。三揖穷鬼而告之曰……”虽然此篇系自嘲穷困不达的文字,但所说的“穷鬼”是有民俗基础的。唐代文学家李邕《金谷园记》说:“高阳氏子瘦约,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与之,即裂破,以火烧穿着之,宫中号曰穷子。正月晦日巷死。今人作糜,弃破衣,是日祀于巷,曰送穷鬼。”(北京大学钞本《荆楚岁时记》,转引自刘桂秋《唐代的“送穷习俗”》,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又韩鄂《岁华纪丽》引文有异)可见传说穷鬼是颛顼(zhuānxū)(高阳氏)之子,喜欢穿破衣服,喝稀粥。由于为他送葬,留下了“送穷”之名,习俗是作糜、弃破衣、祀于巷。韩愈在文中说他要送的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鬼,非《金谷园记》所说穷鬼。其数为五,不知是否有民俗基础,而这五种类型是他的发明。 宋代送穷还有在正月其他时间进行的。一是在初六,北宋《岁时杂记》载:“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岁时广记》引)这个送穷之俗,实为迎人日举行。二是二十九日,《图经》记载,安徽“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日,扫除屋室尘秽,投之水中,谓之送穷”(《岁时广记》引)。此《图经》,中村乔推测是宋苏颂的《图经本草》。此俗后世也称作“窈(yǎo)九”,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二说:“闽中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窈九,谓是日天气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枣之属作糜之……窈也,穷也,皆晦尽之义也。”据此,则送穷有将最后一日送走之意,而晦字又有阴暗、暗气之意,送穷也是将这些不好的东西送走。 明清时期破五的送穷风俗承继了唐宋晦日送穷传统。由于唐代以中和节取代晦日节,晦日节遂衰落,其中送穷风俗逐渐移向正月初五。其证据一是明清时期定于五日五更(戊时)送穷,谓之“送五穷”,与文学家韩愈送五鬼诗文的流传有很大关系。其二是破五送穷与晦日送穷习俗相近,比如唐人于晦日送穷,又于二月二日“迎富”,而清乾隆修山西《大同府志》记载:“五日,剪彩纸为人,小儿拥抱戏通衢,曰‘送穷’;有攫而去者,曰‘得富’。”很像是将晦日与二月二的活动移入初五。又如道光陕西《咸阳县志》记载:“五日,剪纸人、破衣,以残饭置僻处,曰送穷。”作糜、弃破衣均是唐人送穷之举。清咸阳送穷中,虽“残饭”和“糜”不尽相同,但也符合穷鬼所食之物,与唐俗大致相同。再如清同治山西《河曲县志》记载:“初五日,俗谓之破五。黎明,扫室中尘土污秽送于巷口,焚香燃爆,名曰送穷。”扫尘土送于巷口的行为明显地与《图经》和《金谷园记》所述风俗一脉相承。此种风俗一直流传到近现代,民国陕西《中部县志》记载:“五日未明,束纸为人、舟车、糗饵,送之通衢,谓之送穷。”所说的舟车、糗饵均是韩愈送穷文中的描写。而民国陕西《续修南郑县志》更明确指出:“五日,扫除门庭尘积炮滓,弃通衢,亦韩退之‘送五穷’故事也。”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晦日•;中和•;二月二(2)(图)
中和 二月一日是中和节,始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这是一个由唐政权创立的节日。据《旧唐书》记载,该年正月诏书说,德宗以汉代崇祀三月上巳、晋朝重视九月重阳,皆“与众共乐,咸合当时”;而二月春方发生,“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为了“俾其昭苏,宜助畅茂”,于是以二月一日中和节,代替正月晦日节。这样中和与上巳、重阳成为新的“三令节”,依照旧例,有逢此三节于曲江赐宴之举。德宗还规定中和节政府休假一日。当时又根据宰臣李泌的建议,规定中和节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穜稑(tónɡ lù)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赠送,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丰年谷熟。 这个人为制定的中和节,将二月一日前一天的晦日废掉,旨在弥补二月无节的缺陷,不过人为设节也是以一定民俗活动为依据的。德宗在诏书中说二月一日是“天地和同”之日,李泌建议中也多是迎春、重农的事项。所谓“勾萌毕达”是说草木的芽苗都长出了;而“天地和同”也就是阴阳和同、阴阳持中,这是自古以来的思想。东汉后期产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就说:中和主调和万物,阴阳要在中和,天地阴阳只有沟通中和之气,才能相受共养万物。概括地说,就是“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所以中和节表达的就是天地、阴阳持中和同、万物资始的思想。关于中和与四时节气的关系,符载说:“中和,王节也,万国承之乐洪庆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发生之盛气曰春,春之于孟也,萌动而方微,于季也,发泄而过强,唯仲春木德乃茂沃,生人之恺乐,洗万物之枯槁,当三阳之正中,凝四气之太和,以正星鸟,以推律度。”(《全唐文》卷六九○)能够反映阴阳和同、三阳正中的仲春节气,惟有春分。符载说“以正星鸟,以正律度”,就是古代以春分标记时间确定节气的反映。春天是万物之始的季节,立春虽是春天到来的标志,但真正体现春天到来的是春分,气候转暖,万物复苏。由于春分成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已非特殊节日,三月三日又有上巳节,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所以二月没有重大节日,比起正月的诸多节日更显空缺,废晦日立中和从节日分布上有其合理性,结果造成德宗“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为古”(《新唐书•;李泌传》)的结果。 中和节的事项中,“司农献穜稑之种”来源于《周礼•;天官•;内宰》的说法:孟春,诏告王后率领六宫的人,将各种播殖的谷类的种子献给王者。献种与进农书都表示重农,上春服是贺春。《新唐书•;李泌传》说还要作宜春酒,也是贺春之意。勾芒既是春神也是社神,祭祈丰年。至于赠送刀尺,我们可以根据唐诗里的描述做一些分析:吕渭《皇帝移晦日为中和节》中说:“赐尺下新科,历象千年正。”在《中和节诏赐公卿尺》组诗中,陆复礼说:“欲使方隅法,还令规矩同。”李观有句:“岂止寻常用,将传度量同。”诗中的历象、规矩、度量等词汇,与《新唐书•;李泌传》赐尺“谓之裁度”之意相符,是应中和之名的表示。 中和节还有另一重要习俗“献生子”。朱胜非《绀珠集》说:“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更相馈遗,务极新巧,宫中亦然,故谓之献生子。”献生子表达的是由“献穜稑”祈年到祈盼生育的观念。 宋代尚有唐人中和节的流风遗韵。《梦粱录》记载,二月一日民间有“献生子”之俗,“禁中宫女,以百草斗戏。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武林旧事》说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进单罗御服。百官服单罗裳而已”。 宋以后中和节基本消失,极个别地方尚有余绪。《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京师于二月一日以江米为糕,上印金乌圆光,用以祀日,绕街遍巷叫卖,称为太阳糕。其祭神云马,题曰太阳星君。焚帛时,将新正各户张贴之五色挂钱,摘而焚之,曰太阳钱粮。都人还有游左安门内太阳宫的习俗。事实上,《尚书•;尧典》就有春分恭敬礼拜日出的记载。祭日供品太阳糕中的鸡,其起源甚古,《山海经》中有金乌载日神话,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出土文物已有其图形,乌变成了三足乌。古人的太阳崇拜表现为祭祀鸟神。清人太阳糕上印“金乌圆光”反映的正是此俗。《燕京岁时记》又说太阳糕上做一只一寸长的小鸡,这是由于日出鸡鸣的缘故,实质也是太阳崇拜的观念。 二月二与龙抬头 中村乔指出,选择二月二日的观念,在隋朝至唐初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当时孙思邈著《千金月令》说,“二月二日取枸杞煎汤,晚沐,令人光泽,不病不老”(《遵生八笺》卷三引)。中唐时二月二日有出郊外游玩的春游活动,如白居易有以“二月二日”为题的诗歌:“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描写春游的青年很多,在渡口都排列成一队行走的情形。从中唐至晚唐的诗人韩琮在题为《二月二日游洛源》的诗中说:“旧苑新晴草假苔,人还香在踏青回。”唐末五代初李绰《秦中岁时记》记载:“二月二日,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由上可知,唐代民间有二月二日春游踏青之俗,采菜是其中的一种活动。 宋代也流行二月二春游采菜,甚至以“挑菜节”、“踏青节”命名二月二日。宋代的《壶中赘录》说:“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岁时广记》卷一引)可知北宋初年二月二日春游之盛。而北宋哲宗、徽宗时张秉“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的题诗,使我们了解到挑菜在二月二日重要到名节的地步。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有《挑菜》项,记载当时宫中还举行挑菜的御宴。挑菜之俗在宋以后一直流传下来。 二月二日还有“迎富”之俗。唐末五代之际韩鄂《岁华纪丽》说:“昔巢氏时,二月二乞得人子,归养之,家便大富,后以此日出野,曰采蓬,兹向门前以祭之,云迎富。”此迎富之俗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巢人乞子以得富,二是出野彩蓬门前祭之。后一习俗来源可追溯到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记正月之俗:“百卉萌动,蛰虫启户,乃以上丁祀祖(道神)于门,及祖祢,道阳出滞,祈福祥焉。”二者均祭祀于门,迎富、祈福祥略有差异;实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