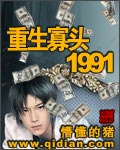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态的合作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陈腐的中间分子对合作企业持怀疑态度,他们把合作企业家当作奸商、投机者和颠覆社会主义的敌人。当卢日科夫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为合作企业发执照
的委员会时,合作企业的实验就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这是一项使命,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卢日科夫告诉我。没有人知道它能否从几十年压制个人积极性的旧体制下,从死守不放的权力下幸存。
一个与卢日科夫不同的合作企业倡导者是亚历山大?帕宁,他常用那种官僚所特有的不露感情又适度的腔调讲话,帕宁在研究所里是那一群没完没了地喝茶、几个小时无所事事的专家中的一员,据说他们都在研究完善社会主义的管理技术。帕宁曾仔细研读了西方管理学教科书,他断定最重要的是要解放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给在莫斯科的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胆地反对党的几十年的方针。他被召到位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委员们倾听了他的建议。帕宁告诉我,当时他必须,也不得不给他的关于个人创造性的想法加上许多华丽的修饰,以便不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抵触。但那些委员告诉帕宁,他们不能帮他实现这个想法,但他可以继续开展研究并和共青团组织联系一下,看来党中央对自由思考这件事情有了一些回旋余地。帕宁对中央委员们的反映吃惊之余,继续进行不懈地努力。随后他建议进行激发个人创造性的有节制实验——允许人们创办自己的合作企业,就是搞烘焙馅饼那样的小生意。最后,当局同意让他尝试,因此帕宁成了卢日科夫领导的合作企业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负责管理第一批“资本主义馅饼的烘焙”工作。
卢日科夫与帕宁在莫斯科市中心市政府大楼六楼一个像舞厅一样大的房间开始主持合作企业工作。大厅里简单地摆放了一些从旁边屋里搬来的可折叠桌子。工作人员白天在那里办公,通常晚上7点钟,卢日科夫走进大厅,他经常和那些企业家一起开会,直到深夜。
新商人们带着自己的计划、文件、问题挤满了大厅,他们那些实际问题,包括如何从国家计划经济中得到原材料,如何为他们新企业弄到房子和车库,等等。“他们中有的留着大胡子,有的披肩散发,有的长相我从来没见过。”卢日科夫以后回忆那些他印象中的新商人时说,“但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独立性强、令人感兴趣的人。其中有人想利用被丢弃的垃圾生产有用的产品,还有人发现人们对居住空间的需求,而国有建筑者们根本就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他们中有的人很聪明、有的擅长发明、有的有创造力——在大厅里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物。”
卢日科夫的年轻严厉的助手伊列娜?巴图里娜,以后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1988年死于癌症。巴图里娜回忆进入这间大厅的人和那些市政府官僚们是多么不同,那些官员看到吵吵嚷嚷的商人们聚在他们的大厅里都感到震惊。“我们经常从一间屋搬到另一间屋办公,”她告诉我,“因为隔壁办公人员都会抱怨那些留胡子、不干净的人坐在走廊上,实际上他们认为这些商人有损整个市政府大楼的形象。”
《莫斯科新闻》记者维克多?洛沙克亲眼见到了那戏剧性场面,他回忆,卢日科夫不得不为超前的合作企业商人们在企图压垮他们的官僚面前辩护。这些官僚之中,有一个是以管理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很难对付的女官僚们组成的集团。她们眼看着新经济从眼皮底下诞生,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她们仍想维护旧体制的各种原则,洛沙克对我说,“她们抵制合作企业运动向前推进的每一小步。”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5)
“我在等待合作企业管理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我记得第一个想办合作企业的妇女是一个职业戏剧演员,她有两个或三个孩子。她打算做的生意是在节假日卖自己烘焙的蛋糕。”接着卢日科夫说,‘主意不错!’另外两个或三个官员也表示同意。与卢日科夫他们唱反调的那些官员开始找能拒绝这个妇女的理由,‘您的公寓多大面积?’他们问。回答结果证明,房屋面积足够大,‘您有健康证明吗?’她也有健康证。‘那您还有时间照顾您的孩子吗?’那名妇女说,她的母亲与他们同住一个公寓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接下来一个在卫生部门控制流行病的女官僚问,‘您的公寓内有饮食行业专用的通风设备吗?’那名妇女甚至弄不明白她问的是什么问题。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设备,连我也不知道。那个女官僚是从饮食行业规则第八章第三条中发现,制作并销售蛋糕必须有专用通风设备。
“卢日科夫马上对那个女官僚说,‘走吧,回到你自己该去的地方!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同意这名妇女从事那项生意!’”这一局卢日科夫赢了,他马上转向第二个人,那个人要开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小店。
在合作企业运动开始几周的一个晚上,一位党的高层领导来视察,并坚持让卢日科夫“把那些来办合作企业的群众都请出去”。卢日科夫解释道,我们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让群众将不满意的情绪释放出来。“既然已经掀起了这场运动,”卢日科夫对领导说,“如果我们不积极引导,我们反倒会被这场运动吞没。”卢日科夫私下里害怕自己会以失败告终,合作企业将被挤垮,他也要遭受指责。合作企业者们可望开始自己的生意,可他们担心未来,他们需要从我这儿得到某种支持。“我尽自己所能鼓励他们,说实在的,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担忧。”
瓦莱里?塞金是市政府执行委会主席,卢日科夫的领导,他对卢日科夫说新生的合作企业商人们具有颠覆性和腐蚀性,他们或许会发展到公然表露与党的领导们进行对抗的地步。“显然,他们反对国家计划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对卢日科夫说,“我警告你:如果以后他们到市政府闹事,你就是那个和他们谈判的人!”
“我很愿意,”卢日科夫回答,“我要带上我最喜欢的帽子,走到阳台上,向他们挥手,就像当年列宁向去打内战的军队告别一样。” 塞金可没有被他的玩笑打动。
以后回忆开始时那风风火火的几个月,卢日科夫说晚上的会议可不全是官僚作风的工作方法,那是对搞市场经济的一丝感觉——人们渴望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国家服务。“和这些新商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他说,“我开始明白那些过去常常猜测的事情……”
阿纳托利·丘拜斯阿纳托利·丘拜斯(1)
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列宁格勒图书馆,内部采用巨大的柱廊结构,总共有28间阅览室、1700万册图书、30万件手稿和112万册地图,在这里工作的尼娜?奥金格知道装有禁书的那个特殊抽屉的具体位置。70年代晚期,年轻的奥金格是这个规模庞大的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她就蜷曲在那个抽屉旁边,翻阅里面的禁书。那些书主要是一些被苏联当局确认为对国家有颠覆性的西方图书,它们被放在一个密室,一间单独的、上锁的屋子里,当有外宾需要借阅时,才在一定的时间内放到那个特殊的抽屉里。任何人想要接近那
些书都必须填写很多登记表,并需要特殊批准。尽管那样,这些书还是经常莫名其妙地消失或者根本无法借阅。“对不起,现在借不了,”工作人员很可能会这样说,“图书馆正在修理。”
为什么那些特殊的书会神秘失踪呢?当局不会给出解释。他们把不允许人们阅读的图书妥善保存起来,这又是一件发生在“发达社会主义”体制下,令人不可思议的荒谬的奇闻。显然,那些书不可能完全被幽禁,因为一个自1814年建成后就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图书馆,不会承认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有关部门更愿意简单地决定把那一类书籍储藏起来。
那时,苏维埃人们的思想控制使人们更加渴求知识,作为年轻学者最爱光顾的图书馆——列宁格勒图书馆,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思想的空间。
在有高高天花板的社会和经济阅览室里,几个年轻的书目编辑知道图书馆内的所有藏书,从用藏语写的书籍到所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书目编辑们同情那些对禁书感兴趣的读者,一旦读者和他们建立信任关系,他们之间可以自由地交流任何事情。那些日子,读者称“列宁格勒图书馆”为“精灵聚集的地方”,这种说法不是指那些藏书,而是指聪明的书目编辑、图书馆管理人员和读者都聚在那里。他们静悄悄聚在一起阅读和小声争论,尤其是在吸烟室和有几张桌子的小餐厅。
克格勃侦察员和告密者也混杂在那些聚在一起讨论者中间,但没有人能明确地知道哪些是划了红线被禁止谈论的危险话题。这个政权已经向衰弱和病态方向发展,它那神话般的触角已经麻木,神经开始混乱。但仍然有某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制约着人们不敢高声谈论。列宁格勒之所以著名,因为拥有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克格勃部门。一次,一名研究员到图书馆借阅几本禁书。他即被告知,图书馆中没有这几本藏书。过了一会儿,借书人带着书目编号又返回来!他知道;他要借的图书就在图书馆里,只不过是被藏起来罢了。随后,克格勃人员开始展开调查,调查他从哪儿弄到的那些书目编号?
尼娜?奥金格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她观察那些进出图书馆的人。她身材不高,披着长长的浓密的红褐色卷发,一双调皮的眼睛会闪烁出热情的光彩,还会在严肃的气氛里黯淡下来,她对每天到经济阅览室的各种各样的读者的情况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很容易就回想起每个人的脸和他们的图书证号。她记得在读者群中,有个身材高大、英俊的年轻人,长着引人注目的浅红色头发,总是阅读与政治和经济有关的书籍。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利?丘拜斯。
对于那个时期年轻好学的学者来说,丘拜斯和他那一代人对克格勃存有敌意,不是因其无所不在而需要戒备,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注意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谈话方式。这种谨慎的态度已经习惯成自然,成了第二天性。他们周围的每一个地方都证明了这个体制在慢慢衰弱,工业运转和经济形式逐渐变得紊乱,领导层腐化堕落,自我吹嘘成风,但是年轻的学者们一直只用低声议论并且使用暗语。执政者所谓“完美的生产体制”早已暗淡无光,就像列宁格勒市中心马拉特大街9号的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的灰色外墙一样,年轻的教授丘拜斯就在这所学院执教。
在图书馆见过丘拜斯几面之后,奥金格也被分派到丘拜斯所在的学院工作。这不是她本人的选择,她本人不是党员,自认为是个自由思想家,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她在毕业后被党组织分配到死气沉沉的应用经济研究所工作。“经济研究所里都是些滑稽的人,”奥金格后来回忆当年时说,“对我来讲,仿佛一下陷入某种极端环境里,周围的人都是保守教条的意识形态专家!而我是一个进步的历史学家。”
阿纳托利·丘拜斯阿纳托利·丘拜斯(2)
这个学院有数以千计的苏维埃式的专家,据称都在解决勃列日涅夫时代悬而未决(没有解决)的众多问题,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在上千间小办公室里,布置着完全相同的浅色木头柜子,薄薄的窗帘,绿色塑料罩的台灯;教室中,黑板排成一条线,就着半杯茶水,苏联研究员们努力地寻找着“科学”地修复这台运转不佳的社会主义大机器的方法。研究员们恪尽职守地花了数年时间检查那些使苏联工业吱吱作响的齿轮,旨在找到推动它们前进、或者至少能阻止它们后退的办法。他们寻找一个“指导方针”、一条线索,指
望能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使钢铁生产量提高3%。每种产业,像机械制造业、煤矿开采业、农业、冶金业和其他十几种产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做相同的研究工作。成千上万的研究员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寻找其他方法,来衡量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经济生活中,许多研究员们知道,至少在心里猜测,他们寻找的完美的“指导方针”的探索是徒劳的。
奥金格到研究所工作不久,就赶上每年都得参加的强制性的秋季劳动,到一个集体农庄采摘西红柿。整个研究所人员都被派往列宁格勒最东面的一个郊区,起伏不平的泥泞道路只有乘拖拉机才能通过。乡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短暂的放松,使人们暂时摆脱学院研究会的折磨和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无休止的讨论。他们住在木制的临时工房里。白天,他们一起搬运笨重的木板条箱子,把摘下的西红柿从地里运出来,晚上他们唱歌、喝酒、聊天。新鲜的空气、疼痛和疲劳的肌肉,晒伤的肌肤、友谊的交流、浪漫的承诺,使他们变得精力充沛。
他们是轮班到农场工作的。奥金格很快就认出另一个组中的丘拜斯。他体态挺拔,相貌英俊,脸色在激动和生气时都会在瞬间变红。他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年轻人,一个有责任感的天生的领导。他是一个正派、严谨、充满自信的人。
回到学院,他继续进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研究”工作。据奥金格后来回忆,丘拜斯不是保守的经济学家,但他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总是勤勉用功,是深受老教授喜爱的学者。他很早就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在学院中这也是很不寻常的。他用温和但不屈服的微笑就把追求他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