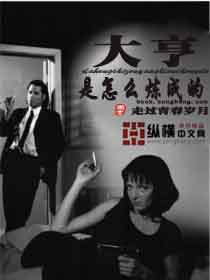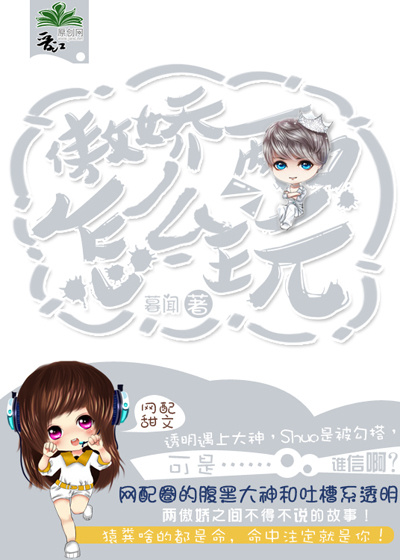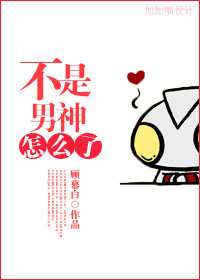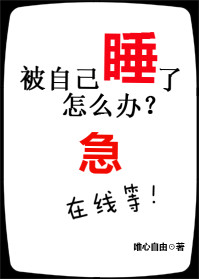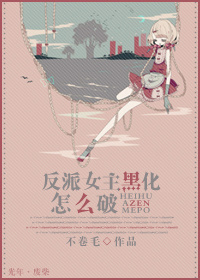怎么办?-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就提到那件使他认为必须跟我结识的事情上来。我们谈了半个来钟头。谈的什么这倒无关紧要,我只讲一点就足够:他说“您必须这样”,我说“不”,他说“您应该如此”,我说“完全不必”。过了个半小时,他说道:“继续谈下去显然也是徒劳无益。您不是相信我这个人绝对值得您信任吗?”“是啊,大家都对我这么说,现在我亲眼看到了。”“您仍然坚持您的意见?”“仍然坚持。”“您知道该从这儿得出什么结论?您不是撒谎专家就是大坏蛋!您看竟然有人这么说话呢!如果别人对我讲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对待他?恐怕会提出决斗吧?但是他的语调中没有丝毫的个人情绪,他犹如一位历史学家,冷静地下判断不是为了贬损谁,而是为了坚持真理,加上他的样子又那么怪异,你若生他的气就太荒唐了。我只能一笑了之。“撒谎专家和大坏蛋原是一样的啊。”我说。“这一次并不一样。”“这么说,也许我既是撒谎专家又是大坏蛋吧。”“这一次不可能二者兼备。不过两者必居其一:也许您想的、做的和您嘴巴说的不是一码事,那么您就是个撒谎专家。也许您想的、做的确实跟嘴巴说的一个样,那么您就是个大坏蛋。两者必居其一。我认为您是头一种。”“您乐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继续笑着说。“再见。无论如何,您要知道,我还对您保持着信任,并且愿意恢复我们的谈话,您什么时候乐意都可以。”
①暗指革命活动。
虽然这件事不合情理,拉赫梅托夫却是完全对的:他这样开始是对的,因为他先把我的情况打听清楚了,然后他才开始行动。他这样结束谈话也是对的,我跟他说的确实不是我心里想的,他确实有权叫我撒谎专家,用他的话说,“这一次”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委屈,甚至也没有觉得面子过不去,因为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而他也确实仍旧对我保持着信任,或许还有敬意。
是的,尽管他的态度不合情理,大家仍旧相信拉赫梅托夫的行动正是最为明智、最为利索的行动。他说话时,言辞之激烈,斥责之严厉简直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但是最富理智的人听了也不会怪罪他,他虽然异常粗暴,心地却是非常温和的。他的开场白大致是这类话每逢他解释一个棘手的问题时,总是这样开始:“您知道,我讲话丝毫没有个人情绪。如果我的话听了不顺耳,那么请您原谅。但我认为,凡是认真负责的肺腑之言,您听了都不该见怪,因为那毫无侮辱人之意,而只是出于需要才说。不过,只要您觉得继续听我说下去没有用处,我马上就停止说。我的原则是:“该提出自己的意见时我总要提出的,但绝对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真的不强加于人。当他认为必须对您说出他的意见的时候,您是决计不能不听的,他一直要说到您对他讲的事情和他的用意理解为止。但是他用两三句话概括说明之后就会问您:“现在您已经知道谈话的内容是什么,您认为进行这样的谈话有用处吗?”假如您回答“不”,他便欠欠身走开了。
他就是这样说话行事的,他的事情多得没底,却全跟他私人无关,他根本没有什么私事,这谁都知道。可是他到底有什么事情,圈子里的人也不知道,只见他忙个没完。他很少在家,老是跑来跑去,四处奔波,步行的时候多。而他家里也断不了人,有一些老朋友,也有不少新相识。因此他给自己规定两点到三点之间总要在家,好利用这段时间谈。工作和吃午饭。但是他常常几天几天地不在家。那时就由他的一位朋友待在他家里替他接待来访者,这人对他绝对忠诚,却总是缄默无语,犹如一座坟墓。
我们看见他坐在基尔萨诺夫书房中阅读牛顿对《启示录》的解释以后,约莫已过了两年光景,他离开了彼得堡,他告诉基尔萨诺夫和其他两三位密友说,他在这儿再也无事可做,能做的他都做了,再过三年左右他才能再有事可做,今后这三年是他的空闲时间,他想着利用这段间。采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来给未来的活动做些准备。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曾经返回他原先的田庄,卖掉了他留下来的土地,得到三万五千卢布,上了一趟喀山和莫斯科,把将近五千卢布分发给了那七名受他接济的学生,好让他们能够完成学业。从此他的这段真实可信的故事就结束了,至于他离开莫斯科以后的去向,那谁也说不清了。在他失去音讯的几个月里,比大家更多了解他的人也不再为他保密了,把他在我们中间生活时按照他的要求一直没讲过的事情都透露出来。我们圈子里的人这才知道有好几名学生靠他接济,才知道了我上面讲过的有关他私人方面的大部分的事情,还知道了许多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远没有把一切解释清楚,甚至什么也没有解释明白,只是将拉赫梅托夫描绘成一个使我们这圈子人都感到更为神秘不解的人物。这些故事或者以其怪诞离奇而令人惊诧不已,或者跟圈子里的人对他的看法完全相悖,我们总认为他对儿女私情十分冷漠,他没有一颗属于他个人的心,能为私生活的体验而怦然心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此处把所有这些故事都讲述出来显然不得体,只引用其中的两个,两类当中各引用一个:一个属于不合情理的一类,另一个是跟圈子里的人原先对他的看法相悖的一类。我从基尔萨诺夫所讲的故事中来挑选吧。
在拉赫梅托夫第二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离开彼得堡之前一年,他对基尔萨诺夫说道:“请给我大剂量的治刀伤的创口贴药膏。”基尔萨诺夫给了最大的一罐,他以为拉赫梅托夫要把这药送给本工作坊或其他易受刀伤的工匠的作坊。第二天早晨,拉赫梅托夫的女房东惊恐万分地跑来找基尔萨诺夫,说:“医生老爷,我不知道我那位房客出了什么事啦:他的房门上着锁,半天不出来,我往门缝里一看,他整个儿人倒在一摊血里。我喊起来,可他隔着房门对我说:‘没关系,阿格拉费娜·安东诺夫娜。’什么没关系!救救他吧,医生老爷,我怕出人命啊。你知道,他对自己下毒手。”基尔萨诺夫急急忙忙赶去。拉赫梅托夫打开房门,开朗地微笑着,笑中有一丝苦涩,基尔萨诺夫看到了一件不止会叫阿格拉费娜·安东诺夫娜惊奇无奈的怪事:拉赫梅托夫整件内衣(他只穿一件内衣)的后背和两侧衣襟都沾满了血,床底下有血,他睡的毡褥子上也有血。原来毡褥子上扎着几百枚小钉,钉子帽向下,钉子尖朝上,从毡褥子下面伸出将近半俄寸长,拉赫梅托夫在这些小钉子上躺了一夜。“这是怎么回事?哪能这样干,拉赫梅托夫?”基尔萨诺夫惊恐地说。“一个试验。需要这样。当然是不合情理,可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我看我能吃得住。”足见除了基尔萨诺夫看到的之外,女房东大概还可以大量地讲出拉赫梅托夫种种奇闻边事来。但是这位心地纯朴、衣着寒酸的老太太疼爱他,简直达到发疯的程度,从她那儿当然什么消息也得不到。就是这一次她跑去找基尔萨诺夫,也完全是拉赫梅托夫自己让她去的,好叫她放心:她以为他是想自杀,竟痛哭不已。
过了两个来月,拉赫梅托夫有一个星期或者一个多星期下落不明,可是当时谁也没理会,因为失踪几天在他并不罕见。这是五月末的事。现在基尔萨诺夫讲出了下面的故事,讲明拉赫梅托夫怎样度过这许多天的。这是拉赫梅托夫生平的一段爱情插曲。恋爱来源于一起事故,这起事故足以表明他不愧为尼基图什卡·洛莫夫的称呼。一天,拉赫梅托夫从帕戈洛沃一村步行进城,一边走一边沉思,照他的习惯,眼睛多半望着地上。走到林学院附近,传来一个女人的绝望的惊叫声,他一下子从沉思中猛醒过来。他一看,一匹马驾着一辆轻便车飞奔过来,车上坐着一位太太,她自己赶车,却驾驭不住了,缰绳拖在地下,那马离拉赫梅托夫只有两步远了。他奔到了路当中,可是马已经从他身边飞驰而过,他没能抓到缰绳,只来得及扳住马车的后轴,把车子煞住了,可他也跌倒了。人们跑来帮太太下车,扶起拉赫梅托夫。他的胸部有好几处伤,主要的是车轮刮掉了他腿上一大块肉。太太清醒过来以后,派人把他送往自己的别墅,别墅离出事地点不过半俄里远。他也同意了,因为他感到虚弱无力,但是他要求一定去请基尔萨诺夫,不请任何其他的医生。基尔萨诺夫认为胸部的受伤处虽不要紧,但却使得拉赫梅托夫失血过多而虚弱不堪。他躺了十来天。那位被救的太太当然亲自看护他。他虚弱得任什么别的事也不能做,只能跟她谈谈天,反正这段时间也是白费了,两人越谈话越多,谈兴越浓。太太是一位十九岁左右的寡妇,一个聪明、正派,不算贫穷,一般来说完全能够自立生存的女人。拉赫梅托夫那些火一般的话语当然没有涉及爱情,但却使她听得入了迷,“我梦见他被光轮环绕着”她对基尔萨诺夫说。他也爱上了她。她从他的衣着和种种方面看,认定他是个身无分文的赤贫的人,因此当他在第十一天起床下了地,说是可以回家去的时候,她便酋先向他表白爱情,并且提出结婚。“我对您比对别人更加坦率。您看,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的命运跟我自己拴在一起的。”“对,这是实话,”她说,“您不能结婚。不过您还是可以爱我到必须离我而去时。”“不,我连这个也不能接受,”他说,“我应该抑制住我心中的爱情。对您的爱会拴住我的双手,就是不恋爱,我的手也不能很快地松开,已经给拴住了。但是我一定要松开,我不应该恋爱。”这位太太后来怎么样了?她的生活应当发生一次转折,她大概自己也变成一个特别的人了吧。我本想打听的,可是我至今还不知道,基尔萨诺夫没有把她的名字告诉我,他自己也不知她的下落。拉赫梅托夫请求过他别再跟她见面,也不要查问她的情况:“如果以后我猜想您会知道她的什么消息,我就忍不住要问起您,而这样做又不妥。”听到这个故事,大家才回忆起来,当时拉赫梅托夫有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也许两个多月比平日更加阴郁,无论人家怎样指责他那可恶的弱点,即抽烟,他也不再激昂慷慨地埋怨自己,人家用尼基图什卡·洛莫夫的名字讨他欢心,他也不再有那开朗甜蜜的笑容了。我记起了更多的事:我们初次谈话后没多久,他就喜欢上了我,因为我跟他单独相处时总爱跟他开个玩笑。那个夏天,他跟我谈话有三四次之多,在回答我的玩笑话时,每次都情不自禁地说出这样的话:“好,可怜我吧,因为我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渴望生活的人啊。”接着又补充道:“算了,没什么,会过去的。”事情也确实过去了。可是有一次,在深秋季节,我跟他开玩笑过多,深深地触动了他,又引发他说出了这几句。
敏感的男读者也许由此而推论道,我对拉赫梅托夫的了解比我说出来的要多。也许是这样,我不敢反驳他,因为他很敏感。假定我知道得多,可是我知道的,而你,敏感的男读者,永远不会知道的事难道还少吗?不过,我真的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如今拉赫梅托夫在哪儿?他的情况怎样?有朝一日我还能否再见到他?关于这些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或推测,也就是掌握他的所有的熟人知道的那些情况。他离开莫斯科之后有三四个月下落不明,我们大家猜想他是到欧洲旅行去了。这种推测看来是对的,至少可以由这件事证明:拉赫梅托夫失踪后一年,基尔萨诺夫的一位熟人在从维也纳开往慕尼黑的火车上碰见一个俄国的年轻人,他自己说曾游遍各斯拉夫国家,所到之处跟各个不同的阶级接触,每到一国都要停留下来,以便充分了解当地居民中全部主要成员的观点、习俗、生活方式、生活设施以及富裕程度,为此他在城市里住过,也在乡下待过,常常步行着走村串乡,就像结识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那样,乘车或步行游历德国北部,由此再到南方,进入到奥地利境内使用德语的各省份,现在他正在往巴伐利亚去,接着到瑞士,经过符腾堡和巴登入法国,同样遍游法国后到英国,这还要花上一年的时间。如果这一年还有富裕的时间,他就去看看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如果时间不够,也就做罢,因为这并不那么“需要”,他“需要”考察的是上述的那些国家。为什么?“为的是加以对比”;再过一年,他无论如何“需要”到美国去,他更“需要”研究美国,这比研究任何其他国家更为迫切。他将在那里长住一段时间,也许一年多,也许就定居了,如果他能在当地找到事情做。但是再过三年左右他大概会回到俄国的,因为看来,不是现在俄国“需要”他回来,而是过三四年之后才“需要”。
这一切都很像拉赫梅托夫,就连叙述者头脑中储存的那么多的“需要”也很像他的口气。就叙述者所能记起来的,那旅客的年龄声音、外貌都跟拉赫梅托夫很一致。不过叙述者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自己的旅伴,况且相处的时间也不长,总共才两小时:他是在一个小城上的车,到一个村庄就下去了。因此叙述者只能用很一般的话来描述他的外貌,不是完全可信的:这多半就是拉赫梅托夫,但有谁知道他呢?也没准不是他呐。
还有一个传说,说有个俄国的年轻人,本来是地主,他去拜访十九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新哲学之父、一个德国人①,并对他这样说道:“我有三万泰勒②,我只需要五千,其余的请您拿去用吧。”(那位哲学家生活十分贫困)“因为什么?”“好用来出版您的著作。”哲学家自然没有拿,但那俄国人好像还是用他的名义把钱存进了银行,然后给他写信说:“请随意支配这笔钱吧,即使把它扔到水里,这钱您已无法退还给我了,您不可能找到我了。”这笔钱好像至今还存在银行里响。假如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么毫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