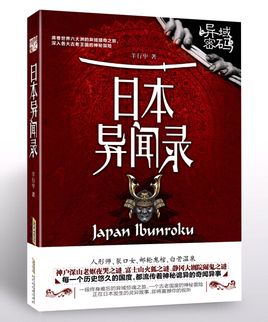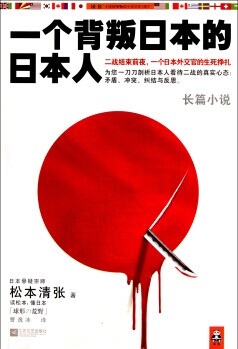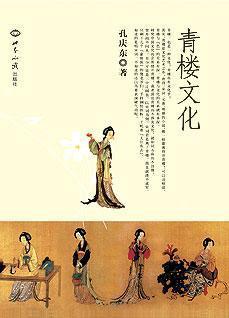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支那国民性研究”(3)
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理论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正明显走向失败的1943年出笼的,因而书中处处流露出了对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恐惧和无可奈何的心态。他从战争现实中总结出的这些“支那国民性”,当然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而且,与其说他总结的是“支那国民性”,倒不如说他很好地总结了日本的国民性。要问在侵华战场上“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妄自尊大”的究竟是谁?历史早已经做出了回答。在日本败相毕露时,却扬言“攻入重庆和昆明,彻底地把蒋共歼灭”——岂不正是暴露了大谷孝太郎们的“歇斯底里”、“妄自尊大”吗?!
最后,还有一位名叫杉山平助(1895~1946)的文学评论家所写的《支那、支那人与日本》一书,也值得一提。杉山平助在七七事变后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被派往中国前线采访,这本书是杉山平助在华北各地观察采访而写成的随笔文集。其中,有一组文章题为《论支那人》,对中国人及其国民性问题的议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辱骂,集中代表了当时一些日本文人在目睹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后而产生的一种气急败坏的心态。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
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
在这种心态下,他“挖支那人的灵魂”的办法其实就是辱骂。他认为中国的古典和文化虽然伟大,但几经亡国,早已没落,体面和自豪丧失殆尽,“他们在性格中的某些地方含有高贵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却是怪癖的、变态的、阴暗的、受虐的”;“从总体上看,他们不过是一个老废的民族而已。我们所敬畏的古代支那人,和今天的支那人毫无相似之处”。杉山平助尤其对中国人的“自尊”感到难以忍受。他说:“支那人开口闭口轻蔑地说日本没有固有的文化,一切都是模仿的,是从自己的祖先这里传去的。然而,他们所引为骄傲的文化,不过是几千年前的人留下来的糟粕。”他写道:“像支那人那样,具有那么强烈的自尊心,除了惊叹之外没有办法。假如我们这样想:此次日本军队大振武威,打击他们,会使他们觉醒来,尊敬日本吧?可是这样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今天,他们从心底里仍然顽固得很,深信自己和日本之类的国家比起来要优秀得多,所以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是瞧不起日本人的。” “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早一点看透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把中国人与日本的性格做了一番对比,说:“正直、性急、喜怒形于色的阳性的日本人,面对富有耐性、口是心非的阴性的支那人,在搞阴谋方面绝对会败给他们。在支那人眼里,日本人简直就是黄口孺儿”;“古典支那人的优秀的头脑,到了现代支那人就变成了可怕的罪恶”。杉山平助一方面认为日本人在智谋方面不是中国人的对手,提醒日本人小心,一方面又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他说:“最初我错把他们的性格看得坚硬,而后来我才明白事实上支那民族的动脉已经硬化了,是交织着老年的狡黠和冥顽的那种硬化。看起来是强硬处,实际上是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妨碍生命的癌变。”为此他提出,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性格,日本在战术上应避实就虚,既然“玩阴谋”玩不过中国人,那就在军事上狠狠打击他们;既然中国人不会从内心屈服,那就只有彻底战胜他们。他在该书前言中叫嚷:“抛弃优柔寡断的态度,转为积极的进攻。”
杉山平助并不是中国问题及“支那国民性”的研究者,而只是一个肆意放言的文学评论家。他在中国转了一圈后,被中国人民的英勇顽强的抗战所激怒,于是就有了上述的气急败坏的詈骂。但杉山在“支那国民性”的评论中颇有代表性,他的言论表明,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支那国民性”的“研究”,与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支那人”及其性格的詈骂,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所谓“思想战”“宣传战”或“思想宣传战”(1)
侵华战争中,日本一些学者文人在纳粹德国战争理论的启发下,杜撰出了“思想战”、“宣传战”、“思想宣传战”之类的概念。许多学者文化人著书立说,对“思想战宣传战”问题作了系统的阐发,提出了对华“思想宣传战”的种种理论、战略和方策,还有许多文化组织与机构也全力投入“思想宣传战”问题的研究,《大陆的思想战》、《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之类的书陆续抛出。同时,日本军国当局加强了对国内的思想统制和舆论宣传的控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宣传问题的“大纲”、“纲要”之类的文件,操纵和统制了全国舆论。在官民共同运作下,日本的所有舆论媒体机器都开足马力,对华“思想战”、“宣传战”可谓轰轰烈烈。
一、所谓“思想战”、“宣传战”或“思想宣传战”
日本悍然全面侵华之后,虽然迅速占领了中国许多地区,但在军事侵略取得进展的同时,中国的抗日斗争却越来越广泛和激烈,日本军队深陷于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汪洋大海中不能自拔;而且,日本侵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其野蛮非道的行径,遭到了中国人民及世界各国的一致声讨,因而在道义上就首先已经失败了。中国人的抗日斗争为何如此顽强?中国人民为什么排日抗日?此战出师何名?如何使中国民众放松或停止抗战?如何争取一些中国民众协力战争?为解决并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批批的学者文化人潜入中国沦陷区,展开调查研究。这些人看到了军事侵略并非万能,而要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目的,仅靠烧杀抢掠的“三光”作战政策并不奏效,然而他们却以侵略者的固执与偏见,普遍将日本在道义上失败的原因归于日本宣传不力,归因于中国抗日宣传的“巧妙”,从而强调今后要加强对华“思想宣传战”。例如,曾任陆军省情报部长的清水盛明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写了一篇题为《参考·对外宣传和日本的国民性》的文章,一开头就说:
此次事变中我国的对外宣传不及支那,不仅没有将帝国的真意让列国理解,甚至皇军连战连胜的成果,也常常被支那的谣言宣传所打消。尽管在武力战方面取得了赫赫战果,但在思想宣传战方面却连连败北,这不仅是帝国上下的痛事,也让对我国抱有好意的外国人连声慨叹。
清水盛明所言可能是事实,但他对个中原因的分析却十分荒谬,他认为是武士道的奉行的所谓“不言实行”的国民性使日本人不善于或不愿意宣传。他看不到日本在宣传上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是侵略者。正如一条狼一边撕咬猎物,一边宣传自己是多么善良,会有什么效果吗?清水只是强调思想战的重要,认为“随着事变进入长期化,今后的武力战要被经济战、思想战所取代而在战争中占主要地位”,日本必须制定宣传计划、建立宣传机关、加强思想战研究、培养思想战人员。
还有一个叫伊佐秀雄的人,七七事变后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对中国的抗日宣传做了一番调查,回去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支宣传战》(原载《改造》20卷8号)的文章,其中的看法也颇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的抗日宣传是“有组织的”,认为蒋介石的宣传做得无孔不入,明明北京、天津、太原、青岛等重要城市纷纷陷落,特别是连首都南京都被攻陷,在“惨败”面前,中国方面却宣传什么“我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即使全国都化为灰烬,在灰烬中也会爆发出复兴的光热和力量,必定能够求得中国光明的前途;只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确保主权、才能实现民族与国家的永存”云云。伊佐秀雄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不认输,就在于中国政府的宣传,在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本来就有“夜郎自大”的“自负”心理,“连像猪一样生活的苦力都以他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而沾沾自喜,目不识丁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等的国民”。伊佐认为,蒋介石的这种宣传正好切合这种民族心理,“使得这种宣传也渗透到最下层的老百姓中,他们在日本占领区域为日本人拉洋车,累得汗流浃背,心里却在蔑视日本人”。伊佐描述了中国抗日宣传的巨大效果,说他最近在中国搞到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材料,他发现在中国,抗日教科书和抗日剧本充塞学校,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抗日展开,整个国家同仇敌忾。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有效地对付中国的抗日及抗日宣传,日本许多学者文化人著书立说,就对华“思想宣传战”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并提出了对华“思想宣传战”的种种理论战略。还有许多文化组织机构也全力研究“思想宣传战”问题,如名为“精神科学研究所”的一家研究所,集中研究所谓“大东亚战争下的思想战略”问题,先后推出了《大东亚战争下的思想战略草案》(全五卷)和《大东亚战争下的思想战略》(全五卷),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对华“思想战略”;连“社会教育协会”这一名堂的协会也在研究对华文化侵略问题,推出了《支那事变和文化工作》、《围绕支那的文化战》和《大东亚战争和思想战》等一系列书籍,极力鼓吹对华“文化战”和“思想战”。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所谓“思想战”“宣传战”或“思想宣传战”(2)
日本的“思想宣传战”的理论,表面上看是对世界历史上的历次战争中思想宣传所起的重要作用的总结,但实际上,其主要理论和灵感的来源是纳粹德国的战争宣传。德国在“一战”中失败后心有不甘,许多军人和文人对失败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军事,而在宣传。鉴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与德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德语在日本一直是第一外语,因而日本军部及一些学者对德国人在战后出版的总结“思想宣传战”经验教训的书倍加重视。1938年,原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副参谋长鲁尔道夫的《国家总力战》(1934)被译成日文出版,对日本的思想宣传战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上述伊佐秀雄在《日支宣传战》一文中认为,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主要是因为宣传做得不好。他援引希特勒(时任德国总理)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话,并表示强烈共鸣,希特勒的话是:“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被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假如宣传这种东西本身被理解其意义的人所掌握,它就会成为可怕的武器。”在纳粹德国的影响启发下,日本学术文化界的许多人著书立“说”,把“思想宣传战”看成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英文的propaganda(宣传、鼓吹)有意识地译为“思想战”、“宣传战”或“思想宣传战”,并对“思想宣传战”在历次战争中的运用情况,对其地位、内容、方式方法和目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述。从1937年起,这类专门的著作陆续出笼。据笔者所掌握的不完全的材料,主要的著作有水野正次的《总力战和宣传战》和《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思想战纲要》(1942)、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1942)、田中丰的《战争和宣传》(30年代末)、井上哲次郎的《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39)、竹田光次的《大东亚战争和思想战》(1943)、奥村喜和男的《大东亚战争和思想战》、鹿子光信的《大东亚战皇国思想体系论》、小西铁男的《思想宣传战》、精神科学研究所编辑的《大东亚战争下的思想战略草案》、国策研究会的《大东亚战争文化体制论》(1944)、华北宣传联盟编《蓦进华北的剿共·思想战体形的确立》(1942)、社会教育协会的《大东亚战争和思想战》和《围绕支那的文化战》等等。同时,侵华日军有关方面也在吸收相关建议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思想战”的计划,如“北支那方面军参谋本部”在1940年5月出台了一份文件,题为《极密·在华北的思想宣传战指导纲要》,就“思想战”的各个方面,如宣传、教化、民众组织、情报搜集、对中共等抗日“思想策动”团体图22丸山学《大陆的思想战》卷首插图的剿灭、对抗日集会、结社、言论、著作的取缔等等,都分章节做了具体的部署和规定。
这些五花八门的关于思想宣传战的专著,都从各个方面为日本的对华侵略制造理论根据,千方百计地将日本发动的战争“正当化”,如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东京:目黑书店1942年版)一书,从“文化学”的高度,提出了“战争就是异质文化的相克”、“没有文化的地方不会发生战争”的论断。他强调:
有人说战争破坏文化,那是肤浅之论。异质文化相接触的时候,处于优势的一方对处于劣势的一方进行吸收、抱合,对于提升人类文化是自然的、必要的。没有它,人类文化就不能进步。所以,战争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这种行为与清除一座陈旧碍事的建筑物、建设新的雄伟建筑物的行为很相似。作为清理的手段必然伴随着破坏的现象,但只以这一点来观察战争是从前的所谓和平主义者的战争观。(《大陆的思想战》第2页)
从一般原理说,战争无疑具有摧枯拉朽的正面作用。但丸山学完全模糊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他所指的战争,具体就是指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他力图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加以“文化”化,把烧杀抢掠行径说成是“文化的攻势”,说成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从而为日本的侵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