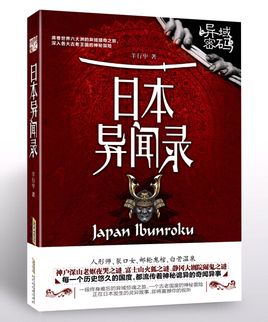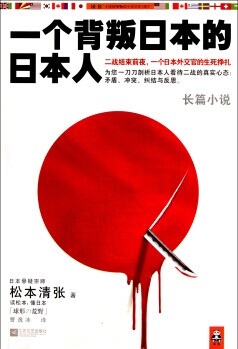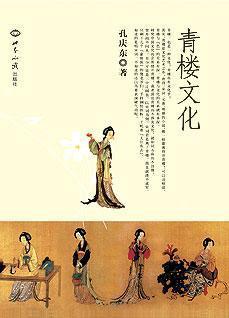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号上还有《蒋政权下在内地出版的“救亡新书”》,并把这些书分五类胪列,其中包括“主张抗日抗战的书”、“关于战时教育及战时训练的书”、“关于战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书”、“关于国外问题的书”、“关于战时文化问题及文艺问题的书”等,并对这些书的发行范围做了推测。
在第十四号上,有《“孤岛”上海文化界的动向》、《维新政府统治下的各地报纸的概况》、《蒋政权教育部的诸设施及其办法》等文章。
在第十五号上,有《现住北京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录》(计七百七十四名),每人以一百来字的篇幅做了介绍。
在第十七号上,有《京津文化界一瞥》,并附《国立、部立各院校概况总表》、《国立、部立各院校学生人数统计表》、《国立北京大学概况表》、《国立、部立各院校教职员状况统计表》、《国立、部立各院校教员等级及学历统计表》、《国立、部立各院校学生状况统计表》、《北京特别市私立各校馆概况统计表》、《天津特别市公私立各级学校统计》等。
第十八和十九号上,则集中介绍英国、美国对“蒋政权”的教育文化援助问题及“蒋政权”的国际文化合作问题。
从第十八号起到二十号,分三次连载《现存的教育、研究及其他一般文化机构地方别一览表》,内容极为细致具体,包括名称、科别、地址、创立年月、附设机关、备注等内容。
第二十四号头条是《上海教育界的动向和“学潮”问题》,分析了其中的抗日学潮的起因,认为是“蒋政权和共产党方面的煽动所造成”,并将历次学潮(达四十余次)列出表格,包括“学校名”、“学潮的原因”、“学潮的经过”三项。
第二十七号刊载《中国的研究机构及学会、协会等的近况》,搜集罗列了日占区及香港一百四十多个研究机构。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其他形形色色的对华情报组织(2)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号连载《重庆方面的文化机构的现状》,对非日本占领区的公立、私立及共产党方面的大学、学院、专科学校、学会、协会、研究院所、图书馆、博物馆等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
从以上简单介绍的内容可以看出,日本的这个“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已经全面地搜集并掌握了中国各地——特别是沦陷区,也包括部分中国的大后方地区的文化情报,有的情报还十分细致具体。日本对华情报搜集的无孔不入,整理与研究的细致缜密,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仍令人惊叹并发人深省。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机构除上述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外,还有“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1931年4月设立),主要是搜集和保存有关中国文化的图书资料。
“东亚经济调查局”,成立于20年代中期。这个调查局的情报搜集范围不限于经济,而且对中国的政治动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排日、抗日局势,也非常关注。在这方面它编辑出版了《支那排日教材集》(1929),将中国的中小学教材中有关排日的内容收集在一起;还出版了《转向满蒙的排日运动》(1929)、《支那国定排日读本》(1931)等书。通过集中报道中国的排日,极力向日本国内煽动反华情绪。此外该调查局所编写的《满洲读本》,向日本国内介绍了满洲的情况和日本人在满洲的经营,鼓吹对满洲的扩张,在十几年中多次再版,在日本读者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东亚研究会”,成立于20年代中期,实际上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文化问题。该研究会成立后最大的“业绩”是长期连续举办“东亚研究讲座”,以连续出版物的方式陆续出版。到1943年,共出版一百一十辑。每辑均有一个专题,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文艺、社会、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有些讲座则密切服务于侵华战争的时局,如第九辑是《应该如何应对支那》,第四十三辑是《中国共产党概观》,第九十九辑是《重庆抗战力的概观》,第一百○一辑是《美国援助重庆的全貌》,第一百○三辑是《国民政府的清乡工作》等。兹以1932年出版的“东亚研究讲座”的第四十六辑《支那的排日运动》一书为例略加评析。《支那的排日运动》由波多野乾一著,收集并分析了中国排日及排斥日货的各种情报,书中列举了中国历次排日及排斥日货的来龙去脉,认为到当时(1932年)为止一共有九次大的排日浪潮:第一次是1908年的“辰丸事件”(即日本船非法停泊中国领海事件——引者注),第二次是1909年的安奉铁路线改建事件,第三次是1915年的“日支交涉”事件,第四次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五次是1923年的中国要求“收回旅大”而被日本拒绝事件,第六次是1925年的“五卅”事件,第七次是1927年日本出兵山东事件,第八次是1928年的“济南事件”,第九次是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在叙述历次排日运动的时候,作者刻意淡化日本对华侵略是造成中国排日的主要原因,而刻意强调中国人历来有排外的传统;分析了排日、抵制日货给日本带来的损害,却刻意淡化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坏。该书最后还提出了三条对策,第一是“确立强硬的外交方针”,第二是“恢复与列国的协调”,第三是“绝对禁止支那的反日教育”。波多野乾一的这本书正好出笼于伪满洲国建立的时候,书中罗列的中国排日的情报及他本人所做的对策分析,对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政策走向不能说没有影响。
《支那的排日运动》是以“研究会”的名义刊行的个人著作。对于日本政府和军方来说,这类书及其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所以政府和军部自己也搜集并出版了一些类似的东西。这里只举一本书为例,就是日本政府的“陆军省”于1931年刊印的题为《关于支那的排日侮日》,这本小册子未署作者,也没有版权页,只在封面上写着“昭和六年九月,陆军省”几个字,可见此书属于当时的陆军省的内部情报资料。该书列出了一个长达五十多页的表格,题为《排日侮日不法行为的事例》,分“事件名称”、“场所”、“时间”、“事件概要”四项内容列表,总共达一百一十八条。书后“附录(一)”是《最近一般青年广泛购读的书籍一览表》,列出的图书有:《日本侵略满蒙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帝国主义问答》《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国耻史概要》《不平等条约问答》《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痛史》《日本蹂躏山东痛史》《日本侵略下之满蒙》《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土地丧失史》《不平等条约》《中国国际条约义勇论》《中国国耻史略》等,共十六种。还对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排日内容以图表形式加以罗列。在“附录(三)”中列出了当时中国流行的“排日歌曲”,并译成了日文,包括《国难歌》《国民革命歌》(三首)、《国耻歌》《抗日运动歌》《忍耐》《打倒帝国主义》等。可见,当时,日本军方在中国搜集的相关的文化情报,也达到了十分细致入微的程度。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其他形形色色的对华情报组织(3)
随着对华情报搜集热潮的兴起,日本在中国兴办的新闻社及报纸,也成为在华情报机构的一种。如1934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通信社”是一家有着日本军部和外务省背景的通信社。值得注意的是这家通信社没有按当时日本的一般习惯叫做“支那通信社”,而是叫做“中国通信社”,不称“支那”而称“中国”主要目的也许是因为“中国”这一名称有利于它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中国通信社”以“对支那情况的迅速、准确的报道”为宗旨,成立后,编辑发行了《支那情报》(半月刊)、《中国通信资料》(半月刊)等。其中,在《中国通信资料》第五十八号、六十九号和七十号上,连续发表了有关中国“抗日真相”的材料,为七七事变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起了一定的煽风点火的作用。
对华情报搜集与研究的时兴,使得民间私人也宣布成立有关机构。例如,1925年,一个叫森长次郎的人宣布成立“中支经济调查所”。这是一个由个人名义成立的一个文化情报机关。森长次郎20年代在中国武汉滞留并从事经济商业活动,当年武汉地区以抗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占领旅顺而展开了声势较大的抵制日货的排日运动。这些排日运动对日本的对华扩张起了一定程度的阻遏作用,也引起了日本上下的关注。在此情况下,森长次郎决定成立“中支经济调查所”,对“中支”的情况做调查研究。他在谈到自己建所宗旨时写道:
先前伊集院氏在担任支那公使的时候说过:“日本如果不改良地图,就无法明白支那之大。的确,整个的支那之广阔,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能力。此前的日本人,无论是政治家、实业家、学者还是军人,都想把支那整个儿地放在菜板上,或者企图将它放在菜板上,结果就好像蚂蚁在面包上爬来爬去,只不过左右往返而已。我自身也是如此。我反省自身的同时,也为这些感到可惜。反省的结果就是决定建立“中支经济调查所”,目的是在支那的研究方面具体、深入而且细致。
老实说,只是支那中部,已经令我有望洋之感。相信也许终其一生也难以尽知。明知有局限还如此标榜,也是希望它的波纹向外一圈圈扩大,并尽可能地向外扩大。
这个调查所,有我个人只是“单枪匹马”而已,并无太多的预期,只是想从身边开始,或许会有一些收获,并乐于公诸于众。我相信我的支那调查研究,绝不是一家、一个公司或一地方的私事。(《支那排日谭》书后)
森长次郎及其“中支经济调查所”第一个“业绩”就是写了一本《支那排日谭》(上海日本堂1925年2月出版),这本书搜集了武汉地区排日方面的种种情报,包括排日思想的根源、排日组织、“支那人的日本观”、排日宣传、排日与支那官方、与英美的关系、排日的影响等等。情报来源主要是当地的报纸、书籍,再加上他的所见所闻。他分类罗列这些材料,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析评论,得出的结论当然完全是荒谬的。例如他认为中国民众的排日是受军阀的蛊惑煽动所致,中国人的排日是基于“自大思想”和对日本的“嫉妒心”等,都是些陈词滥调。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七七事变后各种对华情报活动的活跃(1)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对中国文化情报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加重视。除了政府及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团体、学校、协会、研究会从事中国文化情报的搜集活动之外,各新闻社都相应地成立了“调查部”,以利用自己的传媒优势进行对华情报搜集。如《朝日新闻》社在1937年后,成立了“朝日新闻社东亚问题调查会”、“朝日新闻社中央调查会”、“朝日新闻社调查部”等情报机构,并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告书。《读卖新闻》社编辑局1937~1938年间则连续出版了《支那事变实记》共十五辑。
某些学者文化人也对搜集中国文化情报、并以此服务于日本的占领而乐此不疲。有关文化情报机关越来越多,除了上述的“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调查部”等以前建立的机构组织更加活跃外,还有一些新的团体组织纷纷出笼。诸如“东亚研究所”、“日满支拓植文化研究所”、“大东亚问题研究会”、“东亚调查会”、“大东亚文化协会”、“国策研究会”、“大东亚问题调查会”、“东亚思想战研究会”、“国民精神研究所”等等,其共同目的都是协力侵华战争,为日本如何长期占领中国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出谋划策。有些团体组织从名堂上看似与对华问题无关,如“精神科学研究所”、“国民教育研究所”之类,实际上也在积极从事着对华文化侵略。
其中,“东亚研究所”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1938年9月)成立的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对华情报与研究机构。当时的近卫首相出任该研究所的总裁,可知该所是官办的情报机构。据《东亚研究所报》第一期载,近卫在“东亚研究所”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处理当今之支那问题,谋划将来东亚之大计,是日本国民的重大使命。而研究此种形势的机关组织尚不完备。为了依据科学性的研究来确定国策,就要集中精锐之学者,推动官民之协力,作为帝国最初之尝试,特创立东亚研究所。”企画次长青木对研究所的情报调查和研究做了说明:“一、调查之地域为满洲、支那、远东俄领、北太平洋、南洋、印度、澳大利亚及中亚;二、调查之重点必须与帝国利益紧密相关;三、各地域的调查,必须是有机的和综合的;四、本所不仅进行调查,而且委托官民之机关及权威人士,获得他们的协力,以推进调查;五、不进行调查之外的活动;六、本所虽不是国民的宣传引导机关,但必要时可向国民公布有关事实;七、本所愿意接受有关机关之资料与教示。”这就将“东亚研究所”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情报调查机构的性质,规定得十分清楚了。从成立后到日本战败前夕,东亚研究所除编辑出版了上百种有关中国的图书外,还编辑了题为《东亚研究所资料》的大型系列资料集。这些资料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总数多达四百余种。内容涉及关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金融、军事、教育、思想、民族、宗教、地理、气象、矿产资源、农牧业、商业物产、交通运输、外交关系等一切方面。其规模与范围之大、研究之细致,当令人叹为观止。该研究所资料课于1941年编辑的《东亚研究所日文图书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