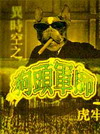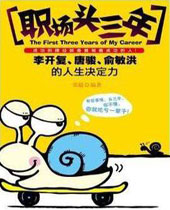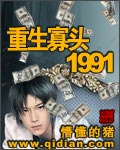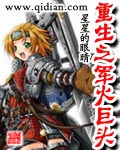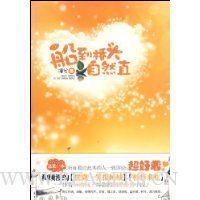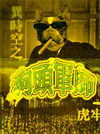怀旧的舌头-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北酸菜。东北酸菜跟东北乱炖似的,没大讲究。 而家乡酸菜,却是一般人做不了的。首先是原料难找,最好的酸菜都是野菜做原料,比如刺盖、苦蕨等,都从山上采来,新鲜,无污染。现在野菜少了,也有用白菜的。其实这白菜也不是北京常见的大白菜,而是圆白菜,圆白菜比大白菜更瓷实一些,白菜味儿更重一些,但一用圆白菜,酸菜的味道马上就下了一个档次。 讲酸菜,一定要说到“投”这个字,“投”字很常见,投篮、投靠、投军、投案、投标、投产,都跟投有关,但您没听说过“投酸菜”吧,对了,我们那地方做酸菜,不叫做而叫投。 投酸菜之前,先要晒菜。把菜洗完了,放在簸箕里晾晒,等晒得菜叶有点发蔫了,才能开始投。投酸菜得有酸菜底儿,这酸菜底儿就是酸菜缸里剩下的部分,类似于发酵用的引子之类。哪家要是没了,就到邻居家借一碗即可。这酸菜底儿,传了千年,如春风野草,生生不息。 下一步煮野菜。把发蔫的野菜煮个七八成熟,再往里搅点面粉,和酸菜底儿一起倒进缸里,用专用的酸菜缸盖儿盖上个一周左右,揭开,没有白花,大功告成。这菜呢,就叫酸菜,这水呢,就叫浆水。 酸菜做工简单,但吃法多样,可以直接捞到碗里,拌上熟油及其他咸菜,是日常凉菜,而浆水则是夏天最受欢迎的冷饮。 再说酸菜浆水面的做法。取浆水若干,少许酸菜,少许石葱花,先倒油锅里过一遍,然后加水烧开,单独盛放。再用另外的锅烧水煮面,面条捞碗里,和浆水混合,加油泼辣椒和韭菜,即是浆水面。这浆水面味道清香,如同菜中之苦瓜,有败火清肺之功效。 刚才说到了石葱花,这也是野菜一种,长在山里石头边,外形酷似葱,因此得名石葱。石葱花不好采,放暑假小孩没事干了,家长就打发到山里采石葱花去,一暑假也就能采一罐头瓶,晾干后可以吃个半年一年。 三、我姨家一表哥,跟朋友到广州去做生意,生意还不错,但没过三月,人就跑回来了。 问原因,说是饮食不习惯。问多了就有点委屈,说:“想念浆水面啊,越是吃不到就越是想着,还哪有心思再做生意,干脆回来算啦”。 我姨就跺脚:“大鱼大肉你不想着,竟然惦记着酸菜,真是没出息!”你看看,酸菜浆水的威力有这么大,就跟风筝的线一样,不管到哪都能把你牵回来。 我也没出息的。有一年回老家过年,回来的时候心血来潮,就提回来了一小捅酸菜底儿,想自己投点酸菜,以后做浆水面吃。按我妈交代的方法投了一次,几天后揭开桶一看,白花花一片,全坏了。打电话咨询我家老太太,老太太说:“你别看酸菜是土东西,精贵着呢,你得用缸,不能用塑料的东西!”好好,于是我赶紧去市场买了个缸,把剩余还没吃完的酸菜底儿又投了一遍,结果发现还是不行,于是泄了气。 太太是苏州人,结婚以来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饮食问题,饮食问题落到实处就是面条问题。她跟面条有仇,什么面条,吃着都不对味儿。所以,别说浆水面,就连面条,我们家也是一月吃不上一回。 去年回家,一到家我妈就端上了浆水面,我扑棱扑棱连吃三碗,把我太太看傻了,于是端起碗尝了一口,说:“还行,不难吃”。这是迄今为止,她对浆水面最高的评价了。 四、我这个人没什么远大理想,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卧谈理想,别人说了好多,问我,我说:“我要开个面食馆,就做家乡的鼓角儿、粉鱼儿、搅团、圈圈、锅盔、酿皮和拉面,我就不信北京这么大,人这么多,会没市场?” 同学笑我没远大志向,送我外号“浆水面”。即使到现在,同学聚会,时不时还会提到面食馆,然后大家就会心一笑。 说多了我就说:“我要组一个团,以中国四大石窟麦积山石窟的名义把你们带到天水,然后顿顿给你们吃酸汤浆水面,等吃上瘾之后再带回北京,然后我自己开一家店,发展你们做第一批忠实顾客并兼作市场推广”。 嘿,真有那个时候,我也就不用在纸上这么痛苦地遥望了,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几碗就几碗,吃一晚,还要晾一碗。 不亦爽乎。
第三部分程青松: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图)
干革命的人自己烧不烧饭吃?针对这个疑问我好奇地问过外婆。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厨房中度过的外婆告诫我,小孩子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吃饭也是件神圣的事情,至少要虔诚和专心。她还说,雷公都不打正在吃饭的人。这话还真有点道理。即使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家家户户照样有条不紊地盛饭、上菜、喝汤。有一天,我确信我找到了答案。看《闪闪的红星》时,我发现潘冬子肩负着给红军送食盐的光荣使命。原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革命者是要吃饭的,他们不仅仅需要食盐,还喜欢吃鱼。《小兵张嘎》的一开头,就是张嘎在白洋淀里抓鱼。嘎子奶奶家里藏着一位养伤的八路军,嘎子抓回鱼来就是为了给伤员滋补身体。
小时候吃肉的日子有限,购买供应肉需昼夜排队,我和哥哥都被父母委以过排队的重任。
有次父亲出差带回来一只罐头,加热后母亲平均分配给我们兄妹三个,吃过以后我们方知美味为何物,对那只罐头的芳香记忆也留存至今。
大约在1978年,不知道是在《小朋友》,还是《儿童时代》杂志上,看过一个叫“七把叉”的外国人的漫画,他有一个异于常人的胃,饭量也非常人所及。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食物多得可以吃死人的故事。七把叉的大胃,让人畏惧,也让人羡慕。
80年代,生活渐渐有所改善。年年腊月街坊邻居都要大动干戈灌川味香肠,我们家也不例外。父母攒了一年的工资拿去买了30斤新鲜猪肉。母亲用菜刀将猪肉切成两寸左右的肉片,然后用手将辣椒面、花椒面、姜末、葡萄糖以及很多稀奇古怪的香料和肉片搅拌均匀。接下来的工序就是将搅拌好的肉灌进肠衣里。每到大约在半尺长的地方,父亲就会用细麻绳给香肠打上结。最后的工序是用松枝熏制香肠,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燃烧起松枝,让松树的清香渗入肠衣内。 过年时,家家都会煮香肠吃,我家也不例外。我们家煮香肠,隔几层楼的邻居都能闻到香味。春节后,饭桌上的菜开始清淡起来,香肠变成款待客人的食品。悬挂在厨房窗户上的麻辣香肠,总是诱惑着我和妹妹年幼的胃。我家楼下,父亲单位食堂烧开水的锅炉里终日燃烧着熊熊大火。终于有一天在我和妹妹趁打开水的机会,忍不住从窗户上割走了一截香肠。香肠被扔进炉膛里,冒着令人垂涎的红油。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那是我和妹妹生平第一次吃烧烤。 今年春节,我收到了已为人母的妹妹寄来的香肠,请来北京的好友品尝,个个叫好。我想,她肯定是从外婆和母亲那里学到了灌香肠的秘诀。
第三部分李振华:清蒸 (图)
清蒸可能是最健康的吃法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的简单、方便,只有有一锅热水和一个笼屉就可以实现的简单方式,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却是非常清雅的,在淡淡的烟雾之中酝酿着口腹的欲望,其中之滋味也各有不同。
古人惯常的吃法如此,如西游记与水浒传之中侠客和妖怪有着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把人蒸来吃了,根本不如现在生活与要求之丰富,如酱爆/红烧/水煮之错综复杂,本来很粗暴的事情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作者的原因,还是很有知识份子的味道,即蒸来吃看似简单,却深藏学养。如清蒸鲈鱼就被不同的诗人歌咏,现在看来当时的情景更加的接近我们生活的本质,为了追求一种简单质朴的美味,多了浅尝的余味和近乎疯狂的行动,如为了美食而奔走相告,在众多的选择之中,清蒸激发了食物中特有的鲜醇,也同时屏弃了食物中暴烈之气,如云南和客家菜中的腊味合蒸就更加的是突出人工与自然之间的醇和之气,一种是将在香肠之中的辣味与腊味中和而成绝品,一种是将三种不同的蜡制肉相互融合而成一种,其味厚重中有淡香,可能是清蒸的原因吧,两个菜都是通过高温下的水蒸气将这些人工淹制晾晒而成的,取自然之精华的材料缓缓的化开,其中美味自然随水气氤氲而出,随着物理的冷却凝结再坠入碗中,周而复始应了太极的阴阳更替之道,口感也浓厚感醇,口味也清淡相宜。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 出没风波里。 范仲淹
显然吃鲈鱼也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运动,在现在看来还是非常KAWAYI的事情,因为我们吃的可能已经是鲈鱼的片段了,甚至是成片的生吃,谁还会想要清蒸呢!通过日本酱油和绿芥末调治的酱料,将鲈鱼浸入其中的时候,少却的些微烹调带来的清雅,强调是鲈鱼肉质的鲜美,如果说两者还有互通的地方就是追求其鲜美的特点,一种是通过芥末的辛辣,一种是通过葱姜的合成气体。在这里一步一步的递进着一种循环的操作过程:生食…白灼…清蒸,却是有着类似于:水中…地上…天空的想象,如果我是鲈鱼也要为这种优待受宠若惊了。
清蒸鲈鱼为了保持其新鲜度和肉质的鲜嫩,切忌长时间的蒸,而是要蒸的恰倒好处,如10…15分钟就已经可以了,所有蔬菜类食物与之相同,而肉类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将其制成入口粘糯之感。另,一些本来是煮的甜品,蒸来更是美味,如冰糖木瓜,加冰糖/银耳/枸杞,蒸45分钟,其味道要强于水煮多矣!
另外如海外兴起的生食运动,让国人为之,稍嫌生猛,但如将其略微清蒸,无论是鱼肉、蔬菜都不失其营养,并保持其新鲜,祛除其细菌,可谓一者多劳,权且将清蒸视为一种懒惰的烹饪方法,也可收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效果。
第三部分丁颖:橘子棒冰和光明冰砖 1 (图)
小时候吃根棒冰,那真叫难得,一定是长达3天没上房揭瓦才有的犒劳。那时候多的是桔子棒冰,颜色橙黄可疑,木棒也粗糙,常有木刺划伤了手嘴,可即便是那样,卷毛孩子也舍不得立即丢弃木棍,先是舔,而后轻轻吮吸,渐渐味道尽失,才将木棍含在嘴里咀嚼,像吃甘蔗一样,挤尽木屑中的最后甘甜,连木屑都寡淡无味了,卷毛孩子就开始舔噬棒冰苍白无力的包装蜡纸,那上面的甘韵也是值得回味半天的。整个棒冰的进食过程可以长达半个小时,像是一种仪式。而印象里这仪式总是发生在发出红褐光泽的街上,每个洞开的门窗后面都有一双饥渴而艳羡的眼睛,卷毛孩子很享受这一路的注目礼,故意拖延每个过程。右手还没把5分钱交到叔叔的手里,左手却伸得比右手还长,像嗷嗷待哺的小兽。从接过棒冰的那一刻起,卷毛孩子就变得安静而耐心,甚至还有些神圣的意味。卷毛孩子总是拒绝叔叔的好心,自己剥皮,被剥去的蜡纸一定是不扔的,折一下左手里攥着。第一口总是用舌尖轻轻碰一下,迅速的,仿佛倒是带了电似的。棒冰始终不很靠近嘴唇,每到舔噬的时候,就伸头凑前,小心翼翼,舌头都不敢生硬用力,生怕稍一用力,棒冰便消失不见。舌苔轻柔而迅速地扫过,自下而上的,闭上嘴,一副意味深长的模样,每一口的最后都是以“吧唧”一声告终,到了那时,舌苔上的甘甜已经几近走失,一个干燥无味的舌苔期待着再一回的恩赐。总有那么一两滴融化了的糖水滴到地上,哀伤得像卷毛孩子自己的眼泪,卷毛孩子来不及悲伤,抬起头来的时候就已经目光坚定神情成熟,手法愈加熟练地保护起那根未尽的桔子棒冰。那是卷毛孩子的4、5岁时光,总有两条澄清鼻涕在流淌,天空不高总是湛蓝,街道不宽,两边是火红的砖墙,还有沙堆,孩子们在砌堡垒,卷毛孩子孤单但不寂寞地走过,整个幼年。卷毛孩子的快乐最为重大,伴随着仪式,形容得意,只一次就足以回味一个星期,教其它孩子的吵闹黯然失色。
对于麦乳精,卷毛孩子是从来不冲泡的,用钢勺撬开盖子后直接舀来吃的。满满一口,塞的舌头都挪不动地方,先是香,渐渐被口水融化开来的时候,就是馥郁难忘的甜了。家里的麦乳精是“乐口福”牌的,红黄相间颜色鲜艳的铁罐头放在大衣橱的中间,下面是一只抽屉,上了锁的,卷毛孩子知道里面有一只长了漆黑乌亮胡子的脸谱,青面獠牙,塞在一团红丝绒的里面,每次父亲双手背后,眼光神秘地从里屋走出来的时候,卷毛孩子就一声尖叫没命地跑到母亲那里,躲在她的身后,嘴里叽里哇啦地叫着,眼睛却像铁器受了吸铁石的吸引,直直朝父亲的手里望去,只消那团红丝绒,卷毛孩子便经受不住,咿咿呀呀叫上半天,那青面獠牙的脸谱不用露脸,单单露些根胡子出来,卷毛孩子就能哭出眼泪来,这游戏百试不爽,父亲、母亲各有角色,形象生动。所以,当父亲母亲不在,卷毛孩子打开大衣橱,端来板凳,跨上去拿麦乳精铁罐的时候,内心实在不太好过,她知道那眼睛就在抽屉的黑暗中,红丝绒的里面,它有透射的能力,即便有铜锁的挟持,也能令卷毛孩子如芒刺脊。而这样的时候,也令卷毛孩子莫名地增加了些快乐,那甘甜经由这小小的冒险变得益发刺激和可口,让人上瘾。父亲母亲一锁上门去上班,放假的卷毛孩子就被这大衣橱里的神奇深深吸引。只是一桶麦乳精很快吃光,不过一个礼拜的时间,父亲母亲还没有发觉,卷毛孩子也没有蛀牙,每天仍旧等待父母离去之后打开大衣橱,搬来小板凳,那个用钢勺撬开铁盖子,盖子上面已经有锈迹,残渣被刮得干干净净,只那个罐子还兀自幽香着,甘香得像是能把卷毛孩子吸进去,而里面一定是一个巧克力世界。这个时候,红丝绒里得眼睛漆黑乌亮,射出两道冷光,卷毛孩子每次都心有余悸,也每次都明白它其实出不来,就不免有些得意。
第三部分丁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