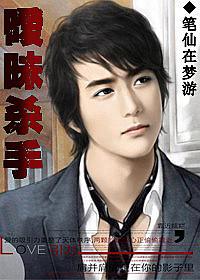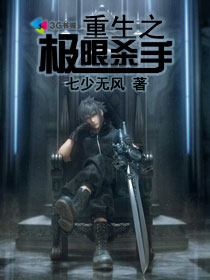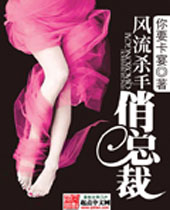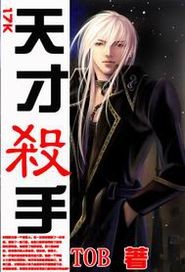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个泰国女人和我交往并成为我的朋友,并不是想获得什么物质利益,也不是因为别人雇她把我拖下水,因为事实上,我早就已经下水了。她之所以这样对我,可能是因为她心地善良,也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进入她的生活,或许,我们相互吸引,走到了一起。跟我在一起,她的真正动机到底为何,我从来没完全弄清楚。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与我做伴,陪我说话,总能激起我最原始的欲望,她也是我最信赖的朋友。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告诉我跨国业务高层和国际外交中常用的手段。“如果有美女试图引诱你,那么她们的房间里肯定藏有照相机和录音机。这不是说你没有魅力,只是说,事情往往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她告诉我,在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些交易中,像她那样的女人,曾发挥了关键作用。
执行第一次任务后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又被派遣到苏拉威西岛出差三个月,那是加里曼丹岛东部的一个偏远岛屿。根据这个岛屿地图的形状,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酒后乱跑的长颈鹿”。政府选中了这个岛屿,作为发展农村的试点。过去,这个岛屿在东印度公司组织的香料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它已经沦为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下定决心,要把这个落后的岛屿打造成进步的象征。而我们美国人则认为,这个岛屿将成为我们矿业、林业和农业获取稳定收入的潜在基地。这里富有金矿和铜矿,植被保存完好,因此几个巨头公司虎视眈眈,跃跃欲试;一家经营牧场的得克萨斯企业就购买了这里上万英亩的森林,他们把这些树木伐光,卖掉。他们还计划在这里养生畜,然后用足有足球场面积那么大的巨型驳船,将牛肉运走,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市场出售,赚取可观的利润。同样,苏拉威西岛也是政府移民计划的重头戏。这个计划和美国对亚马孙雨林地区的殖民情形如出一辙,对当地居民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作为和平队志愿者的我,曾亲眼目睹了当地居民的贫穷生活。移民计划的目的,在于将爪哇岛城市里的穷人迁徙到人烟稀少的地区。当时爪哇岛的人口密度居世界首位。跟拉丁美洲移民计划一样,该移民计划得到了国际发展机构的资助和支持。政府为这些贫民窟里一无所有的居民提供一定补贴,鼓励他们迁徙到无人居住的农村地区,以此减少反政府暴乱发生的可能性。虽然有专家学者不久就发现此类移民计划,不论是在亚洲,抑或是在拉丁美洲,通常使当地居民生活更悲惨,但政府不为所动,继续实施他们的计划。于是,当地土著居民被驱赶,土地被破坏,文化被消灭。新移民过来的城市人口,开始努力耕耘这块被破坏的土地,但并没有取得成功。
到达苏拉威西岛的时候,有人给我安排了一幢政府所有的房子,位于古老的葡萄牙望加锡(出于民族独立的考虑,在苏哈托的示意下改名为乌戎潘当)城外,女佣、园丁、厨师、吉普车及司机一应俱全,全听我差使。和往常一样,我们的任务在于寻找目的地,并去考察,因为那些地方可能拥有跨国企业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我们要与社区领袖会谈,搜集所有相关信息,最后撰写可信的报告,论证用以兴建电厂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巨额贷款的可行性,论证贷款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从而将这个落后的国家带入现代化强国的轨道。
正在开发的得克萨斯牧场附近,有一个叫做“贝茨维尔”的镇,已经成为电厂的可能选址。一天清早,司机带我们驶出乌戎潘当,一路沿着那景色壮观的海岸线进发,抵达港口城市巴里巴里。然后从这里出发,小心翼翼地沿着曲折蜿蜒的公路,慢慢开进偏远内陆那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我们驶过的所谓公路,不过是将丛林砍去后留下的一条狭窄的小路。我感觉又回到了亚马孙雨林地区。
就在吉普开进平朗的一个村落时,司机告诉我:“就是这里,贝茨维尔到了。”
我迅速扫视了周围环境,因为贝茨维尔这个名字激起了我的好奇。我到处搜寻蝙蝠的踪迹①,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司机带着我们,在这附近慢慢转悠,经过一个广场。这种广场,和遍及印度尼西亚的诸多其他广场没什么两样:好几条长长的椅子,旁边矗立着几棵大树。在大树深处的几个树枝上,挂着体积超大的黑色团状物,就像超大的椰子。然而刹那间,其中一个团状物张开了。就在我意识到那是一只巨大的蝙蝠正展翅欲飞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司机把车停下来,带我来到树下,正上方就有一只蝙蝠。那个让我无比兴奋的蝙蝠缓缓地扇动着它的翅膀,在我们上方盘旋,它的躯体足有猴子那么大。它张开双眼,头朝下盯着我们。有传闻说,这些蝙蝠能让电线短路,它们的翼展宽度超过6英尺。什么飞禽有这么庞大的体积,能和我眼前所见的蝙蝠一较高下?无论我怎么挖空心思地想,都是徒然。
我们继续走。稍晚一些时候,我们见到了平朗市的市长。我问了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们本地的资源如何;如果在他所辖的地区由外国人兴建电厂和其他产业,他们对此是什么态度,等等。即使在会谈过程中,我仍然还想着那些蝙蝠。我问市长,这些蝙蝠是否会造成什么问题,他回答说:“不会。它们每天晚上就飞走了,在远离我们小镇之外的地方找果类吃。早晨,又返回这里。从来就不碰我们城里的东西。”他端起茶杯。“和你们国家的公司极为相似,”他说,同时精明地笑起来,“它们飞往其他遥远的地方,靠掠夺那些地方的资源来生存,在那吃喝拉撒,然后又回到栖息地。”
这种论调,我经常听到。我逐渐认识到,美国大众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剥夺他国资源基础之上的这一事实,而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相而被美国剥夺资源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对此心知肚明。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就知道我们的军队并不是用来保护民主制度不受侵犯的,相反,只是用来保护那些开发利用资源的公司的。因此,他们为此担惊受怕,怨恨与日俱增。
苏拉威西岛也是布吉斯部落的居住地。几个世纪前,欧洲的香料贸易商对这些部落充满畏惧,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野蛮、最嗜血的海盗。这些欧洲贸易商返航回到家后,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就吓唬他们:不乖乖听话的话,“印尼海盗布吉斯人会把你捉去的”。
20世纪70年代,布吉斯部落仍然过着原始生活,和他们数百年前的生活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他们建造的大船,气势磅礴,威严无比,穿梭于各岛之间,将群岛商贸的通航要道紧密地编织起来。操作这些张着黑色帆布的大船的水手,穿着宽松的长筒裙,头上佩戴鲜艳的头巾,脸庞两边挂着金耳环,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别在他们腰带上的,是威猛无比的大砍刀。他们的这身行头,在我们看来,是因为他们仍然以他们的祖先为荣。
我逐渐和一个年长的造船工人混熟了,他叫布尼,他一直按照祖先传下来的方法以造船谋生。一天,我和他一起吃午饭时,他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海盗。“现在,”他递给我一片可口的水果,接着说,“我们很困惑,不知道该做什么,凭我们这些木制帆船,凭我们这几号人,我们怎么可能赶走美国人呢?他们有的是潜艇、飞机、炸弹,还有导弹。”
这样的问题让我心烦意乱。他们的言行最终让我确信,我应该做出改变。
和那位造船工人谈话若干年后,我结束了作为经济杀手的职业生涯。辞职的决定,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提到过,是我在一次远航度假时做出的。那时,我在加勒比海列岛中的一个岛屿上度假。这些岛屿曾是海盗的据点,他们以此为基地,抢劫西班牙黄金运输船队。一天下午稍晚的时候,我来到一个年代已久的废弃的种植园,在废墟上坐下,陷入沉思。我想到了建造这些城墙的非洲奴隶,想到了他们所遭受的令人发指的悲惨待遇。此刻,我认识到,我也是一个奴隶。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灵魂折磨后,我下定决心,要远离这肮脏的阴谋。于是我飞回波士顿,递交了辞呈。但随后,我并没有揭露这个新帝国建立过程中那令人恐怖的真相。因为在威胁和贿赂面前,我屈服了,退却了。随后的这些年中,我的过去一直折磨着我。我的所作所为,我所知道的真相,不得不咽在肚子里,独自一个人承受这种煎熬。接下来,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我站在那令人毛骨悚然、化为焦土的大坑的边缘,而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以前就耸立在这里。我知道,最终我得站出来,我得向世人自白。
2004年,《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出版后,我开始回答电台采访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以前我对自己的角色和将带来的灾难知之甚少,事实上,作为经济杀手展开行动的我,对那些我曾经外派工作过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我们曾经战胜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可以藐视其他任何大国。我们大肆吹捧“进步”和“工业化”。我们扶植了一种新的第三帝国精英势力—公司帝国的走狗。但是,我们征服的那些地方的大多数人们又怎么样呢?我必须重新认识,我将从执行任务踏入的第一个国家说起。
过去,我一直借助主流媒体追踪印度尼西亚发生的范围广泛的事件。而如今,我则挖掘得更深,我的信息来源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其他我曾经效力过的机构。此外,我还从非政府机构和学术出版物中获得了尽可能详尽的材料。在我越来越熟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被称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发生的背景后,我的好奇心被进一步激发。这次经济崩盘始于亚洲,给亚洲数以万计—可能是数以百万计—人口带来灾难,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挨饿受冻,有的则绝望自杀,其影响迅速席卷全球。对于愿意听到真相的那些人来说,亚洲金融危机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真实意图是那么的险恶,同时也昭示世人,不要试图人为操纵经济体,除非这样做的目标在于进一步充实公司帝国的腰包,而让其他人成为其牺牲品。
乍一看,官方数据告诉我们,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经济发展不断创下新高,至少持续到了1997年。这些数据无不反映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得意之情:通货膨胀率很低,外汇储备总计超过200亿美元,贸易顺差超过9亿美元,银行业得到稳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1997年之前,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幅度(以国内生产总值来测算)平均每年为9%—诚然,并没有达到我昧着良心、为了迎合我的主人而预测的那令人叹为观止的两位数增长,但9%的成绩仍然非常可观。世界银行、咨询公司和学术研究所聘用的经济学家,拿出这些数据用以论证我们这些经济杀手所执行的经济发展政策是十分成功的。
这些经济学家所提到的“经济奇迹”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印度尼西亚人为此承受了极高的代价,而那些数据并没有涉及半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不久,我就对这点深信不疑—经济发展的受益人仅限于处于经济阶梯顶部的那些人。通过滥用廉价劳动力,国家收入飞速增长。而那些身处血汗工厂一线的工人,在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长时间地工作;同时当地政府出台优惠外资公司的各种政策,允许它们破坏环境,允许它们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那些被北美和其他“第一世界”国家视为违法的活动。虽然该国法律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上升到每天大约3美元,但很多公司根本无视这一规定。据估计,2002年,印度尼西亚52%的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足两美元。从很多角度分析,这简直就是当今时代的奴隶生活水准。即使每天有3美元的收入,很多工人也无法维持家人的基本生活。
让印度尼西亚人民背负沉重不堪的负担的这些政策,印度尼西亚政府竟然默许了。这绝非巧合。为了让该国的精英们积敛大量财富,该国大举借贷,从而积累了有如天文数字的巨额债务。面对这些巨额债务,印度尼西亚政府不默许这些政策,又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根据世界银行整理的全球金融发展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理的国际金融数据(IMF…IFS),平均算下来,该国一直是亚洲各国中背负外债比例(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最高的国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即1990年到1996年这一最危急的期间,其负债比例高达60%(同期,泰国的负债比例约为35%,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均为15%,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约为10%),并在这一数据上下徘徊。在1990年至1996年期间,该国的还本付息再加上短期债务,占外汇的比例平均接近300%(同期,泰国的比例为120%,中国内地为60%,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25%),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毫无疑问,正是我们让这个国家背负了如此沉重的巨额负债,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偿还,为此,印度尼西亚人民被迫以其他形式偿还债务,那就是满足我们公司帝国掠夺资源的野心。我们这些经济杀手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既定目标。
衡量国民经济的砝码,又一次被证明是极具欺骗性的。在印度尼西亚,情况往往如此。外汇储备逐步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率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十分可观,但是,这不过描述了印度尼西亚一小部分富裕人口的状况罢了,其他人则生活在主流—可测算—经济之外,而正是他们背负了那些可怕的债务。
贫困、公司的虐待行径和美国消费者之间,通过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是其他国家血汗工厂的典型)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密切,不言自明,恐怕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