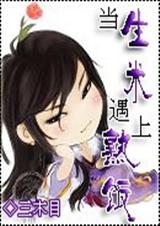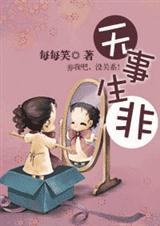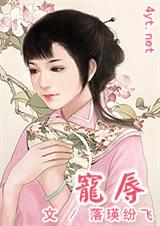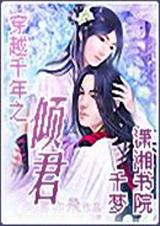朱明画卷(vip完结)-第1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仪华揉着太阳穴,正想说没事,却想起今日后宫诸妃不快的目光,其余人或嫉妒或羡慕的目光,又觉一阵头疼,下意识的点头:“恩,让李进忠去回王爷一声,说我身体不适晚上不去宫宴了。”
稍作吩咐,掀开薄被起身,直接坐马车回府。
当天晚间,哪里知道随口说起的推诿之词,竟然成真。她一回到府里,人就不到,身上一阵阵的发冷,吓得盼夏赶紧请了太医来。一看才知,是日间晒了正午的日头,下午又在较凉的地方睡了,却是染上了风寒。后来,这太医又说了几句“三月春寒料峭,最容易伤寒,要多注意”的话,便开了药方离去。
仪华精神萎靡,喝了汤药,就睡得人事不知。
等第二天醒来,也没见到朱棣人影,却听李进忠传达了一个王命——朱棣下了禁今,她伤寒一日不好,她一日不许出主院——这样的命令,仪华有些悔了,又见身边的人一个个把她盯得死紧,简直让她苦笑不得。
不过本就只是轻微伤寒,顶多四五日便可痊愈。却一转眼旬日过去,朱棣仍以她身子不好未全好为由,将她禁足。
仪华隐隐感到不对,认为朱棣有事瞒着,却思量不出所瞒何事。
一如彼时,她见院中槐花开得正好,就拿着一本闲书,坐在槐树下的石凳上,百无聊赖的翻着书页,实则正思量着这几日的事。
犹处思量间,忽听侍人禀徐增寿来了。
仪华一喜,想到徐家限制徐增寿出行,她姐弟二人已二个多月未见,忙不迭撂了闲书,到院门口相迎。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在门口翘首以盼一会,却见徐增寿一脸不忿,仪华忙开口问道。
徐增寿抿着唇不说秸,瞪了一眼四周侍人,不由分说的拉着仪华去了书房,“啪”的一声关了书房的门,气急败坏道:“大姐!‘士争凑燕’是好事,不说也罢!可这些造谣的,居然说你不敬长辈,以为稳坐太子妃之位,害郭惠妃受伤,好代她行亲蚕礼!”
(今晚还有一章,不过估计根晚,大家明早看吧,是一定很晚,明上午看吧)
第235章 薨逝
自那日代行亲蚕礼,心里已有思量,现下听来也不太意外,只是 “士争凑燕”又何解?
疑惑刚生,仪华已不假思索,沉声道:“一个冲着我来,另一个必是冲着王爷去!这“士争凑燕’是怎么回事?”
徐增寿性子冲动,却知事情轻重,见仪华一副全然不知的样子,诧异的看了看她,自觉地消了火气,将这半月发生的事一一详叙。
上月祭礼那日,乐元璋宴群巨,至酒过三巡,有人借下月蓝玉征罕东一李,说起朱棣最近两年疆场上的风光。一时话题起了头,有心无心都热烈讨论起来,这一讨论,自然说到朱棣麾下将才兵马扩大上面,然后便有一文人赞了北平如令人才云集,朱棣封号又为“燕”,笑称 “士争凑燕”一词是为朱棣所造。
这一番括,原不过走途迎拍马之意,并没引起重视。
始料未及的是,一夜之间,“士争凑燕”竟流传开来,并有了其他解意。
此词本指人才赴集,出于《战国策》一则,乃是讲战国七雄中的燕,其主燕昭王复辟了燕园后,为了向强大的齐国雪国破之耻,许重金广招天下有智之士,以至各国才能者纷纷赴燕,最后燕国殷实富足、国力强盛,终于打败齐国得报大仇。
这样一个记载流传了上千年的故事,至本日,却将它赋予了一个新的涵义:以燕昭王暗指燕王朱棣,取其“燕”字;燕昭王忍辱负重多年一朝复国,如朱棣一直蛰服众兄弟中,终在两年前一战成名;燕照王广纳贤士之举,更昭然译为朱棣这两年“占据”将才共马;至于最后燕照王直取齐国都城,而朱棣是直指何地便不言而喻。
听到此处,仪华脸色骤变。
从正月过后,随着五位藩王滞留京师的日子渐长,太子病危的流言难堵悠悠众口,开始大肆流转;紧接着,东宫之位的下任健承者的选择,俨然就成了所有人最关心的事。
而如今后继者,以皇孙世嫡为依据的朱炆、以无嫡立长为凭的晋王、以及以无嫡立贤为倚仗的朱棣,三位为最炙手可热的人选。至于身为皇二子的秦王,因德行有失,已被排除于太子过世后的长子地位。
如此这般,朱棣正处风口浪尖上,却又有“士争凑燕”这一暗喻,且不管暗喻是真是假,但难免众口铄金,以至朱元蜂认为朱棣野心勃勃从而防备,甚至还会影响朱棣在军中的声望!
……
仪华思绪每转急下,极力克制下心中惊怒,迭声追问道:“这到底是从哪里传出去的?流传到什么地步?”
徐增寿摇头道:“不清楚是从何处流传出来。至于流传范围却是极广,就连酒楼的说书人,最近讲得也是燕昭王的生平之事” 说着兀自皱起眉头,边思边道:“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不利您的流言,只是后来关于“士争凑燕”的传闻多了,就有人质疑亲每礼那日,郭惠妃意外受伤的事。”
言至此,徐增寿忽又想起一个传闻,嗤之以鼻道:“大姐,有人拿郭惠妃和徐家的姻亲关系作文章,说郭惠妃假装受伤,是为了让你主特大典!”说时火气又起,忍不住一拳击上书案,愤怒道:“简直就是胡乱造谣。”
这“嘭”地一声重响,将仪华从纷杂思绪中唤回,看见徐增寿一脸愤怒,却双眼关切的看着自已,不觉心中一暖,勉挤敛去一片心思,打起精神安抚了徐增寿,再详问了一些事后,也不留他晚膳,让李进忠送他离开。
人走后,仪华独自坐在书房,脑中翻来覆去想着徐增寿说得话。
幕色将合时,王府各处一一掌了灯,朱棣也从外回来了。
这时,仪华仍坐在书房里,忽听“吱呀”一声房门开了,抬眼一看她收拾了一下心情,从书案后含笑走了上前:“王爷,您回来了。”
朱棣点头,随手关了门,走到离仪华一步的距离停住,低头道: “下午你三弟来过,你都知道了。”
仪华没想朱棣一踏进屋就直说,稍怔了下,微微点头。
见仪华脸上笑容淡去,朱棣解释道:“别多心,开始没告诉你,是你正好病。后面……”乐棣皱了皱眉,走到靠墙的太师椅坐下道: “事情发展的出了意料外,以免你白为此操心,便瞒了过去。”
仪华本想就“流言”一事而论,却听朱棣后面一句,不由临时接了话道:“王爷不想巨妾操心,王爷仅一直瞒了巨妾?,就瞒了过去。难道流言的事一日不说这话时,她定定地望着朱棣,等他回答。 朱棣好一段日子不见仪华这样坚特,他微微有些意外,口中也答非所问道:“中伤你的流言,我有把握这几日内压下去,再把事情告诉你。”
“王爷。”仪华语气坚定她打断,看着昏黄烛火笼革下面庞柔和了几分的朱棣,一字一字咬字清晰道:“您与我是夫妻,夫妻是要相伴一辈子,荣辱相共!”
朱棣听了略有触动,颌首道:“好,下次不会再隐瞒你。
冰冻三尺外一日之寒,朱棣根深蒂固的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可改,仪华暂搁了话题,另道:“如今流言都传入市井中,王爷方才却说这几日就能压下去,难道您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
流言只会越传越烈,要压制银本不可能,朱棣又会有什么办法……
仪华念头刚生,就见朱棣默默走至窗扉下,凝立不语。
“王爷?”久等不到朱棣回应,仪华望着他的背影试探一唤。
朱棣依然不语,良久后,他倏然回过身,生硬道:“要压下一个流言,就要出现另一个更值得商讨的话,引去其他人的兴致。”话一顿,声音沉了下去,缓缓道:“六日前,五弟暗中给我捎了消息,太子……最长只有不到十五日的涛命。而这个消息一出,中伤你的流言也会慢慢消去。
艰难延续生命命数月,太子他终将寿元了?!
许是让太子病危一事,搅得人心惶惶数月之久,一时仪华竟好似恍然未闻,只木然的重复道:“太子他就要……”
一语未成,门扉“啪啪”被人重重拍响,李进忠惊惶的声音从门外传来:“王爷王妃,太子殿下薨逝了!”
第236章 丧礼
前一刻还惊于太子寿元将尽,这一刻却闻太子薨逝的噩耗。
然而太子病危的传闻流传已久,经过初闻时的震惊,也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
一如仪华此刻的心情,相对于太子薨逝的冲击,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才更令她担心。毕竟只要太子还活着一天,京中各方势力依然会维持表面的平衡,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上谋逆夺嫡之罪。
但是现如今太子归天,东宫空缺,一切就变得名正言顺了。
常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处于京中局势这巨大漩涡的人,更多看见的是夺嫡天下,享拥立之功;而忘却能决定一切的人,只有金陵皇宫中那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心念至此,仪华忽然想知道朱棣此时又是何种想法,她凝起双眸向他看去。
烛影摇曳,朱棣高大的身影屹立在一片昏黄光影中,光晕柔和,却无法缓和他黝黑刚硬的面庞,也就这样一如既住的刚毅神色,让人窥探不到一丝一毫的情绪起伏。
凝视之间,朱棣眸光一凝,四目相对。
“大哥仁厚,对底下的幼弟颇为照顾。”朱棣率先开口,目光有一刹的隐痛。
也仅是这一刹,朱棣目中已然一目坚定,面上却露沉痛之色,道:“去换素服,我们即刻前往东宫。”说完推门而出,吩咐全府上下做服丧准备,严禁王府人员进出。
一时间,整个燕王府忙做一团,四下到处是奔走的侍人。
仪华出了书房,看了一眼院中忙着换白纸灯、挂白布的侍人,也匆匆回到寝房里,卸去脂粉钗饰,换上素服白鬓花。
约小半个时辰后,挂着两只大白纸灯的燕王府府门大开,驶出一辆青帷黑盖马车。
马车里,仪华一身白衣素服坐窗口下,手轻撩窗幔一角,看着沿街商铺前一盏盏白灯一条条白布在眼前晃过,又间或不安的看一眼沉默不语的朱棣。
朱棣却似乎一无所觉,只是闭着双目,靠在车壁上一言不发。
路上前往东官奔丧的马车络绎不绝,一律的青帷黑盖,在茫茫夜色中也分不清彼此是谁,就拥拥堵堵一齐向东宫驶去。
这样的行驶下,临到东宫时,已黑压压跪了一地着素服的官员。
因身份使然,他们一路畅通无阻,穿过丹墀下文武官吏,登上玉阶直奔大殿。
大殿,本为东宫正殿大堂,现在已作为灵堂。只见这灵堂上,太子的灵柩安置于正首,前方的紫檀供桌上,纸线香烛焚烧,长明灯幽幽燃着,再至供桌一旁,正是披麻戴孝的朱允炆,领着庶母兄弟跪地哭灵。
“燕王、燕王妃到!”殿外丹丹墀上留守的礼官太监,眼尖的一下认出前来的这对夫妻,忙打锣一声高喊道。
通禀声又尖又细,即使在殿内外一片呜咽声中,以及对面近一百名僧侣的念经声下,依然极易辨别。
遂须臾片刻,就有闻讯的司礼宫人出大殿,将他们迎了进去。
一踏进殿内,仪华就感异样的目光瞬间聚了过来,她脚下顿了顿,随即亦步亦趋的跟在朱棣身后,一一逐制的行过上香叩拜等礼仪;而后转身,看见朱允炆强撑着单薄的身子,摇晃着站起行拱手礼道:“弟妹年幼,侄儿代自己与弟妹给四皇叔、皇婶见礼。”话里带着压抑不下的泣声。
仪华听着鼻子莫名一酸,再顺朱允炆的话往过一看,只见两个不过熙儿一般大的小男孩的跪在地上,迷茫无措的望着他们几人,眼里不禁有些湿湿的。
“四皇婶。”朱允炆见仪华目含怜惜的看着他兄弟几人,心中一动,想起幼时仪华待他的温柔,情不自禁道:“三年前炽堂弟在京中,曾说您身子不大好,这几年没有联系,也不知您身子耳好些了?但还是请您勿要为怜惜侄儿们伤心费神。”
话中关切之情拳拳,却让仪华听得意外非常,终是泪盈于睫。
正心怀感动间,殿外忽起一阵骚动,众人纷纷侧目看去。
远远地,只见几个着素服的人往里奔来,隐约还能听到一些哭声。转眼间,人影越跑越近,哭声越听越明,当即便认出来人正是晋王夫妻。
仪华眼睛一跳,目中泪意已消,默然看着奔丧而来的晋王夫妻。
晋王面上哀痛不巳,一路跌跌撞撞地直奔太子的灵柩,“噗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诉说着未能见太子最后一面的遗憾,以及对太子英年早逝的痛惜。
其后,晋王妃也是一副哀恸的样子,任左右两名侍女搀扶着,走到太子留下的妃妾子女面前,哭了小半会,一时又哭道:“……能从太子殿下而去,是佑泽你们及家人的福禄,只是难为侄儿侄女们还小,没有人照应了!”
周王妃这一说,一众妃妾宫女想到殉葬的命运,再也不住心中绝望放声大哭。
一旁仪华冷眼旁观多时,此刻心中却是震惊、愤怒皆有之。
今上朱元璋登基之初,即制定宫中殉葬一列——君逝后,除去正室嫡妃以及特恩免殉者,一律妃妾皆要殉葬——可如今太子已逝,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又有谁敢为那些妃妾求情,即使这些妃子中有是小王子养母的,有是生养过小郡主的,却无一幸免!
仪华心中滋味莫名,说不清是对殉葬的令人发指,还是对封建皇权压迫的一种无力。她只手捂胸口,恍惚的在太子十几位妃妾中看去,片刻,月光停留在了一对相拥大哭的母女身上——她们一个正是掌东宫十年之久的陈次妃,一个是太子的长女,年仅豆蔻的江都郡主。
“莫受影响,她们死后都有封号谥文,且恩泽娘家父兄。”察觉仪华情绪不对,朱棣瞥了一眼哭到一片的太子遗妃,皱眉道。
仪华怔然抬眸,触上朱棣隐含关切的目光,她只能微微点头,道:“恩,臣妾知道,只是一时感触而已。”
这边夫妻二人低声交谈,另一边跪灵许久的周王,愤怒地看着哭声震天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