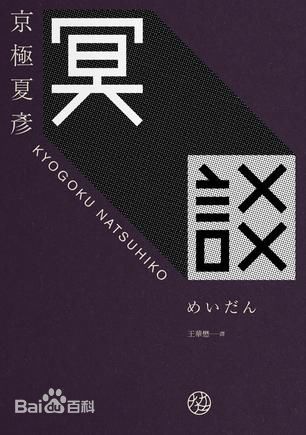冥谈-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这个角度来看,《劫之滨附近的祭祀俗信》要说是珍本,也算是珍本吧。
我在市史编纂室发现了这本珍本。
说是编纂室,也只是市公所角落一个布满灰尘的房间而已。虽然还算大,但有一半是仓库,或者说储藏室。
不,那里本来就是储藏室。
听说五年前,在重新翻修老朽化的市公所时,挖出了好几箱古文献记录之类的纸箱,真的如山一般多。
公所方面原本似乎打算处理掉,但有人指出里面或许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便决定暂时保管。
我觉得这是个贤明的决定,但或许只是办事人员胆小怕事罢了。况且有人指出可能有贵重物品,指的如果不是学术价值而是古董价值,那么心态也不怎么值得嘉许了。
若是考虑到先前说的对这种事不怎么热衷的县民性格,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即使如此,总之古老的资料是保留下来了。
不过也只是因为丢不了罢了。
整理需要人力,也需要时间,还有空间,也就是得花钱。在财政紧缩的时节,似乎还是不可能挤出那种预算。
它在储藏室被晾了两年。
约三年前,在届龄退休的职员号召下,几名对乡土史有兴趣的人集合起来,组成了市史编纂委员会。虽然叫委员会,但并非官方组织,而是一群民间志士。每到周末,有空的人就集合起来,将箱子里面大量的纸山加以分类,整理得稍微像样一点,这样罢了。成员全都超过六十岁,几乎都是有兴趣、但没经验的门外汉。
挤不出预算,但想做的话就请便——就是这样的公家机关差事,是一场消极的计划。
我每个月会参加一两次集会。
表面上的名义是市史编纂的顾问,但说穿了只是整理资料的帮手。当然,市公所没有付我酬劳。我不是顾问,而是天经地义似的义工。
我是被大学时代的恩师拜托的。
恩师……算吧。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称呼了,他在近世史的研究领域是个知名的学者。
他也是这个市出身的。市史编纂的号召人是他的亲戚,委员之一还是他中学时代的导师。
我和他是在课堂上认识的,我在东京的大学专攻日本史。
就像前面提到的,我的专门是近世经济史。我会选择经济史,其实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我在研究生时代,主要研究近世的海运经济。我也曾经前往古老的世家望族调查,整理塞满整个房间的纪录本。那个时候真的很快乐。
我本来想留在大学的,可是无法实现,我舍弃了成为学者的道路。
现在我在县立的小博物馆担任馆员。我等于是停止自己的研究了,但一样每天接触老东西,几可媲美古物商。我工作的博物馆规模很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收藏,但还是有古文书之类的物品,所以我也习惯整理那类资料了。
我幼年失怙,母亲也在前几年离世了。老家卖掉了,已经拆个精光。我现在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的县南。除了是我的出生地以外,这一带与我几乎是毫无瓜葛了,或许是这一点让我觉得寂寞吧。
所以我才答应了委托。
接到他的来电时,我眼前顿时一片黑。
事到如今他怎么有脸……?
我这么想。不,不对。他果然、果然对我……
恋恋不舍的心情,
不能说没有,我这么想。
我,
喜欢他。我憧憬他,然后,
我们发生关系,有了紧密的连系,然后,
我被抛弃了。不,是我抛弃他吗?不是的。不是什么抛弃被抛弃的问题。男女关系没有高低主从之分,只是我们的关系崩坏罢了。总而言之,我跟他——恩师,完了。
若要说完了,我跟他根本就不应该开始。
他有妻儿,我们是社会上所说的不伦、外遇。
我不想用不伦这种字眼,可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直到研究所即将毕业的这段期间,我和教授的确是这种关系。
可是事情并不顺利。
我想要继续研究,却无法留在大学。不,如果我想留下来,应该可以留下来,也可以去别的大学继续做研究。
但我厌倦了。
所以我回到了故乡,我不想待在东京了,我想离开他的地盘。
我幸运地被当地的博物馆录取。可是我才刚回到故乡,母亲就死了。老家、回忆、一切——我清算了过去一切,展开孤身一人的新生活。
虽然是毫无起伏、低调而凡庸的生活,但我十分安定。只是虽然安定,却有一种失落感般的情绪。
几年过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打电话来了。
愤恨、怀念、憎恶、倾慕、怨怼、希望、不安,还有期待。
我期待些什么?
什么都好。我近乎可笑地一个劲地动摇,可是,那些僵硬的感情波动没有任何意义。那个时候的我,一定就像个搞笑失败的小丑般滑稽吧。
他的声音既不亲昵,也不生疏,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地,平板、明朗、不带私情,那只是大学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过去那段浓密的时光,全都被他当成从未发生过。
我,
只能“是”、“是”地扮演着内向而无能的小职员,在演不下去之前,电话就讲完了。
我半晌无法思考,但还是不知为何打了他告诉我的电话,亲热地对着电话另一头慈祥老公公般的老人寒暄。我想做什么?我无法理解我当时的动机。
也不像是逞强。要说的话,那是一股类似挫败的情绪。
我怀着身体中心灌满了铅般的沉重心情前往故乡的小镇。不,市公所不在平河町,所以如果要求正确,这样的说法是有些误谬的;然而我当时的心情,就像要返回如今已不复存在的老家一般。
当时我……应该觉得厌恶吧。
可是,
集合在市公所储藏室的所有老人,虽然不活泼,但都很随和。那欢乐又不欢乐,感情已经磨灭殆尽般的奇妙聚会,不知何故抚慰了我没来由地变得自暴自弃的心。
也是因为眼中看到的景色有些令人怀念吧,我觉得这种腻人的感情毫无侵入余地的状况也不错。
仔细地查看充满灰尘味及霉臭味的纸堆,和行将就木的老人进行毫无建设性的对话的时间,只有无用也毫无意义的热情空虚漫舞的房间。我想不管经过多久,市史都不可能完成吧。
尽管如此,
我还是固定前往市史编纂委员会。
没有几个月,所有老人对我而言,就已经成了可爱的存在。那个人已经无所谓了,阅读古文献也开始变得有趣了。
不过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虽然也有一些卷轴,但都是知名绘卷的模仿品,怎么看都不是江户时代的东西。而且还画得很差,几乎没有史料价值,做为美术品,也只能说是毫无价值。
江户时期的文书严重遭虫蛀蚀,很多都无法判读。
找到《劫之滨附近的祭祀及俗信》,是半年前的事。
当时我心想:总算挖到可以正常研究的资料了。我也实际前往当地,进行上面记载的史迹的查证工作。因为我认为不能对内容囫圃吞枣,那或许都是创作。可是,什么都没有留下。
那些地方我去过好几次,应该早就知道什么也没有,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然而不管是石佛、祠堂、石头还是松树,什么都没有留下。连记得它们的人都没有。唯一留下的神社,也是昭和中期烧毁后重建的。
即使如此,和古纪录等相比对,还是可以确定位置。这块土地人口过疏,所以也没有经过开发,即使古迹本身消失了,街景也没有大规模翻修过。
照片也是,虽然模糊不清,但还是派上了用场。
那个十字路口百年前有一座小祠堂。
那座小丘战前有一棵大松树。
那条坡道底下会出现黑色老太婆的幽灵。
那栋屋子后面会有鼬鼠升起火柱⑤。
遥想这些,心灵就丰润起来。我也从同一个角度拍摄现在的照片给其他老人看,大家都兴奋得眼睛发亮,我也觉得高兴。虽然这些调查与市史编纂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是,唯有一个史迹,怎么样都查不出地点。
是记载在最后的“夜语神之祠”。
其他史迹有地志方面的详细记述,有些还记下了当时的地址,很容易就能查证到。可是“夜语神之祠”却没有这类资讯,只写了是在业之滨。
业之滨(gouno hama),我判断应该是劫之滨(gouno hama)的误植。
这跟什么都没说一样。
因为旧乡滨村没有那种地方,即使查递整个滨田町也找不到。没有。
不对,
原来是有的。
我感觉应该有的,我知道的。那个……
模糊照片上的地点,我是记得的。
腐朽般的桥。
被岩石与植物围绕的歪扁祠堂。
那是一张粒子粗糙、模糊晕渗,宛如雾气彼方的风景照片,然而我却不知为何,拥有比照片上可以看到的更多的视觉资讯。
我知道,因为我会经……
去过那里。
我会经去过。虽然我完全不记得什么时候、为什么去了。
视野不良的景色。栏干。拟宝珠。明明是淡褐色,却显得黝黑的脚底下的木板。
还有祖母的手掌触感……
这些细节的风景与肤触,不是从这种模糊照片可以感觉得到的。
业之滨有祠也。祭神不明。噤声无语渡一桥,名风桥,心中默念拾圆石,即可知已逝亲人之遗念。然此为邪法、外法之类,一生只得渡桥一次。又,若无能渡桥,亦有殡命之事,或执心不足,将无法复返。为魔所、恶所之类。夜语所指为何⑥,不明。应为夜语,或世语。
——过桥之前,
——不能说话。
——过桥之前,
——只能聆听。
——即使听到,
——也不能答。
原来……那地方是魔所吗?那么祖母去那里做什么?
而且还带着连走都走不稳的幼小的我,去那种令人忌讳的地方做什么?那是……
父亲死后的事吗?
父亲过世,记录上是我两岁时的事。
我当然什么都不记得。父亲的长相、声音还是气味,我都一无所知。
据说父亲是自杀的。
祖父是渔夫,听说父亲不想继承家业,年轻的时候就离家了。他在远方的某地认识了母亲,为了成婚而回到故乡。这是我听母亲说的。她告诉我,父亲换了好几个工作,但总是不顺利,当然跟老家的人也处不好,终于过不下去,选择了死亡。
父亲死后,照顾我和母亲的是祖父母。厌恶家业,抛弃父母和老家离开的儿子,即便死了也不能原谅,但媳妇和孙女是无辜的——是这个意思吗?
话虽如此,还是有许多争端。
母亲和祖父母处得不好。
姑且不论沉默寡言的祖父,祖母似乎和母亲彻底不和。
直到祖母过世,母亲连一次都没有笑过。
我觉得就是会这样的。
祖母人很严厉,我也照三餐挨骂,一次又一次挨打。母亲似乎是为了不给祖父母添麻烦,拼命工作;但不管拿多少钱给家里,再怎么努力地做家事,似乎还是无法让祖母满意。祖母吼母亲的声音,就是叫醒我的闹钟。母亲在睡床上啜泣的呜咽声,是我的摇篮曲。
可是母亲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苛责、被怎么样不讲理地挑毛病,都绝对不会忤逆祖母。
祖父待我很好,但和母亲几乎不说话,感觉是尽量避免和她有所接触。
不……祖父跟祖母也不怎么说话。我想他们两人应该也处不好吧。祖母只要看到祖父对我好,脸就会立刻垮下来。家里无时无刻是剑拔弩张,绝对称不上是个明朗的家庭。不,我成长在彻底阴暗的家庭里。
祖父过世,是我小学三年级的事,三年后祖母也走了。
后来母亲便开始露出像人的表情来了。
即使在临终之际,祖母仍旧口出秽言地责骂照护她的母亲。
看在即将升中学的我眼里,祖母根本就是个鬼婆。
听我这么说,母亲却否认说:
——不是那样的。
什么不是那样?我不明白。祖母过世的时候,母亲悲伤地哭泣。我不懂她在想什么。我真心觉得祖母的死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我实在太痛恨她了。但与其说是痛恨,其实更接近害怕。我从来没有祖母对我好的记忆。我记得的全是她对我和母亲的唾骂,以及挨祖母打时脸颊的疼痛。全是这样的记忆……
然而,
我却会怀念祖母。
祖母有什么让我怀念的回忆吗?
我记得的全是些厌恶的事。
因为是塞满了那种讨厌回忆的老家,在母亲过世之后,我立刻就卖掉了。不到三个月,那里就被铲平,盖起了公寓。已经面目全非了。我觉得爽快透了。照理说应该是爽快透了。然而,我却也感到寂寞。
明明没什么好寂寞的。
看来自从和他分手之后,
我变得十分不稳定。
话说回来……
我是和我痛恨的祖母一起去那里的,我好像跟她手牵着手一起走。
而且……
还是走在魔所。我们究竟是去做什么的?那张模糊照片上的地点是……
哪里?
——夜语神。
是夜语还是世语?哪里都找不到这样的地名。我滴水不漏地查遍了,但没有找到。
那是上星期的事,一名老人在实际上是储藏室的市史编纂室提到了这样的事:“这么说来,很久以前,我会经听说过岬角的后头有黄泉的入口还是什么的。”
“你是说梵之端后面吗?是那个像岛一样的地方吧?那里不是赛之河原⑦吗?”
“不是不是。那里是……”
——抛却烦恼的地方。
老人这么说。抛却烦恼的地方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喏,不是说下地狱的死者要在阎魔大王面前招出生前做过的坏事吗?然后依生前的罪状决定刑罚,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些要在地狱偿还的罪业恶业啊……”
会变成浑圆的石头,
噗通,噗通地。
“喷出现世,然后被扔掉。应该就是罪状,或者说类似罪业的东西吧。人的烦恼的数目有一百零八个,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