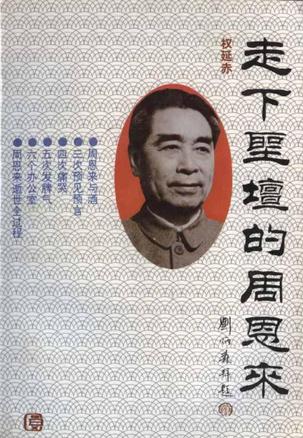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
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
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
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
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
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
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
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
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
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
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
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
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
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
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
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
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
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
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60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
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
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
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
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
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
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
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十、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思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思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思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