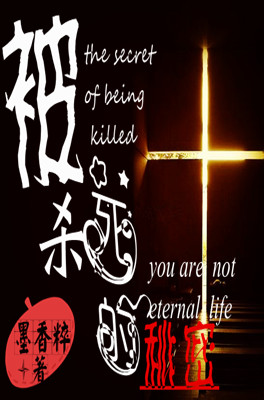杀死一只知更鸟-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太火了,摇不动了。”他说。
“你不在乎他会出什么事,”我说,“他那么干都是为了你,而你却让他出去遭人枪击。”
阿迪克斯把我的脑袋按到他下巴下面。“还不是担心的时候。我从没料到杰姆会在这样的问题上失去理智——原以为会给我找更多麻烦的是你。”
我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保持冷静,学校里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要为什么事保持冷静。
“斯各特,”阿迪克斯说,“到了夏天会有更糟糕的事,那时,你更要冷静……我知道这在你和杰姆看来是不公平的,但有时候,我们要善处逆境,而且在紧要关头我们的行为应该是——好吧,这方面我不多说了,我能够说的是,等你和杰姆长大后,可能会带着怜悯的心情和某种感情来回顾这件事,你们会觉得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心愿。这个案子,这个汤姆?鲁宾逊的案子触及到人的天良——斯各特,如果我不尽力帮助那个人,我就没有脸去教堂做礼拜。”
“阿迪克斯,一定是你错了……”
“怎么我错了?”
“啾,大多数人好象认为他们是对的,你是错的……”
“他们当然有权这样认为,他们的看法有权受到尊重,”阿迪克斯说,“但是,在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之前,我首先得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大多数人公认的准则是应当遵守的,但如果这样做违背了一个人的良心,就不应当遵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不遵守。”
杰姆回来时我还在阿迪克斯的膝上。“怎么样,孩子?”阿迪克斯问。他放下我。我暗暗地把杰姆上下打量了一番,看来他虽安然无恙,脸上的表情却挺奇怪。可能是杜博斯太太给他吃了一剂甘汞吧。
“我替她打扫干净了,说了对不起,但心里并不这样认为,我还说每个星期六我会去照看那些山茶花,让它们尽快恢复原样。”
“如果你心里不通,嘴里说对不起是没用的。”阿迪克斯说,“杰姆,她老了,又有病。她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该计较。当然,我宁愿她对我说那些话,而不是对你们俩蜕,但是我们不可能事事如意。”
杰姆好象被地毯上的一朵玫瑰花迷住了似的。“阿迪克斯,”他说,“她叫我读书给她听。”
“读书给她听?”
“是的,爸爸,她要我每天下午放学后和星期六过去为她大声读两个小时的书。阿迪克斯,我得去吗?”
“当然。”
“可她要我读一个月。”
“那你就读一个月嘛。”
杰姆的大脚趾轻轻踩在玫瑰花的中间,往下压。最后他说:“阿迪克斯,在人行道上没关系,但是屋里面——黑乎乎的,怪吓人的。天花板上有些影子和舄IJ的东西……”
阿迪克斯严厉地一笑。“那可会激发你的想象力。就假设你们是在拉德利家嘛。”
星期一下午,我和杰姆爬上杜博斯太太门前的台阶,穿过她家的过厅。杰姆手里拿本※艾凡赫〃,脑子里装着深奥的知识。他敲敲左边的第二扇门。
“杜博斯太太?”他喊道。
杰西打开木门然后开开纱门。
“是杰姆?芬奇吗?”她问,“你和妹妹一起来,我不知道……”
“让他俩都进来,杰西。”杜博斯太太说。杰西让我们进来后,就到厨房去了。
我们跨过门槛,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这种气味我在那种被雨水冲洗过多次的旧房子里闻到过,那种房里常有煤油灯,舀水的勺子,没漂白的家织被单。一闻到这种气味我就害怕,就特别警惕,老想着会出事。
墙角上有张钢床,床上是杜博斯太太。我不知道是不是杰姆把她气得卧床不起的。突然问,我有点同情她了。她身上盖了几层被子,看上去似乎还友好。
床边有个大理石面的洗脸架。上面有个玻璃杯,里面有只茶匙,架上还有个红色的洗耳器,一盒脱脂棉花,一个有三条小腿的闹钟。
“看样子你把那个不讲卫生的妹妹带来了,是吗?”这是她的第一句话。
杰姆轻轻地说:“我妹妹讲卫生,我也不怕你了。”可我看见杰姆的膝盖在颤抖。
我想杜博斯太太会唠叨一阵,但她只说了旬:。你可以读了,杰里米。
杰姆坐在一把藤椅上,打开《艾凡赫》。我拖过另一把藤椅,在他边上坐下来。
“坐近点,”杜博斯太太说,“到床边上来。”
我们把椅子移上前去。我从没有跟她挨得这么近过,实在想把椅子往后移。’
她很吓人。脸是脏枕套的颜色,嘴角因为有唾沫而发亮,唾液象冰川似的顺着下巴上深深的皱纹慢慢流动。脸上布满了老年斑,灰白的眼睛里有针尖大的黑色的瞳孔。手上有很多疙瘩,指甲上长了一层薄膜。她没戴下面的假牙,上嘴唇向外突出。隔一会儿,下嘴唇和下巴就要一起向上动一动,这一来,唾沫流动得更快。
我只在不得已时才看她一下。杰姆又一次打开书,开始读起来。我想跟着他看,但他读得太快。杰姆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但杜博斯太太听得出,让他停下来把那个字拼出来。杰姆读了大约有二十分钟,这期间,我时而看看煤烟熏黑的壁炉,时而看看窗外,反正不看她就行。我发现杰姆越往下读,杜博斯太太纠正的错误越少,杰姆有时甚至省去了一整句没念。她早不在听了。
我朝床上看去。
她有些不正常。仰面躺着,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只能看见头和肩膀。头缓慢地从一边倒向另一边。隔一会儿,嘴就要张得大大的,我可以模糊地看见她的舌头在微微地起伏。嘴唇上不一会儿就堆起了一条条的唾液,她暖进去,然后再张开嘴。她的嘴好象有独立的生命,能和身体内外的其他器官分开工作,就象落潮时的蛤蜊一样。偶尔,她嘴里发出扑哧声,好象什么粘东西正在开始沸腾。
我拉拉杰姆的袖子。
他看看我,再看看床上。杜博斯太太的脑袋有规律地不时摆向我们一边。杰姆说:“杜博斯太太,您不舒服吗?”杜博斯太太没听见。
突然,闹钟响起来了,把我们吓呆了。不一会儿,我们已经在人行道上往家里走了,神经还绷得紧紧的。我们不是逃出来的,是杰西打发我们走的:闹钟声还没停,她就到了屋里,把我和杰姆往外推。
“嘘!”她说,“你俩都回去吧。”
杰姆在门口犹豫了一下。
“她该吃药了。”杰西说。门关上时,我看见杰西很快朝杜博斯太太床边走去。
我们到家时才三点四十五分,所以我们在后院踢了一会儿球,才去接爸爸下班。阿迪克斯给我两支黄色铅笔,给杰姆一本橄榄球杂志。我想这是对我们和杜博斯太太第一次约会的不加说明的奖励。
杰姆跟他讲了在那儿的经过。
“她吓着你了吗?”阿迪克斯问。
“没有,爸爸,”杰姆说,“可是太Hq人作呕了。她好象一阵阵发病似的,老吐唾沫。”
“她也是没办法。病人的样子有时候是不讨人喜欢的。”
“她可把我吓坏了。”我说。’
阿迪克斯从眼镜上面看看我。“你用不着跟杰姆去嘛。”
在杜博斯太太家的第二天下午跟第一天一样,第三天也一样。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固定的程序:开始一切正常——就是说,她首先和杰姆谈一阵她喜欢的话题,她的山茶花啦,我们爸爸为黑鬼帮腔的怪癖啦,她的话逐渐减少,然后不和我们说话了。接着闹钟响起来,杰西把我们“嘘”出去。剩下的时间就是我们的了。
“阿迪克斯,”一天晚上我问,“什么叫为黑鬼帮腔?”
阿迪克斯脸色阴沉。“有谁这佯说你吗?”
“没有,爸爸,杜博斯太太这样说你。这是她每天下午的开场白。去年圣诞节弗朗西斯这样说我,那是我第一次听到。”
“你是为这个揍他吗?”阿迪克斯问。
“是的,爸爸……”
“那为什么还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对阿迪克斯解释说,把我惹火的与其说是他说话的内容,不如说是他说话的神态。“好象他在说我们很下贱似的。”
“斯各特,”阿迪克斯说,“说人家为黑鬼帮腔和说人家下贱一样,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话。这是很难解释的。没有知识的、下贱的人,认为有人站在黑人一边反对他们时,就这样说。他们要找一个粗鄙的、难听的说法来污蔑某人时,这种说法就是指我们这种人。”
“你并不真的喜欢黑人,是吗?”
“我当然真的喜欢。我尽最大的努力爱每一个人……我有时处境不利……孩子,被人加上有人认为是很难听的称号并不是侮辱。这只说明那个人太可怜了,对你并无损害。所以,别对杜博斯太太发火。她本身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下午,杰姆正吃力地读着沃尔特?斯各特爵士(这是杰姆的叫法)的作品,杜博斯太太每次都要纠正他。这时,有人敲门。“进来!”她尖叫一声。
进来的是阿迪克斯。他走列床边,拉起杜博斯太太的手。“我刚从事务所来,没见列孩子,我猜想他们会在这儿。”
杜博斯太太朝他笑了笑。她看起来那么恨他,我真不知道这时她怎么有脸跟他说话。“你知道几点了吗,阿迪克斯?”她问,“五点十四分。闹钟五点三十分响,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
我突然想起我们在杜博斯大太家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闹钟每天都比前一天晚几分钟响。前一段,到铃响时,她已痉挛了一次。今天,她已跟杰姆罗嗦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还没有要痉挛的迹象。我觉得上当了。闹钟是我们离开的信号,如果哪一天钟不响了,我们可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约好杰姆读书的时间要完了。”阿迪克斯说。
“我想只延长一个星期。”她说,“目的是为了保证……”
杰姆站起来说:“可是…“一”
阿迪克斯伸手拦住他,杰姆不做声了。回家的路上杰姆说,原来讲好只读一个月,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太不讲理了。
“再读一个星期,孩子。”阿迪克斯说。
“不。”杰姆说。
“要读。”阿迪克斯说。
下一个星期,我们仍旧每天去杜博斯太太家。闹钟已经不响了。等杜博斯太太说“够了’时,我们才可以回去。所以,我们到家时阿迪克斯已在看报了。尽管她不再痉挛了,但在其他方面还是老样子:每当沃尔特?斯科特开始较长地描写护城沟和城堡时,杜博斯太太就不耐烦了,就开始挑我们的岔子。
“杰里米?芬奇,我说过你捣坏我的山茶花会后悔的。你现在后悔了吧?”
杰姆也就说他当然后悔了。
。你以为会把我的‘银边翠’弄死吗?杰西说你捣坏的山茶花又长起来了。下次你会知道怎么办了,对吧?你会连根拔掉,是吗?”
杰姆想说他当然会。
“你这小子别跟我吞吞吐吐的!抬起头说是的,太太。可我想,因为你爸爸是那么个人,你会感到抬不起头。”
杰姆就抬起下巴,毫无恶意地看着杜博斯太太。几周来,杰姆学会了一种彬彬有礼、漫不经心的表情,来回答她的那些听了使人血都会凝固的凭空的捏造。
总算熬到头了。一天下午,杜博斯太太说“够了”后,又加了一句“到此结束了,再见”。
终于结束了。我们高兴地连蹦带跳来到人行道上,边跑边叫,好象卸下个大包袱。
那年春天挺合我们心意:白天越来越长,我们玩的时间越来越多。杰姆在忙着收集全国各高等院校橄榄球队队员的主要资料。每天晚上阿迪克斯都给我们读报上的体育消息。从亚拉巴马州球队队员候选人来看,亚拉巴马今年可能又会去参加加州玫瑰杯大学橄榄球赛,这些候选队员的名字我们一个都不会读。一天晚上,阿迪克斯刚读了一半温迪?西顿的专栏文章,突然电话响了。
他接完电话后,走到过厅内的帽架前说:“我去杜博斯太太家看看,用不了多久,一会儿就回来。”
可他去了很久,我上床睡觉的时问早过了,他还没回。他回来时带回、一盒糖果。他在客厅内坐下来,盒子放在椅子边的地上。
“她叫你去干什么?”杰姆问。
我们已有一个月没看见杜博斯太太了。我们路过她家时,她从不在走廊上。
“她死了,孩子,几分钟前死的。”阿迪克斯说。
“噢,”杰姆说,“好。”‘
“死了是好,”阿迪克斯说,“免得多受罪。她病了很久,孩子,你知道她一阵阵痉挛是什么原因吗?”
杰姆摇摇头。
“杜博斯太太用吗啡上了瘾。”阿迪克斯说,“她把吗啡当止痛药用了好几年,医生让她用的,她本来可以用吗啡一直到死,而且不致死得那么痛苦,可她太固执了……”
“爸爸,是怎么一回事?”杰姆间。
阿迪克斯说:“就在你那次恶作剧之前,她喊我去立遗嘱。雷纳兹医生告诉她只剩下几个月了。当时她的生意情况很好,但她说:‘还有一件事不正常。”’
“什么事?”杰姆迷惑不解地问。
“她说她离开这个世界酌时候要不托任何事的福,不叨任何人的光。杰姆,如果你象她那样重病在身,也许会认为只要能减轻痛苦,不管用什么药都是无可指责的。但她不这样认为。她说要在死之前戒掉吗啡,她说到做到了。”
杰姆问:“你是说她一阵阵痉挛就是这么回事吗?”
“是韵。你给她读书的大部分时间,我怀疑她一个宇都没听。她的全部精力和身体都集中在那个闹钟上。即使你没落在她手里,我也会让你们去给她读书的。。读书也许可以分散她的注意力。还有一个原因……”
“她死时无忧无虑吗?”
“象山上的空气一样自由自在。”阿迪克斯说,“差不多直劲最后一刻她都是清醒的。是清醒的,”他笑了笑,“脾气还很坏。她从心眼里反对我的一些做法,还说我很可能要花我一生剩下的时问不断地把你从牢狱里保释出来。她叫杰西绐你准备了这个盒子……”
阿迪克斯伸手拾起那个糖果盒子交给杰姆。
杰姆打开盒子,里边用湿棉花围着朵又完好又水灵的白色山茶花。这是朵“银边翠”。
杰姆气得几乎眼睛都瞪出来了。“老鬼,老鬼,”他叫着把花扔到地上,“她为什么总不放过我?”
阿迪克斯很快站起来,杰姆把头埋在阿迪克斯衬衣的前襟里。“嘘,”阿迪克斯说,“我看她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现在一切都好了,杰姆,现在一切都好了。你知道她真是个了不起的有教养的女人。”
“有教养的女人?”杰姆抬起头。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