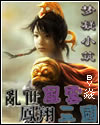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于塞瓦斯托波尔的用途,苏联时期没有作过任何修改。1944年5月10日,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以命令形式宣布,我国军队“……已占领黑海上的要塞和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市”。由此可见,苏联最高当局也确认了塞瓦斯托波尔作为要塞和海军主要基地的地位。
1948年,我国政府通过了“关于恢复塞瓦斯托波尔市和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决议,确定该市拥有以前的市行政边界,以及相应的塞瓦斯托波尔卫戍区边界。决议要求加速恢复塞瓦斯托波尔为“头等海军要塞”,享有特殊地位,并下令“将塞瓦斯托波尔市划为共和国直辖市”。因此,作为主要基地的军事行政单位,其市级民事行政机构由当时起也划归莫斯科直接管理。
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8年10月29日通过,将塞瓦斯托波尔市划为独立经济行政中心,预算单列。实际上,从这时起,克里米亚州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便管不到塞瓦斯托波尔这片地方了。
塞瓦斯托波尔市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单位都间接地属于俄罗斯联邦政府各部委。统计工作也是单列的。比如有报道说:“1951年第一季度克里米亚州工业生产完成计划 104.3%,塞瓦斯托波尔地区完成 100。6%”。
如果从苏维埃这条线来看,塞瓦斯托波尔市同克里米亚州各自都是独立的存在,有特殊的户籍管理和准入制度,那么从市的党组织这条线来看,根据苏联共产党按地区和生产部门建构的原则,该市归克里米亚州党组织管辖。这是国内所有地区通行的原则。军队也好,对外不开放的城市也好,特殊单位也好,不管隶属于谁,党的系统均归地方党组织统一进行政治管理。
1954年克里米亚州移交乌克兰后,党的克里米亚州委(相应的还有党的塞瓦斯托波尔市委)均改属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管理。这导致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非军事行政机构也要单方面改变没有法律根据的系统归属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苏共在历史上形成的作用,党的许多机构在很多方面都取代了国家机构和国民经济机构。顺便说一下,这正是这位克拉夫丘克和“鲁赫”分子声嘶力竭地予以揭露的状况!
然而,乌克兰虽在塞瓦斯托波尔确立了事实上的市政管理,但却并不意味该市居民自动失去俄国国籍,根据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他们应该拥有俄国国籍。
根据苏联宪法,国防功能是苏联及其国家政权最高机关专有的特殊权力。因此,塞瓦斯托波尔这个黑海舰队主要基地从属全苏的特殊地位无论如何也没有改变,该基地始终应受苏联管辖。有关塞瓦斯托波尔国防生产发展的一切决定,均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对发展市区经济和住宅建设,均按苏联各部系统,首先是国防部系统,实现基本拨款。
由此可以明确看出,塞瓦斯托波尔作为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特殊地位,已为文件所证实,它从未交付给乌克兰,而苏联的继承人则是俄罗斯联邦。因此,有一切根据可以证实,俄国对以1991年塞瓦斯托波尔市占有土地状况为界的黑海舰队主要基地拥有主权。试图人为地把“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这两个概念分开,在方法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1995年以前,俄国同乌克兰谈判时总是坚持“俄国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准确说法。然而在1995年6月9日索契协议中,却出现了一个原则上完全不同的说法,即“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位于塞瓦斯托波尔”,这使乌克兰对文件作出有损于俄罗斯联邦的解释。
这便是有关当前这一迫切问题的某些事实材料。毫无疑问,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证明,此前作出的种种决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但是已经干过的事情,从历史上是抹不掉的。总不能从历史上抹掉别洛韦日之夜干下的那些勾当吧!既然干了,那历史名城塞瓦斯托波尔的问题和黑海舰队的问题,便是那个夜晚造成的悲惨结果之一。
但是应该记住,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时,也承认过必须建立对战略力量的统一指挥,对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留统一监控权。而且“战略力量”这个术语还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在这个具体情况下,黑海舰队是全苏海军的一个战略性行动分支,它应从南方海域保卫独联体。必须强调一点,管理和生活保障基础设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战略性行动单位。任何试图分割舰队的做法就意味着将舰队消灭。
远在1992年,俄国海军领导便提议帮助乌克兰建立自己的舰队,甚至简要提出了乌克兰建立这支舰队应解决的一些任务。但这些想法只作了预先讨论,后来并没有进一步展开。
在我看来,促使乌克兰领导与俄国对峙的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便是克里米亚。1991年1月20日克里米亚实行全民公决,问题是:“您赞成恢复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作为苏联主体之一和同盟条约参加者的地位吗?”有 82%居民参加全民公决,其中 93%的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态度,占有投票权的克里米亚人的3/4。
全民公决的结果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所认可,它颁布了“关于恢复克里米亚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法令。由此可见,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与当时构成统一国家苏联的其他主体一样,也拥有独立加入国家法律关系,签订条约加入同盟的权利。
1991年3月 17日全苏全民公决时,半岛居民中有87%的人表示赞成保留苏联,以作为更新后的平等主权共和国联邦。
1991年9月4日,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克里米亚国家主权宣言”,但乌克兰于1992年4月 29日通过的“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的法律,却大大限制了它的权利。
1992年 5月通过了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该宪法引起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抨击,同时亦未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
同年5月末,以最高苏维埃为代表的俄国立法当局,听取了专门委员会就1954年的决定进行法律评估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完全根据现行国际法准则,以维也纳公约为依据,起草并通过决议,认为将克里米亚州由俄联邦转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定违反宪法,应予废除。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意见分歧,在俄国完全放弃谈判的情况下,导致出现了长期政治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政府于1995年8月份作出了“关于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解决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民族问题的措施”的决定。当时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危机状态,而这种危机又因为以前被驱逐出境的公民及其后代回迁克里米亚而造成半岛上的危机状况大大加剧。但就整体而言,这个决定的目的并不是要克服经济困难,而是要建立族群方面的“同盟军”。因为所谓“原住”居民,包括的主要是1945年以后移居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伊姆人、克里米亚犹太人;而所谓“非原住”居民,则是指俄罗斯人等其他人。
此外,作出这些决定,是希望从立法层面上巩固克里米亚鞑靼人国民会议在乌克兰的特殊地位,使其进入乌克兰的政治法律范围。乌克兰政府的决定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被驱逐出境的民族,首先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必须有自己的代表进入行政机构,即明显地表示,希望能在多民族地区按多民族原则建立政府。
这样,基辅力图改变半岛的族群政治格局,希望在未来历史上把克里米亚共和国变成乌克兰版图内的克里米亚鞑靼国。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有考虑到当前泛突厥主义的倾向,也没有考虑到这些行动对乌克兰和整个黑海沿岸地区可能造成的后果。
乌克兰领导在这一问题上缺乏远见的政策,清楚地为不应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东西所证实。我有意使用“不应该”一词,是因为有些题目的确不该受到国家鼓励。其中首先包括那些可以挑起民族仇恨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上,我不能无根据地杜撰,何况我对乌克兰人民还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有许多乌克兰朋友,同他们一起,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光。
《克里米亚之声》报是乌克兰议会出版的报纸《乌克兰之声报》的附录。1997年《克里米亚之声》刊登了历史科学博士沃兹格林的系列文章。这些东西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使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不得不因此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其中特别指出:
……该文同沃兹格林前所发表有关克里米亚的文章一样,其特点为公开仇视斯拉夫,反对俄罗斯,缺乏科学态度,刻意歪曲和直接篡改事实,充满事实错误,表述极为不准确。
……沃兹格林继纳粹空想家希特勒、希姆莱、戈倍尔、罗森堡等人之后,鼓吹某些民族具有与生俱来的恶劣品质,认为是由这些品质决定了这些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也决定了这些民族的个别代表人物和某些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沃兹格林与自己的思想先驱不同,他并不认为犹太人是天生的敌人,而是把许许多多“源于民族内心深处的”恶劣品质强加到斯拉夫民族,首先是俄罗斯民族头上。他的文章着重论证一种思想,认为斯拉夫民族具有无端发动侵略、性喜扩张、力图压倒和消灭其他民族等危险和恶劣的品质。作者一贯鼓吹斯拉夫人和克正米亚鞑靼人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的思想,鼓吹他们的文化在克里米亚具有激烈的对抗性。
克里米亚议会领导致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呼吁书中写道:“鉴于此类能够挑起民族纷争,挑起对俄罗斯人民以及居住在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仇恨的行为,不仅可能发生在沃兹格林身上,而且可能发生在俄罗斯联邦其他科学工作者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故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向各位呼吁,要对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个别国家工作人员、科学机构和科学工作者旨在挑起民族不和,并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其他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地区各国挑起反斯拉夫、反俄情绪的活动加以分析。”
这种“科学”分析的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而且,这样的“理论”基础还要加上基辅当局的政策。
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怀着狂喜的心情欢迎首批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遣送回国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乔尔诺维尔说:“这是一股可以帮助我们把所有俄国人赶出自治区的力量。”
一年年过去,现在可以说,他是对的。克里米亚鞑靼族代表团在乌克兰总统身边设有代表,它在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积极鼓吹分裂主义政策。任务明确而又公开:建立克里米亚鞑靼国,接受土耳其庇护,脱离乌克兰。
口号是:“这是我们先人的土地,我们是它的主人,而你们现在是外来户。”这一口号正在被坚定不移地强行加以推行。肆意强占土地,制造大规模混乱,殴打具有斯拉夫体貌的人,包围政府大楼。当局表现出(我认为是故意的)无能为力。只有少量刑事案件能够得到法院审理。极有可能是出于对俄国人盲目仇恨,乌克兰当局同意将克里米亚交给克里米亚鞑靼人,在那里建立一个对乌克兰“友好”的国家。
看到克里米亚发生的种种事件,看到克里米亚鞑靼人好斗的立场及乌克兰当局对此事的态度,使人不由得要去翻阅我国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方为自身安全,不得不按族群隔离与敌对国家氏族同种族的人员。英国对日耳曼人,美国对日本人都是这么做的。苏联的日耳曼人从国家欧洲部分被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
除此之外,众所周知,在红军解放了一度被德国占领的领土之后,克里米亚鞑靼人,还有北高加索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几个民族,因为一度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被迁徙。
后来,苏联的政治领导对斯大林的行为做了评价,谴责了他的这些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惩罚的是整个族群,而不是犯罪的具体罪犯。被强制迁徙的民族获准迁回自己的原居住区。但这并不意味国家在极其残酷的战争条件下作出这种事是庸人自扰。比如,我手头有一部多卷本20世纪世界战争 ),第4卷中有一份1944年5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致国家国防委员会斯大林的报告称:
经调查和由情报途径得知,并通过当地居民声明获悉,克里米亚鞑靼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积极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合作,并进行反对苏联当局的斗争……
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在由德国和土耳其回国的白卫军穆斯林侨民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所谓“鞑靼民族委员会”,下设分支机构,该委员会在克里米亚所有鞑靼地区均设有分部。
“鞑靼民族委员会”广泛协助德国人利用逃兵和鞑靼青年,组建鞑靼军队、讨伐队和警察部队,开展反对红军部队和苏联游击队的行动。在充任讨伐队员和警察时,鞑靼人表现得特别残酷。
在克里米亚地区,德国侦察机关在鞑靼人积极参与配合下,在准备和向红军后方投放特务及破坏分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鞑靼民族委员会”同德国警方一道,积极参与组织并为德国掳掠了 5万余苏联公民,在居民中为德军募集资金和物资,对当地非鞑靼居民进行大规模告密活动,千方百计欺压非鞑靼居民。
“鞑靼民族委员会”的活动得到鞑靼居民支持,德国占领当局向鞑靼居民提
供各种优惠和奖励。
现在时代变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同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乌克兰人的斗争同60年前不一样了。但应该知道历史,并从历史教训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对历史不能加以报复,不能像目前在克里米亚做的那样。否则我们会走得太远,钻进死胡同。
同俄罗斯对峙的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追求可对欧洲政策产生影响的大国地位。这件事暂时既无经济条件,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