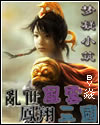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俄罗斯对峙的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追求可对欧洲政策产生影响的大国地位。这件事暂时既无经济条件,亦无政治条件。现在乌克兰正试图宣布自己为海洋大国,虽然在退出苏联之前从未拥有过一支舰队。
这样一来便决定了黑海舰队在乌克兰军事政治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黑海沿岸有6个独立国家(土耳其、格鲁吉亚、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各国为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严重的军事冲突。
1991年以后,俄罗斯将自己的舰队调离地中海。虽说美国在那里已没有实际的对手,即我国军舰,但第六舰队仍以意大利为基地,掌控着地中海的整个军事政治形势。由黑海经由海峡的出口实际上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但为了对黑海地区各国施加影响,美国还必须对经由海峡进入黑海的入口进行掌控。
因此,作为我国舰队基地的塞瓦斯托波尔,就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海上占有极为优越的位置。根据战略计算,塞瓦斯托波尔通向各方的距离都相等,驻在这里的海上军事力量可以控制整个黑海地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第6舰队舰只曾不止一次试图在黑海上展示其旗帜,但由于黑海舰队的积极对抗,终使此事受阻。现在,美国一些政治家和海军将领声称,黑海是美国的生存利益地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想方设法吸引前华沙条约缔约国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不能忘记土耳其不断增长的海上军事潜力,而且它的身后还有美国第6舰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几支舰队做后盾。
黑海战略方向的作用与地位可用历史上的两个实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土联军在海上刚刚取得优势,而俄军指挥部门对舰队在冲突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估计不足,于是战争就打输了。尽管在锡诺普和卡尔斯都打了胜仗,尽管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进行得很英勇,但战争还是输掉了。
第二个例子:18世纪俄国为了保卫南部疆界,打通出海口,与土耳其曾进行无尽无休的战争。比如,1768—1774年战争期间,步兵在鲁米扬采夫指挥下采取打击土耳其行动的同时,还大规模展开了一次大胆策划的机动行动,其创意者是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他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一个向希腊群岛地区派出一支海上考察队,从南方向奥斯曼帝国领地发起进攻的想法。俄国舰队的几支分舰队在那边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其中包括切什梅胜利,实现了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包围,保证了对俄国有利的库丘克—凯纳尔吉和约的签署。
这是历史,这段历史说明,在任何条件下俄国政府均不能低估黑海战略方向对国家民族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
根据国家杜马代表、独联体事务及与同胞联系委员会成员的倡议,经过首届国家杜马向主要军事专家咨询,结论认为在塞瓦斯托波尔水域,俄罗斯黑海舰队不可能与乌克兰海军共用一个基地,并于 1995年 4月通过联邦《暂停单方面削减黑海舰队法》,但于1995年5月份被联邦院否决。
同年10月,国家杜马通过《关于暂停单方面削减和黑海舰队保障供给法》,也被联邦院否决。1996年2月第二届国家杜马克服了联邦院的否决,但法案被总统退回,未予审理。国家杜马坚持必须通过这部法案,并多次指出,黑海地区对保证俄国在南方的地缘政治稳定具有关键意义。
1996年4月,在总统大选选战正烈之际,俄联邦总统下令,暂停分割黑海舰队,因为乌克兰方面试图把一个不能被接受的表述强加给俄罗斯,即把港区同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所有基础设施分割开。看来,是有人提醒叶利钦,他是宪法的“保障”,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因此,有责任捍卫俄罗斯的民族利益。
我认为,由俄联邦总统和乌克兰总统签署的关于分割黑海舰队的索契协议,规定这两个国家的海军拥有单独的基地,但协议为乌克兰单方面破坏。尽管乌克兰方面在敖德萨、奥恰科夫和其他地方拥有很不错的海军基地,它依然坚持要让自己的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拥有基地。两国海军在同一塞瓦斯托波尔湾拥有基地,从军事观点来看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乌克兰海军随时可将我国舰队包围起来,削弱其生活保障体系,削弱俄罗斯武装力量战略行动统一体的活动能力。
从 1992年1月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就分割黑海舰队问题共签署了8个协议和议定书,其中包括索契协议,但其中任何一个均未提交议会批准。
这种做法是与联邦法律相抵触的。根据联邦法律,凡涉及俄联邦国防能力以及武装监督问题的条约,均必须得到批准。
1997年5月末,签署了一个“大条约”,即俄罗斯乌克兰友好合作条约。我已经谈过,签订这项条约的谈判延续多年,原因是困难不小。
这个“大条约”签订了,可两国都得到了什么?有必要把作为条约基础的三个基本问题开列出来,这就是:分割舰队的问题,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租赁条件的问题,交付给俄国的舰只的偿款支付方式和基地租金的支付条件问题。
第一个问题:乌克兰分得了略少于20%的舰队,而俄罗斯回购其余的舰只大致要花5亿美元。此数将从乌克兰欠俄国的债款中扣除。第二个问题:俄国租赁塞瓦斯托波尔湾、卡拉奇亚湾和卡兰京湾,租期20年。第三个问题:莫斯科应支付这些基地20年的租金,共25亿美元。支付的办法是乌克兰用由俄罗斯获得的石油和天然气抵债。
乌克兰违背了1995年的索契协议,拒绝接受两支舰队分别拥有基地的原则,不承认塞瓦斯托波尔是黑海舰队的基本基地。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引发市内和港口水域的经常性冲突。但这个条约对乌克兰、对它亲西方的精英人物十分有利,因为从国际法的层面来看,条约可加强乌克兰现今边界的地位,巩固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归属于乌克兰的事实。签订这样的条约,留下不少未决的军事和社会问题。
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成了两国之间复杂的政治问题中的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制约因素。2005年末,当掀起了一场“天然气”战争——俄国决定提高供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时,乌克兰当局立即对此发表声明,提出将重新审议俄国黑海舰队租用基地的经济条件。有的人还不喜欢我国水兵和塞瓦斯托波尔居民的某些行为,于是便开始抢占俄国灯塔,等等。
我想,不能认为这个条约确实解决了俄国和乌克兰相互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在某些方面,这个条约甚至还加重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只能在两国开始由旨在恢复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的政府执政的情况下,方能得到解决。只有到那时,俄国和乌克兰相互关系中所有凭空臆造的问题方能消失。
就整体而言,俄国不仅必须坚定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且还应当考虑到黑海地带出现的崭新军事政治形势。通过土耳其和乌克兰,西方和美国正在一步步实现把俄国从黑海地区实际上挤出去的目标。同时,北约在该地区海上的军事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涨:举行一次又一次的演习,利用空军对海上交通线实行控制。派空降部队在海岸登陆。这不仅仅是演习,也是深入侦察:对该战略地区开展研究,搜集雷达设备的情报,揭示观察防御系统的“盲区”,等等。
由此可见,目前俄国南方直接与北约擅自划分的责任地带相毗连,这种情况十分严重地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对俄国极为不利,使欧洲裁减军备的成果化为乌有。同时还要考虑到,没有黑海舰队及其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密切配合,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的步兵军团便无法保证俄国国家利益得到可靠的保卫。
控制黑海区域可以保证俄国的经济安全,因为黑海起着把能源由亚洲向欧洲出口的世界交通要道的作用。俄国地位在这一地区的削弱,可使国际恐怖组织积极利用该地区运输武器、毒品,在国内挑起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
我看,这些就是制定俄国黑海地区政策时应考虑的基本因素。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复杂问题,俄国和乌克兰的民族关系问题,都不应该使这两个兄弟民族不睦。大家本是同根生,从历史角度来看,应当同舟共济。统治者来了又走,而人民却永世长存。
乌克兰人民开始觉悟了。“橙色”革命引起的狂喜,已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人们很快弄明白,他们又一次上当受骗了。
2006年夏季克里米亚发生的一些事件,最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根据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决定,2006年6月在费奥多西亚地区将举行一次有北约参加的在“和平伙伴”框架内的演习。但是北约官方代表詹姆斯?阿帕图罗伊声称,这次演习同正在克里米亚进行的代号为“C伯里塞—2006”的演习以及美军和美国物资运抵半岛均无任何关系。
克里米亚因此以费奥多西亚为中心爆发了严重的反北约和反美活动。纠察队无限期地封锁了费奥多西亚港口。美国军舰将装备和武器运到这里之后,老百姓不让他们从港口往外运,因为他们认为,同美国共同举行的以及北约许多国家计划于当年夏季举行的军事演习是非法的。即使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演习,克里米亚人也不愿看到明显不友好的别国军队踏上自己的土地。当时还流传着一种关于演习的神话,说这些“维和部队”登陆,是来消除半岛上“分离主义者叛乱”的,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愤怒。
109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阿卢什塔市国防部“友谊”疗养院过了两天才离开。这两天他们实际上一直被当地居民包围在大楼里,老百姓要美国军人滚出他们的城市。疗养院服务人员拒绝为美国佬做饭,拒绝为他们收拾房间。而且,在不速之客入住当地的第二天给他们断了电,堵死了下水道。美国佬离开阿卢什塔的时候更像落荒而逃,市民们报以高声欢呼,还补充说,“只要全部军人和军用物资不运出克里米亚,抗议活动便不会结束”。
为了躲避抗议和纠察线,海军陆战队员通过“秘密小道”被运送到费奥多西亚,在当地他们还有将近150名同事处于被围困状态。疗养院成了外国军人驻扎的地方,有人试图借助警方把围困疗养院的纠察队员驱走。但抗议者中间的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和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制止了冲突的升级。
疗养院工作人员告诉大家,美国人自闭在自己的楼层,安排了岗哨,不许当地人员进入他们的“驻地”,靠吃干巴巴的口粮度日。
抗议行动席卷克里米亚其他城市,参加抗议活动的成千上万公民不仅来自克里米亚,而且来自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扎波罗什。
美国人终于大失所望,只好登上一艘租来的货轮,向不明方向驶去。他们终于离开了冷眼向客的克里米亚海岸,离开了这些不愿在自己这片被俄国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见到外国军队的执拗的人民。
当我们回头再看取得“独立”的种种途径时,可以坚定地得出结论:除了白俄罗斯,在乌克兰也好,还是其他各苏维埃共和国也好,都是因为发生了政变:当时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被摧毁了,社会政治制度被彻底改变了,这些都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多年的苦难。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别洛韦日交易的“恶根”,当然源于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力图攫取个人权力的图谋。其实,这一协议对于一个国家及其3亿人民的命运可能造成的悲惨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可能却丝毫也未能对他们起阻挡作用。这就是政治上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造成的恶果!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利用权力来办各种各样的事之外,一定还要用它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分支机构,以监督行政机关的活动,清除国家奥林匹亚之山可能作出的任何一个忘乎所以的行为的道理。
俄语与乌克兰语
我想从一则真实的笑话开始这一节。在独立后的乌克兰首都召开的一次高级会议上,会议主席向出席者提问:“大厅里有没有莫斯科佬呀?”回答:“没有一“那就转用俄语吧。”
这则笑话显示出俄语在乌克兰的实际状况。在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今天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对立,在各种政治主张方面存在着对抗,而且还在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上,其中包括语言问题上,也存在着对抗。
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管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是在乌克兰,关于俄语和乌克兰语的问题,一直被民族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用来作为武器。他们千方百计强调,乌克兰语的主导地位是乌克兰民族自觉的基础,是乌克兰人的精神基础。与此同时,共和国内部出现了一种不能容忍俄语的偏执态度,进而更发展成为一场针对俄语的真正的“语言战”。所有这一切又推动极端民族主义卷起风暴,化为激化民族关系的根源,为激化民族关系提供营养。因而语言在乌克兰生活中也就成了一个政治杠杆。
我在前几章中已详细谈到这一问题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的情况。但要把这些国家在俄语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局势完全搬到乌克兰来当然不恰当。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有自己的语言,而俄语则是由于这些地区并入俄罗斯帝国和进入苏联后在移民过程中出现的。
谈到乌克兰的俄语和乌克兰语问题,我认为必须回顾一下我们的共同历史。否则对这个问题就很难评说。由于民族主义政客一伙的兴风作浪,这个问题便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和人文科学问题。
俄国的西南部是罗斯国家的摇篮。这一地区的居民当时便自称为罗斯人。13世纪鞑靼人入侵后,统一的罗斯分成两部分,被称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