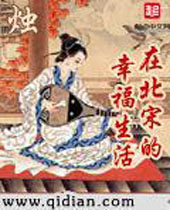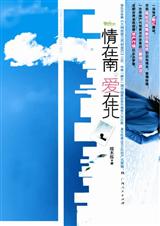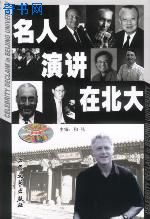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
安子文同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七大”以来的八年当中;情势已有很大变化……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考验了领导干部。有些同志在战争中、土地改革中、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对这些问题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确的。现在看来;整风以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这些同志在整风中背上了包袱;觉得教条主义的人不行;经验主义的人也不行;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意见;不和人商量问题;因此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陆续翻了船。党的组织部门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应该从运动中来看干部;看组织。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观点上看问题;则必然要犯错误。
张秀山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时;刘少奇同志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张秀山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三)郭峰的发言
1953年10月10日安子文作了关于中央组织工作检讨发言后,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同志不满意,认为哪个检讨缺乏政策思想性,不认真。在酝酿与讨论大会发言时,只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主要是说要照顾到中央组织工作历史发展情况,不能要求过高,责备更多。郭峰在准备大会发言时为采纳这个意见。
发言稿写成后,由大区与会同志再度讨论,作了某些辞句修改。1953年10月14日下午,张秀山在大会发言后当场看了一下,提出要加上两点,一是对党员八条标准问题提法的意见,一是对整顿基层组织决议中有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不妥当提法问题。但郭峰认为似乎没有必要,故两条意见均未加进去。
因为巩固在1953年10月3日就去了南方,他没有看过郭峰的发言稿。
1953年10月15日,郭峰在大会上发了言。
张秀山的发言,涉及的都是大问题;郭峰的发言主要是业务方面,其内容大致是:【注27 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简报。】
安子文同志的个人检讨……从检查过去组织工作方面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检查工作的前提,没有检查的标准,因而也就难于辨别是非,也就必然缺乏思想性、政策性,质量不高。
现在就东北地区小组对安子文同志发言的讨论中所提出的意见,综合为以下三个方面来谈一下。
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几年来,三次调动干部到新解放城市搞接管,到新区搞土改,接着,又调干部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之后又集中一批力量建立中央机关,并按照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大力地组织与指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整党建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要从保证党的总路线的贯彻及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的完成和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上来检查,也即是从党在恢复时期的组织工作任务的执行上去检查,我们认为是有着严重的缺点和某些错误的。主要表现在:
1、从贯彻二中全会决议,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规定,及时组织力量转入城市工业,为以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准备上来检查则做得很差。对于如何从组织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更好地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认识不够,研究得很少。中组部对中央有关组织工作方面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贯彻很差。
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精神领会与贯彻不够,对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新情况认识不够。例如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上,有“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提法,这显然是对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的一种摇摆。又如在同一会议上,没有强调指出当时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将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危险。之后,在对农村整党要求上,也没有及时地提出防止与反对富农思想的影响,直到“三反”、“五反”时期才为中央指出与各地实践所补正。又如在是否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这样的原则问题,子文同志在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是有错误的。又如在党的干部政策掌握与贯彻上,“三反”以前,对任人唯亲,特别是对于只重文化、才能,忽视政治品质的倾向,没有及时地发现与纠正,没有展开必要的斗争。这实质上是一种“右”的观点。
从党的组织建设上来看,也还表现出对于坚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组织原则的严肃性,认真地、有效地贯彻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议不够;对于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与提拔工人干部的指示,对工业老干部的培养提高与关心做得很差。如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对于警惕和严格防止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富农、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分子混入党内,以保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方面注意不够。在对待叛变自首分子的审查上,也还不够严肃,使用也有不够妥当的,这自然就增加了领导骨干中的成分不纯。反之,对农村、工厂中党员所存在的问题却估计得很严重,仅仅根据某些地区农村支部的典型调查,就估计农村有30~40%是不够党员条件者;对工人党员也不适当地估计有25~30%是不够党员条件者。事实证明农村不够条件者至多不过10%左右;而工厂中党员不够条件者以旅大为例,至多也只有4%、5%。为什么对于叛变自首分子却严格不够,而对工人农民成份党员的问题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呢?这是否仅仅是个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问题?是否与政策思想指导上存在的某些偏差有关?
关于积极地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以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生长优秀的工业管理人才,以便更有力地保证经济恢复与工业建设任务的完成,这正是党在过渡时期在党的建设上的一个严重的组织任务。对此,中央在1948年底即有指示,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以及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也均有所规定,但作为中央组织部职责上来检查,自1951年以来很少看到中央组织部都对这方面工作的系统检查与具体指导。没有认真组织执行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工人党员的精神,仍然只是把整建党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未转向城市工矿。这样也就大大地影响了工人干部的生长与提高。
3、中央组织部在组织工作的业务指导上,或多或少的存在脱离当前中心任务,而孤立静止的进行工作的现象,对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经验学习不够的严重缺点。
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组织工作的政策思想指导上,对党的总路线,对恢复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任务存在着不明确和模糊的地方,甚至有某些“右”的观点。因而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贯彻就很不够……因而在组织工作业务指导上也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脱离当前中心任务去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组织工作的现象……再加上个人领导上的“打杂”思想,钻研不够,应该认为这是政治责任心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才是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基本问题。
(四)轩然大波
张秀山和郭峰的发言都涉及到关于组织不纯问题,张秀山甚至说中组部“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叛变自首分子“处理得不严肃”;【注28 这里暗示所谓61人叛变自首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刘少奇的罪状之一,11届三中全会以后,此案得到平反。】还有对待富农党员的问题,这些显然是有所指,因而触怒了一些人,引起极大震动。讨论时,华东、西北、东北代表的意见一致,华北坚决反对,双方争吵得厉害,竟起轩然大波,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讨安伐刘”风波。
按理说,张秀山和郭峰都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在会上当面讲,而不是在会下背后讲),不仅是分内的事,是他们的正当责任与权利,而且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党章规定的事。即使这些意见提得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也不能由此说他们是“反党”,是“搞阴谋活动”。
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或许是毛泽东始料不及?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收场。
由于会议出现较大的分歧,毛泽东指示大会暂停,先解决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要求领导小组按照《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团结。毛泽东还召开书记处会议、各大区书记会议,讲团结。
针对这种局面,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上说:“……会议进展得不够好,出了偏差。中央认为,问题出在中组部内部不团结、有矛盾上。因此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也就是饶、安的矛盾问题。”
(五)风向陡转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提出,全国上下要求团结稳定,再争论下去,既不利于团结,又不利于贯彻执行总路线,违背民心、违背大局。谁来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如果说,在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还情愿充当“批薄射刘”的“后台”,那么在组织会议上,饶漱石的确有辫子可抓,毛泽东不能为其辩护,不能为“讨安伐刘”承担责任。他权衡利弊,决心改动初衷,暂停这种“桌面上的斗争”,向刘少奇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他不再强调“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转而强调团结,强调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刘少奇10月22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的讲话稿上,加了以下批语: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注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同日,他对饶漱石的发言稿补充道: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注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于是,会议的方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由原先批评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着重解决饶漱石对这次会议的领导思想问题,批评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刘少奇、安子文野进行了自我批评。
争论暂时平息,会议于1953年10月27日结束。
这段时间,高岗正在南方休假,对组织会议发生的事情,只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片段。尽管高岗没有布置张秀山和郭峰去发言,他事先也没有看过他们的发言稿,他们发言时他根本不在北京,但他还是被卷进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政治漩涡。正如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上所说:
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注3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第五章 风云突变
直到1953年10月之前,毛泽东对高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几何时,他突然180度大转弯,对高岗产生严重的怀疑,弃之如敝履。这是为什么?
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段话:“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注1 “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0页。】
毛泽东长期没有看出高、饶是坏人,或许因为他们早就是坏人,早就搞反党阴谋活动而未被发现;或许他们原本就不是坏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活动而无可“发现”,当然也就不会看出,更不会想到他们是坏人。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到了1953年冬才发现”的“阴谋活动”究竟是什么?邓小平说得很明确:“高岗就是要把刘少奇拱倒。”
高岗自己在反省时一再表示,1953年以前,他只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来北京以后,特别是1953年上半年以后,才有了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既然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满意,他就要助毛主席一臂之力,造舆论,找机会,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
对刘少奇不满,甚至反对刘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拉下来,就等于反党、就等于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么?
其实,“反对刘少奇”并非问题的要害,因为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意愿。并且,在组织会议之前,毛泽东一直是在借助高岗来反对刘少奇的,即所谓“倚高反刘”。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当初高岗散布的许多关于刘少奇的“坏话”就会明白,比如“少奇进城以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少奇不经过主席就擅自发中央文件”、“毛主席只当党的主席,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等等,除了毛泽东本人,哪个“自由主义者”能说这种话?而且,后者已被历史证明是毛泽东的主张。
问题在于,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