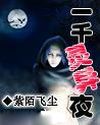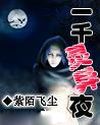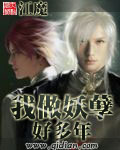一千多年前的荣辱是非:大宋的人大宋的事(选载)-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西夏军队里步兵人数最多,在山区作战时步兵是当仁不让的主力,西夏最精锐的步兵被称为“步跋子”,特别是横山党项羌组成的“步跋子”,身手敏捷,翻山越涧如履平地,远程奔袭其快如风,在复杂地形作战的能力很强,“平夏兵不及也”。
他还挑选党项贵族子弟中能骑善射者组成宿卫部队,既壮大了队伍,还能挟他们当人质,令那些党项部族的首领不敢对自己轻举妄动。
元昊虽然是个狼性不泯的杀星,但在军事上确实很有眼光,居然组建了一支炮兵部队,虽然只有二百人,可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成建制炮兵了。他们使用的武器叫“旋风炮”,能立在骆驼背上发射,发射的也不是火药炮弹,而是拳头大小的石块。
这种炮大约在当时很有名,以至于后来《水浒传》的作者把梁山好汉柴进的绰号安排为“小旋风”,其中的旋风就是指的这种炮,而不是自然界中的旋风。
最能体现元昊狼性的是他还专门组建了劫掠人口(抢回去当奴隶)的部队,这支部队就叫“擒生军”,有十万人之多。只要一声号令,立马就能开出十万的专业抢劫大军,这恐怕连现代的恐怖分子也自叹弗如。
当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基础建设都完成之日,也就是元昊登基当皇帝之时。
1038年(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的南郊筑起祭告天地的祭台,祭拜天地之后,坐上了龙椅,宣布一个新的国家诞生,这个国家的国号是大夏,历史上习惯的叫法是西夏。
此时,中华大地上,北有契丹辽国,西有党项西夏,中原是宋朝,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魏、蜀、吴三国时期英雄豪杰辈出。宋、辽、夏三国时期,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物?
两个不能不说的人物(1)
元昊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一方面凶狠残暴,一方面又彬彬有礼;一方面极端蔑视宋朝的软弱,一方面又羡慕宋朝的文明;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任人唯贤,不讲究所属民族。
历史再一次证明人性的复杂与多元,单纯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并不存在。
西夏建国时就有意模仿宋朝官制,例如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御史台管理监察弹劾,磨勘司管官吏考察和升降,等等。
这些模仿,因为是国家机关的名称,你用我也能用,还算说得过去,最绝的是管理西夏首都兴庆府的衙门干脆就叫“开封府”,把宋朝首都的名字直接就拿了过来。
在官员的任命使用上,元昊很能放得开,不管是党项人还是汉人,只要有才能,别说是地方官,就连中央机构里的中书令、御使大夫、侍中这样的高级领导都可以担任。在这一点上,他比宋朝皇帝强多了,在宋朝政府明文规定“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明显的有大汉族主义的成分在里边。
而元昊即位后,任命了一批官员,仅从名字上看,其中汉人居然占了大多数,但是都为文职官员,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军队的主官都是党项人。这是元昊唯一没有对汉人开放的权力领域,他深知军权意味着什么,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把军队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党项人手里。
元昊知道党项的文明程度比中原低,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西夏除了大力兴办蕃学,培养本民族的人才外,还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和知识分子,在他的高级参谋里,大多数的都是汉人。
这就给了许多不得志的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张元、吴昊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
张元、吴昊是宋朝永兴军路华州(今陕西渭南东)华阴县人,地地道道的汉族人,后来却跑到西夏去“谋发展”。
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后来入西夏时改的,原名不见于正史,因为当初他们在宋朝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卒,到了西夏之后才展露才华,当上了高官。
这张青年和吴青年才华横溢,而且很有抱负,认为自己能干一番大事业。年轻人有些才干,难免有时眼高于顶,少年气盛。但二人本质不坏,性情直爽,有西北汉子的豪放坦荡,尤其是张元,常“以侠自任”,干了不少助人为乐、行侠仗义之事。
人以群分,从他二人的朋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为人。
他们和同乡姚嗣宗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高谈阔论。
这个姚嗣宗字因叔,性情也颇豪放,喜欢议论军事,后当过华阴知县。在他当知县的时候,曾陪同上司陕西都转运使游览华州西岳庙,庙里原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高大雄伟,在上面还曾建有牌楼,在唐末时毁于黄巢战乱,转运使先生看到这个残碑感慨万千,说:“好一座石碑,可惜不知被谁给毁了。”
本来转运使也就是句感慨的话,可偏偏姚嗣宗就接上话茬儿说:“是小贼放火烧的。”
转运使先生以为是最近的事,就问道:“县里为什么不去收捕这些草寇?”
姚嗣宗回答:“县里兵力不足,无法与贼寇争锋。”
这位转运使火了,斥责道:“无法争锋?那国家养你们这些县官是干什么吃的,不会想办法吗?再说了,是哪个贼人这么厉害?”
姚嗣宗恭恭敬敬地回答:“人们都说这个贼人的名字叫黄巢。”
转运使顿时哑口无言。
有的史载说这位转运使是李参,有的说是包拯,都是当时的名臣。可任你学识再渊博,也不可能事事都了解,不知道这段往事也很正常,可姚嗣宗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露痕迹地揶揄了他一把,虽说无伤大雅,可毕竟有着很重的嘲弄意味在里面。幸好那位转运使心胸豁达,没有打击报复他。
这种目无余子的人很难在人人都自视甚高的大宋官场混明白,姚嗣宗最后也没能显贵。
张青年和吴青年也没能通达,科举屡屡碰壁,因此郁闷至极,他们经常借酒消愁,然后写诗发泄怨气,姚嗣宗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穷鳞。”张元也曾作咏鹦鹉诗:“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此中已有另攀高枝之意。
但他们不甘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母国,还想最后一搏,便学班超去投笔从戎。当时正值元昊加紧称帝建国的步伐,宋朝也嗅出了不安的味道,西北边境也在准备应变,自负有王佐之才的张、吴二青年想抓住这个机会谋取晋身。
来到边境,心高气傲的二人不甘心低声下气地去拜见官员,就找人刻了块石碑,凿上自己写的诗,雇人拉着成天在大街上转悠,想以此来造成轰动效应,引起边防高官的注意。还别说,这招挺好使,边帅还真召见他们了,但谈了一番话之后就没了下文。
张、吴这二位,干等了好多天,知道不是科举出身的自己不受重视,想在大宋出人头地是没指望了,最后下定了投奔西夏的决心。但人都是有感情的,故国难离,他二人在项羽庙泪如雨下,高歌三天,慷慨悲凉的歌声绕梁不绝。
正所谓亦哭亦歌奇男子,两人自负奇才,却屡次不被赏识,不知道是二人的不幸还是大宋的不幸。
痛哭一场之后,二人偷渡边关,进入西夏,一路跋山涉水,在景祐四年(1037)来到西夏都城兴庆府。二人故伎重演,不去求见西夏高官,而是成天在城外的一家酒店酗酒,喝得昏天黑地之后就在墙上来点“涂鸦”,写上“张元吴昊到此一游”之类的东西。
此时他们已把姓名改为张元、吴昊,故意用了元昊的名讳,再加上他们到处在墙上题名,果然引来了西夏人的注意。不过,他们不是被客客气气请去的,而是被巡查的西夏大兵一根绳绑到了官府。
元昊听说有如此胆大妄为的人,就想亲自见见,见到这二位后,元昊斥责他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触犯我的名讳,你们看来是活腻了吧?”
张元、吴昊并没有像元昊想象的那样害怕,反而冷笑两声,说道:“你连祖宗留给你的姓都不在意,怎么就在意自己的名字呢?”
这话一入耳,元昊僵在了当场,因为他此时还在姓宋朝赐给他的赵姓。元昊毕竟是一代枭雄,很快就恢复常态,微笑着看这两位,他已经明白这二位是有为而来。
元昊留下张元、吴昊长谈一番,觉得二人确实不凡,就马上赏下官职,二人梦寐以求的富贵,终于在西北边陲到手了。时间不久,元昊还派人偷偷地把二人的家眷接到西夏,二人对元昊更是感激。
被宋朝弃置不用的这二人,不过是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的一个缩影,元昊在这些汉族人才的辅助下,在第二年称帝,他称帝建国不久,就任命张元为中书令,吴昊也被重用。
要说西夏的中书令有职有权,相当于宋朝的参知政事,不像宋朝只是一个荣誉虚衔。张元当上了副宰相,一步登天的他对元昊感激涕零,从此就把自己彻彻底底、从里到外地卖给了党项西夏。
张、吴二人对元昊在大政方针的制定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史称“夏人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这二位对宋朝不重用自己,始终窝着一肚子的邪火,总想狠狠报复一下,能把大宋灭了最好。
他们竭力鼓动元昊独立,给他讲历史上匈奴人刘元海、前秦氐族苻坚和鲜卑北魏的功业,其实不用他们说,元昊早就有这个心思,但他们的话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
张元不仅在语言上煽动元昊称帝自立、夺取宋朝领土,还亲自操刀制定了对付宋朝的战略方针。他对元昊说:“先夺取关中,据山河雄关之险,对宋可攻可守,大占主动。然后再联合契丹,让他们进军河北,我们两面夹攻,宋朝首尾难顾,只好听任我们的宰割。”这条计策绝对称得上狠毒阴险,假如辽国撕毁和约挥兵南下,党项西夏兵锋东指,整天不思武备的宋朝存亡还真就难说,也许靖康的那一幕就会提前上演。
张元、吴昊的遭遇本来让人扼腕叹惜,可他们在投靠异族之后,竟想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为代价,来发泄自己的个人怨恨,这种做法实在是十足的小人行径。
元昊的野心再加上张、吴的策动,夏宋战端再起。
刀剑铿锵中,流血的不仅是宋朝,西夏也在不停地流血。
张元还曾亲临前线出谋划策,在1041年(宋庆历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的好水川之战中,他还跟随元昊参与机谋。这一战宋军损失惨重,大将任福以下几十名将校全部战死,而战后张元在界上寺壁题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面对同胞为保卫家园而流淌的遍地鲜血,张元洋洋得意地在诗后署名:“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有人替张元辩解,说他不是汉奸,对比流血牺牲的大宋将士,真不知道张元不是汉奸还能算是什么东西!
好水川之战后,张元建议元昊出兵渭州,深入关中,待机攻取长安,他说:“宋朝最精锐的部队都部署在边境一线,关中地区并没有防备。我们以大量的部队沿边骚扰,使宋军精锐不敢离城,然后寻找时机大胆穿插,只要取得潼关便可关门打狗,长安则唾手可得。”
元昊采纳了他的意见,发动了定川寨之战,取得胜利后挥军杀入渭州境内,连续攻破栏马、平泉二城,西夏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宋朝百姓苦不堪言。
出这条毒计的张元一路随军前进,不知道他看到百姓如此悲惨有何感触,估计他感到的是报复泄恨的快感,看看他替元昊做的露布(就是布告)上,兴奋地宣称“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借元昊之口表达了奸计得逞的得意。
张元虽然竭尽全力地辅佐元昊,但二人还是有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上两人经常意见不一致,张元主张把攻取的宋朝土地委任汉族官员治理,不要轻易放弃,这样西夏才会不断地扩大疆域,增加税赋收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是元昊的豺狼本性不改,往往攻占一个地方之后洗劫一空便不管了。
这样,随着战争时间的推移,西夏军劫掠的速度跟不上消耗的速度,没有再生产的西夏财力出现了后继无力的局面,这也是后来元昊不得不与宋朝和谈的重要原因。
虽然与宋议和,可元昊又和辽国大打出手,张元屡次劝谏,甚至和元昊激烈争执,但元昊就是不听他的,两人合作的“蜜月期”已经一去不回头了。
张元念念不忘谋取中原的计划,没有元昊的支持就是一张白纸,张元因此成天郁郁寡欢,在1044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十二月去世。
他与狼共舞了八年,最终被自己心里的仇恨杀死。
一败三川口(1)
宋朝不能容忍元昊分裂出去,尽管以前也只是形式上的一统天下。因此,在元昊上表要求宋朝承认他的皇帝地位时,大宋君臣都决心采取武力行动,把元昊这个分裂分子镇压下去。
赵祯下诏把过去封给元昊的所有官职爵位都撤销了,这不过是表明宋朝的态度,人家都自己做皇帝了,难道还会稀罕你给的什么节度使和王爵吗?
要打击元昊,必须得做出实际的动作。
但宋朝实在是很难主动出击到西夏境内,多年以来宋朝根本没有整顿武备,以至于——“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别说进攻,就连守都成问题。
宋朝只好采取经济制裁,停止和西夏的贸易往来,想从经济上压垮西夏。同时还发布通告,宣布谁要是能擒杀元昊,就让他当定难军节度使,这通告是给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看的,其中也包括党项世仇吐蕃首领厮啰和党项内部的部族首领,宋朝还在希望能“以夷制夷”。
宋朝自己也加强边防,在边境上囤积粮食,修筑堡寨,调兵遣将,忙得不亦乐乎。在元昊称帝后,赵祯就任命知永兴军夏竦兼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环庆路安抚使,元昊进表后,又派庞籍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协同夏竦、范雍备战。
战火在元昊称帝的第二年燃起,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西夏军队进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被宋朝守将卢守击退。在这场战斗里,一个没有品级的小军官战功卓著,被破格提拔为正九品右班殿直,这名小军官就是后来扬名四海、被赵祯倚为长城的